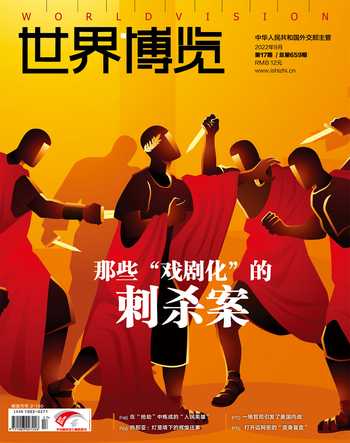《獨行月球》:宇宙那么大,我們還會遇見
Ybor
2018年,導演張吃魚看到一部名為《獨行月球》的漫畫,被其中獨自生活在月球的孤獨的男主人公打動,產生了改編成電影的愿望。如何讓原著故事既保持漫畫的精髓,又符合電影創作的規律,成為了擺在張吃魚面前的難題,他帶著3位編劇推翻一個又一個可能性,讓電影的面貌一點點浮現。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出品公司開心麻花遭遇了經營危機,張吃魚頂著壓力進入了漫長的拍攝和制作。經過4年多的努力,電影《獨行月球》終于在2022年7月29日正式上映。
作為國內罕見的科幻喜劇片,《獨行月球》上映首日以21.2萬場次的放映數打破了內地影史國產片單日總場次紀錄,首日票房突破2.39億元人民幣,成為疫情之后暑期檔票房最高的一部電影,也被電影行業視為“救市之作”。
與開心麻花之前的一眾影片不同,《獨行月球》并不是一部中等制作的喜劇片,像《夏洛特煩惱》《羞羞的鐵拳》和《驢得水》等影片,多以優良的劇作和演員的表演吸人眼球。《獨行月球》是開心麻花走出舒適區的冒險一棋。影片制作成本超過5億,采用了大量的特效場景,走的是重工業科幻片路線,雖然整體基調依然為喜劇,但它足可稱為今年國產科幻片中的重頭戲。
與以往開心麻花作品不同的是,《獨行月球》并非原創劇本。不過,影片只保留了漫畫中的主線故事,即男主角的冒險拯救之旅,而沈騰飾演的獨孤月和馬麗飾演的馬藍星兩人之間的愛情線,是開心麻花團隊后來添加的。
“獨行”體驗
影片一開始,便交代了整個故事的科幻背景。一顆從火星軌道上“出軌”的小行星將要撞擊地球,人類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為此,科學家們啟動了“月盾計劃”,先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研制用來摧毀小行星的核彈,一旦小行星被炸成碎片,“月盾計劃”的團隊再用月球來抵擋,以防碎片墜落地球,引起沖擊波。女主角馬藍星便是“月盾計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而獨孤月是這個計劃的機械維修師。
人類經過多年的努力,終于在小行星撞擊地球之前將其摧毀。本以為危機就此解除,沒想到,遺漏的一顆小行星碎片“派”,將要橫掃月球表面。馬藍星匆忙之下,召集所有人緊急乘坐火箭返回地球,唯有獨孤月錯過通知,被遺落在月球之上。正當獨孤月心灰意冷之際,他卻目睹了一場更大的慘劇,行星碎片“派”掠過月球,迎面撞向地球,頓時板塊斷裂,海嘯席卷各個國家,火山噴發、地震等各類重大自然災害接連發生。

為抵御小行星的撞擊,拯救地球,人類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計劃”。

《獨行月球》作為一部拯救主題明確的科幻喜劇,把一個普通的“中間人”放置到選擇的正中心,讓小人物在蛻變中找到他的意義和信仰。

電影的“男二號”是一只金剛袋鼠,這是目前國內制作的難度最高的數字生物形象,它身上的毛發有5000萬根,每一根都需要用電腦技術進行渲染。
在獨孤月看來,他可能是整個宇宙中唯一幸存的人類。但他并沒有為此感到半點慶幸,而是在偌大的基地悲戚哀嘆,想要在擺爛一段時間后自殺。然而,人類并沒有就此滅亡,他們如同《流浪地球》中的幸存者一樣,從地表轉移到了地下。但是,隨之而來的憂郁和絕望情緒,在幸存的人類心中開始不斷蔓延。當再也無法看到太陽、整日躲在地下茍活且只能保證最基本的生存質量時,絕大多數人確實很難在這樣的處境下活一輩子。
幸好此時馬藍星想出一個辦法,將獨自在月球生活的獨孤月的視頻紀錄向全球人類直播,并用旁白解說的方式,將其塑造成一位月球英雄,重新燃起地球上幸存者們的希望。事情真的會如此順利嗎?獨孤月能否重新回到地球?而地球上的人類又是否可以徹底擺脫小行星撞擊的危險?
《獨行月球》是雙向式的救援,地球上“月盾計劃”的成員試圖拯救獨孤月,同時,獨孤月也在拯救心愛的人以及整個人類。其實,在一開始,馬藍星之所以向全人類轉播獨孤月的日常生活視頻,便是為了消散人類的悲觀和絕望,所以有的觀眾看完之后調侃道:“開心麻花真正詮釋了,拯救全人類的其實是喜劇。”
后來,獨孤月遇上了金剛袋鼠,兩人之間相愛相殺,尤其是后者既像萌寵又似猛男的反差設定,讓這對月球上的“難兄難弟”產生了強烈的化學反應,為人類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笑料。當獨孤月真正聯系上“月盾計劃”成員之后,他從一個公共媒介領域中的“英雄”轉變成幸存者。此時,地球上的人類又變成了拯救者。而到了影片的高潮部分,當獨孤月歷時多年、好不容易和金剛袋鼠回到廣寒宮空間站時,卻得知當年“派”產生的行星碎片即將撞擊地球。他又再次轉變成了拯救者。
這種“拯救者”和“被拯救者”身份的不斷轉換,讓《獨行月球》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情緒張力。可以說,開心麻花團隊這次不單單貢獻了一場優質的喜劇,更是將個體和集體之間的情感鏈接表達得絲絲入扣。
由于有《流浪地球》幕后團隊的全程參與,《獨行月球》的科幻場景非常細膩逼真。獨孤月在小行星碎片撞擊月球時的躲閃場景,以及他駕駛著返回艙在隕石群中的穿行過程,都不比好萊塢的科幻大片遜色多少。至于此次的喜劇效果,除了有麻花式的打臉反差的喜劇手段,更有對演員姓名、流行文化的巧妙挪用。
《獨行月球》在類型的整合層面做得異常圓融,將科幻片里的新穎設定、高能場景,麻花喜劇的爆笑對白,以及強大共同體的情感連結無縫榫合,你會自然而然地被其吸引。
開心麻花式科幻輕喜劇
《獨行月球》票房背后是不可忽視的巨大投入。劇組使用了15個攝影棚,累計4.1萬平方米,整個場景的建設花了半年多,為了實景還原月盾基地,他們將200噸的砂石鋪滿了6000平方米的攝影棚,用來模擬月球表面的粉塵。片中超過九成的內容涉及視效制作,有時候一個鏡頭就要花費技術人員一整年的時間。其中,電影的“男二號”是一只金剛袋鼠,這是目前國內制作的難度最高的數字生物形象,它身上的毛發有5000萬根,每一根都需要用電腦技術進行渲染。電影里不被注意的一秒鐘鏡頭,可能需要27天的時間進行后期制作。
進入開心麻花之前張吃魚會在網絡上寫作,他平時癡迷動漫、游戲和電影,算是一個典型的80后“二次元”。張吃魚喜歡用“熱血”形容自己的創作,在他看來,電影有漫畫不具備的“景深”,前景和后景都可以加入豐富的表達。漫畫較之現實生活總有一些夸張和變形,整部影片的喜劇氣質正好與之相符合。“現實的質地很重要,科幻片本身是高度架空的,喜劇片又特別需要和本土文化結合,笑料要接地氣。”為了將二者融合,張吃魚設計了一些接地氣的細節,比如獨孤月面試時詢問月球的社保該往哪里交。一般科幻片的色調偏冷,喜劇片的色調偏暖,最終《獨行月球》決定,在冷色調的太空出現穿著黃色太空服的人類。
在馬藍星的扮演者馬麗看來,《獨行月球》是一部悲劇內核的喜劇電影,起初有主創提出馬藍星太嚴肅了,但她覺得這個角色身上不能有太多喜感,否則電影的基調就變了,而獨孤月應該更像是一位“孤勇者”。“往常我們拍喜劇電影,只是想辦法讓觀眾笑。笑過可能就過去了,更難的是讓大家感同身受,笑中帶淚。”原著漫畫里沒有愛情的主線,更多呈現了人類孤獨的狀態,張吃魚改編時賦予了《獨行月球》浪漫的氣質。男主角“獨孤月”和女主角“馬藍星”的名字分別代表了月球和地球,月球以地球為中心公轉的天文現象也暗示著兩個人關系的走向。獨孤月對馬藍星的愛情僅僅建立在擦肩而過時的驚鴻一瞥,兩個人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面地深入交談過。在電影最后,獨孤月將自己對馬藍星的愛情轉換為一種對人類的大愛,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擋住了隕石的襲擊。10多年后,馬藍星重回月球,和獨孤月有了一次想象中的重逢。
電影上映后,有人質疑《獨行月球》“先喜后悲”,結尾強行煽情,張吃魚不同意這個說法。“故事沒有提供合理的情感空間,本來不感動,你把它硬往煽情了做,這叫故意煽情。我所做的工作其實是在克制,故事本身特別煽情,我還故意做了消解。”

隕石來襲,全員緊急撤離時,維修工獨孤月(沈騰飾)因為意外錯過了撤離通知,一個人落在了月球。不料月盾計劃失敗,獨孤月成為了“宇宙最后的人類”,開始了他在月球上“破罐子破摔”的生活。
2022年4月,為了慶祝中國第7個航天日,國家航天總局召開“中國航天日”新聞發布會,曾釋出《流浪地球2》和《獨行月球》的海報,兩部影片都在位于青島的同一個影視產業園置景拍攝,使用同一家特效公司。
或許不是偶然,兩部爆款電影的故事內核都是“中國人拯救地球”的敘事。華裔學者、威爾斯利學院東亞系主任宋明煒的研究認為,中國科幻小說自20世紀第一個十年誕生以來,“中國將成為世界大國”一直是創作的核心主題。宋明煒指出,科幻小說在當時被稱為“科學小說”,是梁啟超于1902年創辦《新小說》時推動的新文類之一。梁啟超本人的科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雖然沒有完成,卻為諸多同代科幻小說家所借用,旨在勾勒晚清改革者為中國的自強、民族復興、最終崛起為世界強國而繪制的藍圖。將近100年之后,這一主題再次成為中國科幻電影常見的內容。
“人類本身就對太空充滿了向往,這里面有對未知的好奇。”張吃魚說,最早的科幻電影《月球旅行記》就受到凡爾納小說《從地球到月球》的啟發,選擇了月球題材,“中國已經是航天強國了,我們有了做科幻片真正的基礎,也讓觀眾相信中國人登上太空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我想要拍那種特別有想象力的電影,太空就是最好的舞臺。”
為了讓幻想更好地對接現實,《獨行月球》劇組聘請的顧問團成員中不但有科幻作家,也包括航天航空領域的專家學者。科學顧問的工作一直進行到影片制作的最后階段,配音環節出現了一個問題:發射前的點火倒計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之后到底是說“零”,還是說“點火”?張吃魚說:請教專家后才確定,應該說“點火”。電影中,獨孤月的返回艙被擊中后旋轉起來,顧問專家專門計算過返回艙需要有多少空氣、艙門開到多大,噴出的氣壓才可以讓它停止旋轉。“雖然這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模型,但這種科學的計算是必要的。”張吃魚說。
扮演獨孤月的演員沈騰的大部分戲份都是獨自完成的,需要面對空氣說完所有的臺詞。為了表現出在月球失重的感覺,沈騰通過吊威亞來模擬在月面行走的感覺。盡管電影的科技含量很高,但電影中的金剛鼠不完全由特技制作,它的一顰一笑、一蹦一跳都需要真人演員完成。開心麻花的演員郝瀚接受了這個任務,他特地搬到北京野生動物園附近,用4個月時間觀察袋鼠的行動,還需要在拍攝時穿著笨重的“袋鼠服”——即便在電影最后的呈現里,他沒有任何露臉的鏡頭。
電影的最后,獨孤月的犧牲拯救了全人類,部分評論認為沒必要如此拔高,也讓這部喜劇顯得太悲壯了。張吃魚則認為:“這個人物的動機不合理才是強行拔高。獨孤月自己也說他沒有親人和朋友,他只希望可以保護自己所愛的人。他把私人的愛轉換為對人類的愛,我們不應該質疑這種愛的存在。”
(責編: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