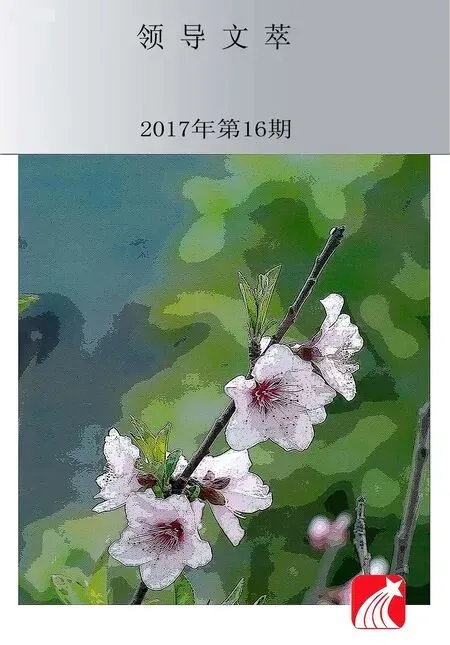撤縣改區,慎重從嚴
張靜
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印發的《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提出,要優化行政區劃設置,慎重從嚴把握撤縣(市)改區;嚴控省會城市規模擴張,確需調整的要嚴格程序、充分論證;穩慎優化城市市轄區規模結構。
相比2021年國家發改委提出的“慎重撤縣設區”,措辭從“慎重”升級到了“慎重從嚴”。2022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提升新型城鎮化質量,嚴控撤縣建市設區。
近些年,撤縣建市設區被視為最直接最快捷的城市擴張路徑,如今這一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由來已久
近些年,省會城市做大體量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合并周邊地市,如成都代管簡陽、西安代管西咸新區、濟南合并萊蕪等。周邊地區并入后,這些核心城市的面積、人口、GDP得到有效提升。二是通過撤縣建市設區來實現城區擴容。這種形式更快捷,由此帶來的城區面積和人口的規模化提升,讓城市在土地資源、地鐵城軌規劃等多方面更加游刃有余。
事實上,撤縣建市設區并非新鮮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我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路徑。“大量的小城市都是撤縣設市而來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葉裕民說。
昆山、江陰、義烏等一大批經濟實力較強的縣先后晉級為縣級市。據統計,截至1998年底,全國共有約350個縣級市。
而這其中,也不乏一些戴上了“市”的帽子、農村人口仍然占比較大的縣,城郊比例失衡、“假性城市化”十分突出。為此,1997年,國務院叫停了撤縣建市設區。
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設市標準,嚴格審批程序,對具備行政區劃調整條件的縣可有序改市”。
第二次撤縣建市設區“熱潮”從2014年開始。
據《華夏時報》統計,2014-2021年全國共有112個縣(市)被調整為市轄區,其中2014、2015、2016年分別有20、26、30個。而在此之前的20年里,每年成功設區的縣(市)最多不超過10個。
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擴容動作最多。
廣州2014年設增城、從化區;北京2015年設密云、延慶區;上海2016年設崇明區;杭州在2014年將百強縣富陽納入市區,2017年又將縣級市臨安設為第十個區;成都則在2015、2016和2020年分別將雙流縣、郫縣和新津縣設為區。
這一波撤縣建市設區潮中,北上廣深、廈門、南京、佛山等一、二線城市正式進入“無縣時代”,成都、西安的“強省會”戰略加快部署。
問題浮現
撤縣建市設區“遍地開花”,問題也隨之而來。
“撤縣設區是很多城市擴大地盤屢試不爽的手段。”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教授馬亮表示,一些城市通過撤縣設區追求土地和行政區劃意義上的城鎮化,并沒有帶動城鄉一體化、人口城鎮化和村民市民化,反而帶來不少城鄉接合部的治理難題。“攤大餅”式擴張在許多城市引發了市域行政區劃混亂、城市空間結構畸形、公共服務和施政效益低下的問題。
許多城市專家認為,一味地撤縣建市設區不但給城市帶來新的問題,而且對于一些偏遠地區或本身缺乏產業支撐的中小縣城也是不利的。這些地區遠離大城市,無論是產業吸引力還是公共服務都存在明顯短板,如果大城市紛紛將周邊小縣城合并,進一步加強資源要素的虹吸,偏遠的縣域將更加缺乏發展機遇。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認為,這兩年撤縣設區的沖動來自于很多城市的后備資源已經短缺,想要擴大地盤到下屬行政區域尋找更多發展空間。這種城市發展路徑與中國目前生態文明的大背景下走綠色發展道路、提升發展效率、減少資源消耗等理念是背道而馳的。所以,嚴控撤縣建市設區的提法是對近年來一些城市無序擴張的調整。
2021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2%,比2020年末提高0.83個百分點。
從國際規律看,一般城鎮化率達到60%以后,城鎮化速度開始放緩,進入城鎮化中后期。中國城鎮化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區簡單擴容的方式顯然不再適合。
“提高城市品質、豐富城市內涵、增強群眾幸福感和獲得感,遠比通過撤縣設區實現城市面積擴大更為重要。”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說。
2021年3月,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超大城市要劃定并堅守城市開發邊界,慎重撤縣設區。
2021年4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提出,穩慎把握省會城市管轄范圍和市轄區規模調整。
2021年,全國僅河南洛陽、福建漳州和三明、陜西寶雞4個城市的撤縣改區申請獲批,數量是近8年里最少的。
省域副中心城市
嚴控撤縣改區后,城市如何“生長”?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穩步推進城市群、都市圈建設,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為省域城市發展指明了道路。
“協調發展的意思是不折騰行政區劃,而是要探索如何用更市場化的手段建立起區域協同發展關系。”尹稚分析。
核心城市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應著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等,側重于總部經濟、創新、研發等環節。而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般制造業以及一些制造端的環節,應合理疏解到周邊地區、周邊城市。
尤其是以省會城市為主的核心城市,“在產業發展上,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應通過與周邊地區、周邊小城市一起,形成梯度分布、分工合力的產業體系。通過中心城市帶動周邊中小城市、衛星城的發展,打造現代化都市圈,實現產業、人口的優化合理布局。”尹稚說。
近年來,我國都市圈發展不斷深入推進。2019年,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2021年,南京都市圈成為此后首個獲批的都市圈。此后,福州、成都、長株潭都市圈紛紛獲批。2022年3月,國家發改委公布了同意西安都市圈發展規劃的復函。
近些年,除了“強省會”,“省域副中心城市”這一表述也頻繁出現于多地官方文件之中。廣東的湛江和汕頭,河南洛陽、江西贛州、山西長治、湖北襄陽先后被“官宣”省域副中心城市。湖南在“十四五”規劃中,將岳陽和衡陽列為省域副中心城市,安徽則提出建設蕪湖為省域副中心城市。
“之所以設立副中心城市,就是為了彌補省會城市以及主中心城市輻射不到的地方。”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秦尊文分析。
能成為省域副中心城市,距離省會200-300公里最為合適,太近難以發揮自身的副中心作用。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分析,“這類城市要有發達的交通體系,只有鐵路、公路、港口、航空港等運輸網絡都較完備,才能支撐作為中心的長期發展。”
產業層面,省域副中心城市要具備較強的帶動能力,有雄厚的產業基礎,能夠承擔轉移出來的非省會功能。
“例如,部分低端產業、大型批發市場、物流集散中心等,都不宜集中在省會。一部分非省會功能向副中心城市及周邊其他地區轉移,省會就能騰出空間追求高質量發展。所以,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對提升省會城市的發展品質具有重要意義。”秦尊文說。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吳垠認為,設立省域副中心城市還可能成為縣域經濟發展問題的又一解法。近些年,縣域出現實體經濟下滑趨勢,比如四川提出設立綿陽、德陽等經濟條件較好的地級城市為省域副中心城市,但這些城市的經濟規模離省域副中心的實際要求還有距離,而要縮短這個距離,關鍵就在于發展縣域經濟,促進組團式發展。
“重視縣域經濟發展,尋找區域發展平衡之道,對主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來說,或將成為參與未來區域競爭的重要資本。”馬亮說。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