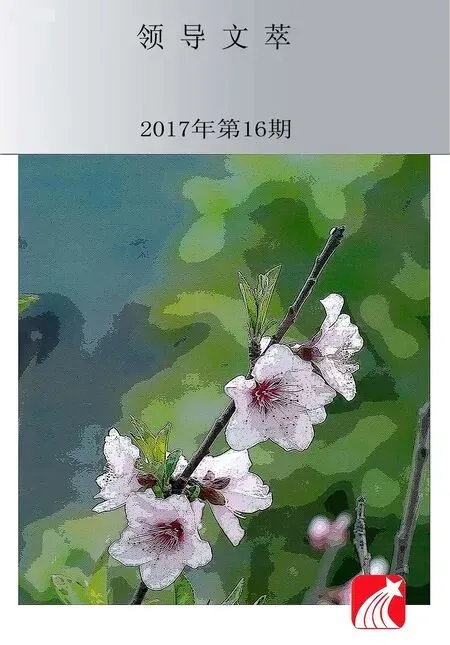曾國藩的格局
鄭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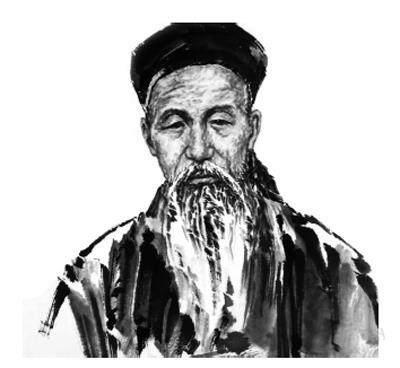
曾國藩給他九弟曾國荃寫信說,“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規模遠大、圣賢氣象。讀他的日記和他的書信,里邊不停地在講做大事要怎么樣怎么樣,所以他講的是格局要遠大。
所謂大格局就是說他超出了當時眾人的眼界、心胸和判斷。曾國藩在長達十年的戰爭中,在洋務運動中,哪些方面有這個體現?我總結了六條:
第一條,發布《討粵匪檄》。他1854年從衡陽起兵,帶了水陸兩支軍隊共一萬七千多人。他那個時候發了一個宣言,這個宣言叫《討粵匪檄》。這篇檄文從一開始就打出了忠義血性的旗幟,闡明了救時、衛道的起兵宗旨。這個事情對他來講是一個很有遠見也很聰明的做法。這個宗旨一明確以后,一方面,他得到了朝廷的首肯,朝廷就知道他“忠義”;另一方面,他又得到了士紳的擁護,中國的士紳基本上都是儒家經典教化培養出來的,所以士紳是擁護他說的那些的。曾國藩的《討粵匪檄》里講了一句話,他說,太平天國搞的拜上帝教。這個教是異教,太平天國反對孔孟之道,燒書,燒毀孔廟,這個是人神共憤,數千年的文明被毀壞,他為此痛哭。曾國藩把太平天國文化上很被動的一面揭示出來。他的忠義、血性、救時、衛道思想一出來之后,實際上使他自己獲得了政治正確這么一個標簽,所以他也形成了格局的高屋建瓴之勢。
第二條,另起爐灶、編練湘軍,戰略明確,艱難東征,攻克南京。一方面,曾國藩有政治正確這么一個立場;另一方面,他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在滿朝文武眾目睽睽之下大膽地改革創新。朝廷本來是讓他練民兵,結果他把它做成了軍隊;本來不要他出省,結果他跑去打武漢,還打贏了——當時咸豐皇帝特別高興,準備叫他做巡撫。實際上他是沒有軍餉,他借助“厘金”制度“勸捐”籌餉。這個厘金后來就成為我們中國最早的地方稅,是一種流通稅,過境一百塊錢的貨物要收一塊錢的稅收。所以,曾國藩的湘軍是帶著稅務局走的。他的以禮治軍的方法中,包括軍隊里的組織形式,比如說一個人他可以召集五百個人建立一個營,這個營打贏了就由他領導,這個營打輸了就解散了。這樣,由“將”來決定“兵”、“兵”擁護“將”,就改變了過去朝廷的軍隊見死不救、一哄而散那種狀況。這個建軍的思想當然比不上現代的軍事思想,但是有很多和中國的傳統契合的東西,比如說宗法關系;比如說以禮治軍;比如說“扎硬寨,打死仗”;比如說堅持從長江上游逐步推進的自主戰略——咸豐皇帝對戰局發展不滿意,很著急,很生氣,多次直接指揮,但是他堅持既定戰略,先到江西,后到安徽,控制長江上游,截斷對方的退路,鞏固自己的后援,又把李鴻章推薦到杭州,把左宗棠也推薦出去,兩個湘軍大將作為奧援,最后他終于攻克南京。
第三條,屢敗屢戰、堅忍不拔。“打脫牙”“和血吞之”,這些都是他的原話。他幾次遇到非常危險的狀況,三次在生死之間:一次是靖港之戰,他蹈水,企圖自盡;第二次是在鄱陽湖;第三次是在祁門。他這些時候都是處在危險之中。他是真正的書生領兵,迎戰強敵,逆勢而行。他跟家人講,“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辱之時”,皇帝猜疑、官場嫉妒、朋友使絆,千難萬險,他都把它們作為砥礪自己和修行自己的機會。
第四條,以拙誠聚人,團結眾人一起奮斗。他說“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他非常重視“誠”的作用,并把它看作和部屬處理關系的準則。他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把“誠”看得跟性命一樣重要。他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他說,“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這個話實際上就是說:我湖南人能夠鼓舞群倫,戡大亂,就是靠的拙和誠。
曾國藩團結人還有一條,就是他以身作則。他說,“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他說,“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所以他做官是“不要錢、不怕死”,是真正比較廉潔的一個官員。
第五條,自剪羽翼、急流勇退。南京打下來之后,滿朝文武和朝廷上這些核心領導人,包括慈禧太后、恭親王他們,都在看著湘軍怎么辦。那么,曾國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辭讓自己過重的權力,使自己急流勇退。第二件,裁撤湘軍,解除朝廷的疑慮。第三件,撤銷厘金局,安撫地方的民眾,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最后,他在金陵修貢院,開江南鄉試,收兩江士子之心。同時,他還辦了傳忠書局,開始出版被太平軍毀掉的傳統書籍。他這些措施的實行,消弭了朝野眾人的猜疑情緒,使他聲名鵲起,也就改變了自己過去那種被大家嫉妒和警惕的一種局面。
湘軍后來能夠善始善終,和其戰后急流勇退而積蓄的力量是分不開的。
第六條,從購“制器之器”到“師夷智”。他開展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開始就是買兵船、買大炮,后來曾國藩說,買的靠不住。當時有一個阿思本艦隊的事:從英國買來了軍艦以后,清政府委任的英國人就插手。曾國藩說我們要自己造,自己造就要買制造大炮、軍艦的機器,所以叫購買“制器之器”,這是他的一個進步,比“師夷長技”進一步。第二點,他提出“師夷智”,那么“師夷智”就不僅僅是在技術上學習西方,而且在科學知識上,甚至于一些人文知識上對西方開了方便之門,這是洋務運動中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比如,譚嗣同在維新時期能夠有那樣重要的思想,就是和他到曾國藩他們辦的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的圖書館看了很多西洋的書有關系。
(摘自《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