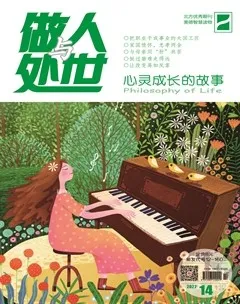張曼菱與任繼愈的“隔代親”
侯愛兵


不覺山行遠,登高已忘年
作家張曼菱與國家圖書館前館長任繼愈,有一段珍貴而又神奇的“忘年交”。張曼菱說:“我像對父親一樣對他。”任繼愈說:“我們有緣。”兩人究竟有著怎樣的緣分呢?張曼菱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是西南聯(lián)大研究者。任繼愈是北京大學1934級學生,曾就讀和任教于西南聯(lián)大。
張曼菱出生于昆明,關于從小就從父母嘴里聽到過很多西南聯(lián)大的故事,當她考入北大后,那些西南聯(lián)大的傳說與眼前的現(xiàn)實奇妙地結(jié)合了起來。這也是她畢業(yè)后致力于西南聯(lián)大研究的最大動力。從1999年至2009年,張曼菱畢十年之功,共計采訪聯(lián)大人物約200位。在所有采訪對象中,年紀最高的為任繼愈。
任繼愈在第一次接受張曼菱采訪時,就喜歡上了這個性格率真、學識淵博的才女作家。任繼愈說:“你的筆法有點兒野,我很喜歡。你就野下去,不要拘泥于條條框框。”任繼愈還對她說,“你以后到北京,就到家里來。”從此,張曼菱每次與任繼愈聊天,都無拘無束,備感輕松,而任繼愈也很樂意和她交流。
當年,抗戰(zhàn)開始后,北大先是南遷長沙,后又遷往昆明。從長沙到昆明,任繼愈與240多名師生選擇了徒步前往,稱為“湘黔滇旅行團”。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歷時兩個月。任繼愈向張曼菱解釋步行入滇的原委:“師生本可以全部采取借道國外、輾轉(zhuǎn)入滇的安全方式,但如果全體都從海外轉(zhuǎn)移,那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這個學校,從未淪陷的國土上走過去。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在步行入滇的途中,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志不窮,人窮志不窮,每一個人都不甘當亡國奴。正是通過步行,我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chǎn)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張曼菱感慨地說:“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于憂患的學人,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我發(fā)現(xiàn)選擇步行的聯(lián)大學子性格都比較剛烈。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的性格,也許這些人本就與眾不同。”在西南聯(lián)大,任繼愈前半段是學生,后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張曼菱攝制電視紀錄片《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從開始拍攝到央視播出,歷經(jīng)五年。其間不斷補充添加細節(jié),在有關任繼愈的內(nèi)容上,張曼菱又三次率攝制組采訪,任繼愈不厭其煩,從來沒有說過類似“為什么不準備周全了,一次問完”的話。張曼菱說:“其實,他是有理由這么說的。但任先生從來沒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當作是西南聯(lián)大的一磚一瓦,隨時可以添上。這部紀錄片制作完成后,任繼愈先睹為快,高度評價說:“集腋成裘,蔚成大觀。”
然而,這部紀錄片由于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突然遇阻。在一次應對“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會擴大會議上,任繼愈第一個發(fā)言說:“《啟示錄》是很有意義的好片子,應該大力宣揚。張曼菱是用西南聯(lián)大的精神制作這片子的。”此后,張曼菱回到昆明,過幾日給任繼愈打電話,任繼愈第一句話就迫不及待地問:“咱們的《啟示錄》怎么樣了?”任繼愈把這部作品稱作“咱們的”,讓張曼菱深感勉勵和溫暖。在諸多老校友的大力爭取下,《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最終成功播出,進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有一次,張曼菱去看望任繼愈,看到他喜歡喝綠茶,回到云南后,就買了一些給他寄了過去。但她沒有想到,等再見面時,任繼愈對她大發(fā)脾氣,批評她寄茶葉太多。張曼菱也很耿直倔強,回去就給任繼愈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表達不滿。但再見面時,任繼愈不但再也不提茶葉的事,反而對她更加熱情,從此再沒有對她發(fā)過脾氣。任繼愈還對張曼菱說:“我喜歡云南人耿直倔強的性格,這大概就是我們的‘民族脾氣。”
談到與任繼愈的多次交談,張曼菱說:“與任先生在一起,可縱情高談闊論。他從不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說大白話,就像《菜根譚》,用最淺顯的話。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任先生的‘內(nèi)養(yǎng)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張揚的語言,也從不給別人以緊張感,總是淡淡的,輕言細語,時夾以‘哎,表達一種會意。與任先生的情誼,令我想起那句古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后來,任繼愈的兒子任重對張曼菱說:“你每次來,他都特別高興。他喜歡跟你談話,你們倆的思想是一樣的。”
西南聯(lián)大建校七十周年紀念日前夕,張曼菱將新編的光盤合訂本《西南聯(lián)大人物訪談錄》面呈任繼愈。他約略一翻,說“等一下”,起身出了客廳,再回來,手中捧著東西。到桌上一展開,是“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兩枚校徽。顏色有別,分別為學生和教師所佩戴的。隨后,任繼愈將兩枚校徽再拿到手上,他拉起張曼菱的手,將校徽放到她手中說:“我昨晚知道你要來,專門找出來送給你。這兩件東西,送給你是最合適的,因為你有這個感情,你對西南聯(lián)大有貢獻。西南聯(lián)大只有八年,像我這樣上完了學,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這兩枚校徽也很難得了。一枚是我當學生佩戴過的,一枚是我留校任教佩戴過的。”這可是任繼愈珍藏了整整七十年的寶貴禮物。張曼菱感動地說:“給了徽章我就是您的弟子了。”任繼愈馬上接話道:“不僅是弟子,而且是入室弟子。”后來有朋友既羨慕又不無調(diào)侃道:“張曼菱,你也真夠貪心的,拿一個得了,還兩個都拿了!”張曼菱說:“老和尚把衣缽傳給小和尚,小和尚敢不接嗎?”其實,張曼菱直到現(xiàn)在還在自問:“大家都知道兩枚校徽代表的是任先生最珍愛的歲月,是任先生生命的一部分,我承受得起嗎?任先生的哲學門下自有高足,我只不過是一名跨界的‘晚弟子。”
2009年7月11日,任繼愈因病逝世,享年93歲。談到與任繼愈的“忘年神交”“情誼甚篤”,張曼菱將此稱之為“隔代親”。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