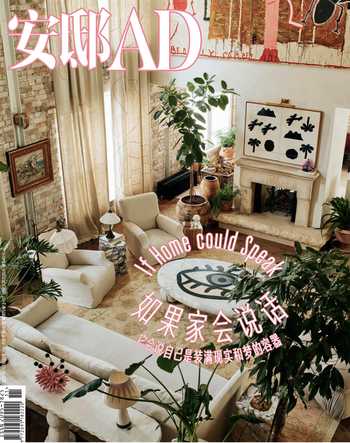太陽的軌跡
遠方





張永和說,建筑是一門“手藝”,它可以是感性的藝術的藝,也可以是嚴謹的匠藝的藝。“環宅”的建造亦是如此。改造后的四合院如院中的植物,在光的沐浴下與人共生。
“我老是想,要有機會建一座四合院,如何能建得比傳統四合院更‘四合院。”張永和對這種傳統的北京民居有著很深的眷戀,穿插在胡同里的四方天地容納了他對北京最深的記憶。八九年前,當他第一次來到這里時,四合院已經被推倒,只能依稀猜測到以前的模樣。被夷為平地的院子像一座被臨時清場的劇院,未來的空間一定充滿了不同可能的期許。他接下這座四合院的改造,心里已經開始想象這里接下來將發生的故事。
叩開斑駁的朱門,門廳的風雨廊上一道透徹的天光傾瀉而下,樹影映射在灰色磚墻上,像一幅靈動的水墨畫。走過一段低矮玄關走廊,隱隱瞥見遠處透著光亮的庭院。此時,一個家庭不同的生活場景沿著四合院的環形房間分布緩緩展開。張永和將建成后的這座四合院取名為“環宅”,皆因書房、客廳、餐廳、廚房等生活空間圍著院子按照一天的光照變化被串聯形成一個“回”字的環形布局,私密的臥室、衛生間等藏在環外。通透的落地玻璃門窗消解了東南西北的空間格局,也讓整個房間與庭院糅合在一起。“四合天地間,悠然成一統”的老北京四合院是一種傳統的“內向型空間”,“環宅”是與傳統建筑的對話,四方之氣盡歸四合院之中,賦予庭院作為整個“環宅”的靈魂地位。



“環宅”有著清晰且易于理解的秩序和邏輯,你在“環宅”中,能看到一天之中太陽隨時間位移的軌跡。通過玻璃門窗引光入室,讓光變得具體且觸手可及。在張永和眼中,東方和西方對空間的解讀有著截然不同的精神內涵與構成方式。西方建筑理念對“空間”的理解帶著具體“形”的定義與思維,這跟東方人的理解方式恰恰相反,“東方的空間在意的是‘空,而不是邊界。”這與中國人理想的世界有關,也解釋了四合院作為內向型空間的含義,及其能給人帶來的精神場域。張永和以“圍棋”為例來說明中國人對空間的認識:“下棋的時候,先占邊占角,在最中心的那個位置叫天元,實際上,天元是一種到了極致的點,而不是西方向外延伸的無限概念。”實體的形式悄然瓦解,變得不再重要。
他說自己小時候住在四合院,院子不大,樹長過屋頂,比房還高,自然的尺度超過建筑的尺度,這就是現實生活環境中自然與建筑的關系。天上飄著白云,地上有母親種植的草本茉莉,一到花季,院兒里有花香、大樹、蟬鳴等,接地氣,又接天氣。他說:“站在院子里,我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在這個世界的中心,腳踏一方地、頭頂一片天。”“環宅”的庭院也能滿足四合院這種特殊的屬性,張永和一開始似乎就已經想好了設計的方向。他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擴大庭院,將建筑推向邊緣。因為院子“足夠小”,構成了人和院子之間的親密尺度,也讓“環”的形態成為可能。“圍著院子轉一圈”的生活方式也產生于張永和想在傳統四合院的建筑形式中創置現代生活的舒適、便利。環繞一周,“環宅”每一個方位所面對的景致皆有不同,帶有一種電影畫面般的詩意。在意大利的維琴察,有一座安德烈亞 · 帕拉第奧設計的“圓廳別墅”,這是文藝復興時代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張永和說:“人一走進去,就有一種電影式的體驗,穿過一系列如取景框的房間,看見窗外不同的景色,完整走過一圈兒后再回到最開始的地方。”他將這種電影敘事的方式引入“環宅”的設計,只不過對于圓廳別墅是“向外看一圈”,而環宅是內向型的觀法,強化了中國空間的特有氣質。
光在“環宅”里變成了一種極為生動的元素,描繪了所有空間的故事性場景。走入以光為軸的時空概念里,空間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表情。張永和說:“光是所有建筑的一部分,尤其是純粹的天光,瞬間能改變人在空間里的感受。”也因此,“環宅”的核心正是空間圍繞著中心的院子按照太陽軌跡展開的生活長卷。對于張永和來說,“人圍著太陽轉”的生活方式充滿戲劇張力,隨著陽光在空間里的路徑進行生活布局,創造了一家五口在此居住的一種模式。早上,太陽剛剛升起,陽光灑在西廂的廚房,主人可以一邊做早餐,一邊與家人在陽光里開始新的一天。中午隨著太陽移動到北屋在躺椅上休憩,下午在東房的光影里寫字、畫畫,傍晚到南房用晚餐,如他所言,“建筑是一種邀請,也許他們會養成這樣一個習慣,但也不必是一件絕對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