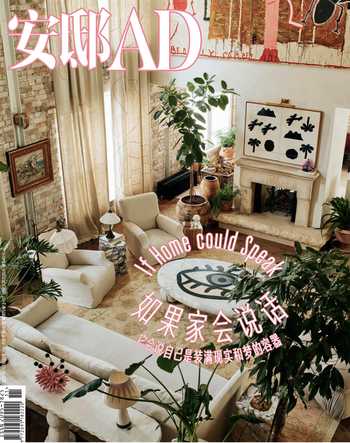清水園家書
雷壇壇



溫熱的漳州海灣,空氣中彌漫著咸絲絲的海的味道,整個小城浸潤在閩南語抑揚頓挫的語調中,仿佛千百年來一直如此平靜祥和。車剛駛進外院,我們就遠遠看見一位清瘦、精神矍鑠的老先生駐足門前笑眼相迎。進入被清水混凝土包裹的院子,在曲徑通幽處,一個既古典又現代的庭院豁然映入眼簾,霎時間,我們墜入一種親切又遙遠的時空錯覺里。
老先生帶我們進入茶室,嫻熟地泡上一壺新茶,汩汩作沸的水聲伴著幾聲清脆的鳥鳴,呷一口茶,仿佛才是一天真正的開始。老人一邊喝茶,一邊給我們講舊事。閩南人有著極強的家族信念,一直以來,父母兄弟皆住在傳統的閩南石厝里。一廳四間,左右為廚房,中間正面上兩級臺階為主廳,主廳兩邊拐進去為臥房。1996年,由于父母離世,老宅便被拆掉,重建為現在的多層小洋樓,大家依然住在一起,卻沒了舊時老宅里的舒展和自在,這成為老先生的心結。此去經年,他總會念起那一方天井里的世界,這五六層的洋樓終不如過去的舊宅老院聚氣。他和弟弟買下這片臨海的住宅用地后,一擱就是很多年。直到前幾年,他們篤定要再建一個像樣的院子,期望新建的宅子能夠成為承載家族記憶并延續下去的地方。


與建筑師牛津的相識讓這個家終于開啟又一次的“變遷”。牛津說:“我不希望只是建一座房子,而是想讓住在這里的所有家族成員,尤其是孩子,能從小感知建筑帶給人更廣闊的世界。”對于建筑師而言,一座房子所包含的藝術、文學、哲學,甚至其傳承的文化性遠比建筑本身更具生命力。他說:“建筑要退,隱藏于人和生活之后。所有的建筑和空間都應該由人的活動與生活習慣決定。”牛津和兩位老先生商榷之后,引入水系的中心庭院,這是閩南民居的自古實踐,也是存于東方人心里的山水詩意。薄薄的水面像一面鏡子,將庭院的四季流轉映照出來。沿著庭院,按照老房子的規劃,左側是餐廳,逢年過節,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會回來,老幼歡聚一堂,吃飯變成家族最有儀式感的事。像老房子主廳的茶室坐北朝南,面向水院,延伸至水系上與南側的多功能室隔水相望。平日人少時,他們把南側的多功能室當作日常的小餐廳,也在這里看書、下棋、練習書法、作畫等。兩位老先生的兒孫們大多工作、生活在廈門,周末驅車回來相聚是一家人最歡喜的時候。老人喜歡游泳,經常和孫子、外孫在地下室的泳池里比賽,泳池上方的水景天窗引入了充足的光線,讓這個藏于地下的泳池成了與庭院相對的另一番天地。


老先生說自己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每天清晨,背著手,在院子里一圈一圈悠哉地走”。周末一到,孩子們從廈門回來,這個四方的院子就成了小孩子瘋跑嬉戲的樂園。去年春節剛搬進來時,大家聚在一起吃火鍋,歸去來兮,似乎很久之前的那種生活又回來了。掛于屋檐上的風鈴與雨鏈連接著天與地,下面的老舊石桶都是平日里老先生的收藏。私密的臥室藏于水院茶室和多功能室的后端。穿梭在連接不同房間的走廊上,移步易景,中國人虛虛實實的詩情畫意便在一窗一景中慢慢浮現。說到此時,老先生拿起一把刻有“藏”字的紫砂老茶壺說:“這座房子跟我的性格很像,就像這上面的‘藏字,雖不顯山露水,但里面各有章法。”房子背靠一條主干道,后面是建設中的現代樓宇,對面穿過一排木麻黃,便是一望無垠的大海。整個院子置于鬧市,卻又以清水混凝土的堅硬質地塑造出一種邊界感,圍出一個“世外桃源”。牛津說:“這是一座幾乎沒有真正‘外立面的房子。整座建筑都退為‘背景,空間反而被凸顯出來。”然而整個空間里的設計顯得極為克制。負責室內空間的設計師黃振耀說:“家族的延續重在氣息,這種氣息的載體便是空間,居住在其中的那種東方傳統禮儀性的文化照應是一種能量,滲透在空間、建筑和每個人的血液里。”在家族觀念很強的閩南傳統里,一座好的房子不只是一代人住,很可能影響好幾代人。







老先生將房子取名為“清水園”,皆因房子用的都是自己經營多年的工廠生產的混凝土,同時也包含了一層清新淡雅生活態度的寄寓。建筑師還用松木模板澆筑,讓清水墻的木紋肌理更趨自然,也讓整座建筑瞬間變得溫和了,甚至有些毛竹模板的墻面在樹的剪影中像一幅自然的畫。當一切就緒后,房子的意趣便落在早年兄弟二人收羅的民國磚雕、舊船木和那些陶藝瓦罐等老物件上,這些附著時間痕跡的舊物就像好的藥引,與內院的黑松、茶室外角的水蒲桃樹、水院池岸邊的榆樹,茂盛的綠竹等開始發酵成東方味道。晚上老先生的家人帶我們站在華燈初上的小城高處,看著近在咫尺的漁船在燈火里靠岸,這種向晚不晚、最難將息的青灰色調好似讓人回到過去,也能穿越到未來。牛津說:“我經常會收到老先生的信息,給茶室更換了新鮮的插花;水院邊的石榴樹結了果;臥室旁栽種的風鈴木一夜之間開了花,姹紫嫣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