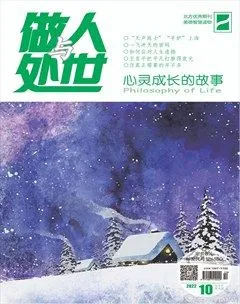再成長一次
陳丹蕊
待到成人萬事催,兒時回憶終難見
成長就像長風(fēng),年年吹過蘆葦叢,泛起陣陣葦浪。但成長卻絕不流于表象,你長了多高重了多少斤,并不能完全證明你成長了。成長應(yīng)該是一個人心智的成熟和精神的升華。人生要不斷成長,這樣生命才會長久。而讀書能讓一個人的心智更加飽滿,讓一個人的精神迅速成長。
看過畢淑敏寫的一篇文章,講述她各個年齡段讀《海的女兒》的不同體會。那時我懵懂地看完這篇文章,心中卻毫無觸動,我太小,看書總是囫圇吞棗。可是,那篇文章的結(jié)尾,我卻一直記著:“有時想,當(dāng)我58歲、68歲、108歲(但愿能夠)的時候,不知又讀出了怎樣的深長?”這句話在多年以后被想起,才知其余味悠長。那時我正第三遍讀那本小說,我靠在椅子上向窗外望去,仿佛看見高樓林立之外的山巒疊嶂迂回,那一刻,我仿佛聽見了群山的回響。
我知道,我開始有了與畢淑敏一樣的“深長”。那本我看了三遍的小說,就是塞林格寫的《麥田里的守望者》。
我第一次讀這本小說,是在小學(xué)六年級,讀高中的表哥不小心將它遺落在我家。那時我還沒有讀世界名著的經(jīng)歷,但想試一試。我打電話問表哥是否可以借我讀,他說:“送給你好了,可是現(xiàn)在你也讀不懂啊!”他的話激起了我非看不可的決心。可當(dāng)我讀完了第一章,都不知道作者到底在講什么。那本書對于當(dāng)時的我來說,用艱深晦澀這個詞都不足以形容。我狠下心斷斷續(xù)續(xù)讀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勉強(qiáng)看到最后一頁,而我看其他的童話和故事書,只一天的時間就夠了。你若問我當(dāng)時從書中讀到了什么,是有關(guān)夢想,有關(guān)人生,還是有關(guān)成長之類的,我只能說:“我多希望像考爾菲德那樣,可以離家出走自由地徜徉一番。”那時,十二三歲的我,固執(zhí)且天真地認(rèn)為像書中主人公那樣離家出走,就是成長的象征了。少年時,對很多小說的情節(jié)都是誤讀的,現(xiàn)在想來那就是所謂的不成熟帶來的后果。
我第二次讀它是在中考過后的一天。在等待成績時,心氣浮躁,隨手抄起它來讀。小學(xué)時讀過的情節(jié),我忘得干干凈凈。但重讀卻又不能讓我完全融入書里,總有記憶的碎片涌現(xiàn)腦海,我有一目十行的錯覺。讀著讀著我便睡著了。在夢里,我好像變成了那個主角,坐在空曠的麥田里看著小孩子嬉戲,一切都拉長成為寂然無聲的慢鏡頭。醒來后,我繼續(xù)讀剩下的,可腦海中只有幾個詞:粗俗、低級。因為整本書里主角罵了很多臟話,墮落地干了許多壞事。那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正義感,至少不說臟話就是一條標(biāo)準(zhǔn),雖然在現(xiàn)在的我看來依舊是淺薄的。讀完后,你若又像之前那樣問我感受,我會答:“要快樂,要向上,不能墮落。”那時我剛結(jié)束生命里重要的一個階段——中考,心心念念都是對未來的憧憬。
我第三次讀它是在不久前。高一下學(xué)期期中考試之后,我的排名不理想,心中難過無以寄托。心情沉悶中,我又想起了那本書,想到我和書里那個失敗的主角多像啊。我安靜地再次捧讀它,竟然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在看到考菲爾德說他的夢想的時候,當(dāng)看到他舍不得用他妹妹給他的錢的時候,我的心開始悸動,又隨著結(jié)尾那句“你千萬別跟任何人談任何事情,只要你一談起,就會思念起每一個人來”而釋懷。我終于明白,初中讀它時缺少的東西是什么了,是經(jīng)歷不夠,因此不能換位思考。考菲爾德一開始叛逆得無可救藥,卻在最后跨過了自己心里的門檻與關(guān)卡,便是一個值得欽佩的人。我由他想到自己,便覺得一切還不算太糟糕。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學(xué)會如何從書里獲得一絲人生感悟,這就是我人生閱歷的不斷豐富,讓閱讀也不斷進(jìn)步。
北島在《青燈》里說:“一個人行走的范圍,就是他的世界。”這種行走是一種精神的成長,是一種精神的行走。如果你這時問我從《麥田里的守望者》里讀到了什么,我會懷著敬畏之心回答:“人不會被任何事打敗。”成長的路上,我不執(zhí)著于希望成為一個做什么的人,而是“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
就像伍爾芙說的:“生命的內(nèi)核一片空蕩蕩,就像一間閣樓上的屋子。”但我們需要用成長與夢想填滿它,生命就會長久而豐滿。我很幸運(yùn),在我這短暫的青春生活中偶遇麥田中一個堅毅的身影;我很高興,我在最熾熱的夏天與這個人相識,炎炎烈日引燃了我的勇氣。夏天是畢業(yè)季,是分手季,可我還是愛夏天。當(dāng)我在夏天凝視夜空時,有流星劃過,我已許下愿望,給未來的時光埋下一顆種子。《左耳》中寫道:“愛對了是愛,愛錯了是青春。”就讓我在這為數(shù)不多、彌足珍貴的青春里,再成長一次吧。
(指導(dǎo)老師 李曉輝)
(責(zé)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