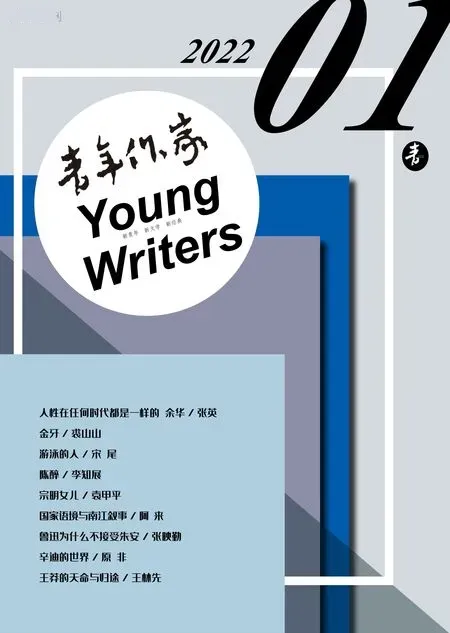這一夜
寇 揮
一
我這幾年常常到洪慶堡村去。這是由于我在西安地圖上發現了秦坑儒谷,就按圖索驥,當走到迷途時,就問當地的老百姓,大多數人不知道,但總有人知道,我就算交了好運。我穿過村子,終于在村外的田野里找到了。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以往的古河道,水枯了,開墾成了田地,種上了莊稼。我去的時候,那兒種植的是一片小麥。綠油油的麥苗在寒風里料峭。這兒實在沒有什么出奇的,要不是那通高高的造型還算講究的石碑,也就與其他地方的麥地沒有絲毫差別了。我站在前面,看著石碑上的文字。
秦嬴政坑儒遺址紀念碑文:
秦坑儒谷即今臨潼洪慶堡村南之鬼溝,西距西安城十五公里,北至縣城八公里,地處秦東陵西南緣。《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三十五年儒生議政有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位皆坑于咸陽。文獻通考又云其后秦始皇令儒生七百人集驪山腳下。漢人記其事云,秦始皇命人種瓜驪山谷湯溫處,冬于實,治儒生諸賢解辯至,則伏機弩射殺,后谷上填土,埋之歷久聲絕。唐顏師古于《詔定尚書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為秦坑儒處也。今洪慶秦屬咸陽內麗山市,人煙稠密,漢唐為新豐縣轄,以秦坑儒處建愍儒鄉,唐玄宗時建旌儒廟于此。命中書舍人賈至撰文勒石彰祭先賢。故又有旌儒鄉之稱。宋后廟毀碑亡。一九七零年于遺址發掘唐刻儒生像一尊,現存臨潼博物館。此地曾有馬王廟一座,毀于一九五八年。此物足證此即古之馬谷建于漢時之儒生塚,傳云諸生冤魂不散,天陰雨濕,鬼聲凄厲,村人稱之鬼溝。始皇暴虐,焚書坑儒,民不堪其苦,揭竿而起,二世而亡。先賢諸儒罹難,歷代悼祭不輟。居是鄉人追念仰止,繕其塚,重修旌儒廟。今勒石昭揭志其崇文仰賢之志也。是為記。
陜西教育學院圖書館館長 高云光 撰書秦始皇坑儒遺址紀念館籌建處 勒石富平縣石刻藝術館承制 田正新 鐫刻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仔細閱讀了碑文,我心里是有了些數。不管怎么說,我找到這個地方,還讀到了文字記載的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歷史事件,這件事就在我的心上重新刻了一刀。童年時光中就聽說的故事,今天好像終于落地了。我長出一口氣,久久地盯著石碑看,看了好久好久,黃昏時分,去村路的拐彎處趕公交車。后來我又去了多次。去時,我買了一瓶太白酒,把它打開,把酒全部灑到了石碑上。轉著圈兒灑的。最后把空酒瓶放到了碑前。碑座造型是贔屭,頭斷掉了,只留下脖頸。這叫我有不祥之感。有一次去時,天已經擦黑了,我走到一戶人家的門樓外,被一條大金毛狗撲上來咬,多虧我用手中的酒瓶抵擋,它才算沒有撲到我的身上。我想是被坑的賢儒們保佑了我。有一年春節期間,大年初一吧,我獨自去了這個地方。也是先用酒祭奠了,走到村邊與幾個曬太陽的村人交談。有一個聽說我拿得有酒,就想去撿回來,后悔把它祭灑到泥土里去了,想到以后就不要把酒倒掉了,祭奠后送給村人喝,也是積德之事。那村人說秦始皇裝扮成農民外出,夜住野店,出來小解時,與幾個讀書人望夜空。有個儒生說,啊,皇帝出宮了。秦始皇一聽就驚了,心想這些儒生這么大的本事,知道他不在咸陽宮里,若是刺殺他,那還了得,回去就下令坑儒。這是我在民間聽到的對于坑儒原因的解釋。這也符合秦始皇的性格,他要殺盡天下能人,留下愚笨的人,他便是天下最聰明的人了,這與他的愚民治國方略是密切相關的。弱民強君,首先削弱民眾的智慧,就從坑儒開始。掐指一算有七八年了,我有時候一年還去坑儒谷兩次,天冷時去一次,熱天去一次,有外地朋友來了也領他們去看看。其實嘛,就是一片田野,不遠處是荒山和村落,也沒有什么好看的。關鍵的意義就是那個石碑,標記了這個地方曾經經歷過秦朝的著名事件。有一次,我帶的白酒是瓶裝的“一斤多三兩”。這是我在村人開設的小賣部里買的。出城時由于行色匆匆,往往就忘記了這樣的事,等到快到目的地了,想起來了,就臨時找家商店。越是鄉村偏僻之地,十元左右一瓶的白酒越是不會缺少。“一斤多三兩”那牌子的酒若不是我臨時抓瞎,還真碰不到,也就不會知道它的存在。我想這一斤三兩白酒祭灑給那二千二百多年前的亡魂們,他們就能多聞到點兒酒香。我猛然想到,那是四百六十多位冤魂,那兒并不是一個人的墓地,我一瓶白酒能管什么用啊!表示意思罷了,有那個心就可以了。二千二百多年過去了,慘烈死去的儒生們還有我這樣一個人拎著酒瓶去祭奠,可見他們沒有白白被害,這件歷史大事依舊在影響著我的靈魂和心靈。
七八年了,八九年了,十年了,我就這樣一年年地前往洪慶堡坑儒谷祭奠亡靈們,每年去一到二次,挎包里都會背著一瓶白酒。廉價的、窮人常喝的白酒。那片田野里被我拋灑的白酒濡潤了,低檔的糧食酒滲入泥土,或者是食用酒精勾兌的白酒,不管怎么說吧,畢竟是白酒,高濃度的,50%之上的酒精度,酒液滲透到地下,透入亡魂們早已與泥土融入一體的骸壤中,骨頭化為骸壤,那么血肉化成的就是糜壤了,儒生們的亡魂如果還沒有飛散,他們就會感知我的心傷,我的只向內流淌的淚水和環流不已的血液。每次到了那兒,我看著遠處的山巒、近處的村落、那灰蒙蒙的谷野,我的心靈深處和靈魂的高空就會演奏出撫摸著還在流血的傷口的安慰。盡管疼痛再起,可內心卻得到了平復。
我站在石碑前,看著那業已漫漶的白色文字。實際上沒有過去多少年,石碑便已經殘破,赑屃頭也掉了,不知去向,時間和風雨的侵蝕無形而有力,難以阻擋。這又是一年的秋末,也是一天的黃昏,四野的暮色升起了,田野邊的房屋有了燈光,我并沒有想到去趕車。我坐在田坎上。我想那些居住在谷邊的農人,他們人老數輩,代代相傳,沒有人是不知道這兒曾經坑殺了許多許多人,他們與墳地相鄰,聽到過兩千兩百多年前的冤魂的哭訴沒有?心里恐懼過沒有?做的噩夢里有沒有成群成群的儒生?他們已經習慣了,從出生就在這里,一直到長大成人,從來都是把這里當做家的。在家里,還會有什么是可怕的呢?有父母親就有家,父母親過世了,他們早已成了下一代人的父母親,仍舊還是家,代代相因的家似乎是不會與墳墓掛上鉤的。我怕什么呢?
說到底,哪兒土地下會沒有曾經鮮活過的尸骨呢?只是由于年代久遠,骨肉和血液這樣易逝的物質化作了泥土,變形也變質了,也就變成了生命賴以生存的土壤。植物生長、結實、收獲,變成動物的營養,生命就這樣相互依存著,循環不息。有上十年了,每次來都是匆匆離去,把高度的白酒祭灑之后就算完成了任務,也就趕去乘車,只怕誤了點回不去了。今夜我豁出去,回不去就不回了,在這野外過一夜,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吧。我這樣想著,看著黑暗邊緣的燈光。天上的星星也出來了。人類發現了自然中的電流,創造了應用它的方法,電就變成了冬天的熱、黑夜里的光。有了電光,頭頂星空中的光就顯得弱了,常常被不用心的人忽視。這個世界人造的東西越來越多,自然便就被迫后退,越來越不“重要”了。這是人的錯覺。這樣的錯覺長期膨脹下去,人會被自然狠狠教訓的。我被村邊的燈光照耀,一時感覺不到真正的夜晚。燈光飄飛到秦坑儒谷的石碑上。我依舊坐在田坎上。關中大地沒有聽說有特別可怕的毒蛇,似乎不用擔心會被咬了腳跟。
我想公交車已經沒有了。當然擋個出租車也是可以回到城里的,可我確實不想那樣。這個夜晚我就在野外過吧。我鐵了心,也就沒有什么可以改變了。村邊房屋的燈終于熄滅了,田野也終究回歸到了原始自然狀態,真正的黑夜的黑暗淹沒了我。我的眼睛努力適應著,瞳孔變大,捕捉著暗色里的事物。我看見那通巨大的石碑旁的土地下面拱出來一個人。他好像是從地洞里爬出來似的,拍打了一下長袍上的泥土。其實并沒有一個什么洞,那土地完全彌合起來,土地沒有發生絲毫變化。緊接著,又有人從地下鉆了出來……有一大片我所目及之地全是從土里鉆出的頭顱,身子和腿腳也出來了。他們一大片又一大片地從泥土里鉆出來,全是穿的秦朝時儒生的衣裳,我猛然發現,坑儒谷的田地上站滿了,全是剛剛爬出來的儒生。我腦子清醒得很,心里想我這絕對不是做夢。
他們走到了我的跟前。
二
這確實不是幻夢。黃昏之后入夜沒有多久,或者是我感覺中沒有多長時間,村莊邊緣地帶的住戶燈都關了,人造的燈光終于給這天上的星光讓道了,他們從大地之下鉆了出來,仿佛粗壯的什么苗芽那樣破土而出,紛紛紜紜,但卻安安靜靜,沒有一點兒聲響。黑壓壓一大群,戰國終結后秦朝時典型的儒生賢士裝扮,給我特別深的印象的是他們的眼睛,星光一樣璀璨,寶石一樣晶瑩,恍惚間覺得繁星落地,遍地都是落星。他們不是隕星,不是石頭,不是鐵,是活的星星。
我坐在田坎上,雙腳似乎失去了行動的能力,宛若一尊石雕那樣沉重而凝滯。我的眼睛卻十分平靜,心里充滿了歡喜地看著他們。有一個儒生跨了一大步,走到我的跟前,伸出雙手。我連忙也把雙手伸出,想站起來,卻沒有能站起來。儒生抓住我的雙手,并沒有拉我起來,而是示意我繼續坐著。
“啊,不用站起來,不用……你今夜能留下來,已經感動了我們。”那儒生說。
我能聽懂他的話。雖然口音聽起來十分古老,字音卻很標準,咬字清晰,每一個字的意思都是不含糊的。我努力站起來。他們都站立著,我如何能獨自坐下呢?
“請拉我一把……拉……”我說。
那儒生臉上的疑色迅速消失,仍舊抓著我的雙手的他的雙手把我拉了一把,我便輕松地站起來了。
“也許是坐得久了,腿腳僵硬了,謝謝,謝謝。”
儒生仍舊抓住我的雙手不放。
“我們感謝您還來不及呢。你年年來看我們,給我們捎酒喝,這片大地下面全是酒香啊!酒香久久不會飄散,濃郁得我們的心靈長期停留在你留下的酒香之下,這片土地簡直被燒酒澆透了,濡潤至極。我們被坑殺后,漢朝時朝廷在這兒修建了旌儒廟紀念我們,唐朝時也有專門的建筑是為祭奠我們而建的,后來全毀于戰火,之后就再也沒有什么人來紀念我們了。你想想看,我們在地下是多么落寞,被人徹底遺忘了,我們被坑殺,血白流了,命白白喪了,一點也沒有起到警告后世的作用。這片大地荒廢了,又被農民開墾耕種長了莊稼。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您出現了。那天黃昏你出現時,我們還把你看作一般的獵奇者,那種遍天下的旅游人群,可你在第二年又出現了,后來年年來,再后來每半年就來一次,還給我們帶來了燒酒,有著濃郁酒香的燒酒,純粹的高粱制造的燒酒。于是,我們決定鉆出地面,要見一見你這位好人。”
另外一位儒生向我走了一步,他把手伸向我,我連忙騰出一只手來與他握一握。他臉上泛著紅光,一副沉醉的樣子。
“啊,喝了你的酒啊,上下通氣不咳嗽;喝了你的酒啊,地下日子不冷酷;喝了你的酒啊,爬出泥土走一走……”
這個時候,又有一位儒生跨上前來。
“不是酒的作用,而是你牽掛追念我們的心腸,你的千古熱腸喚醒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必須出來會一會你,也好了卻我們感激不盡的心情啊!”
儒生賢士紛紛與我交談,這個時間的場面具有了劃時代意義。我想到我來祭奠他們,給他們澆灑,竟然把他們激發活了,爬出了泥土,來到了人世,這個夜晚的場面真是我之外的人和我之前的歲月無法想象的。
我說:“我在還是小孩的時候聽到秦始皇坑殺了你們,還燒毀了世上的書籍,特別是他們活埋你們,我就恨透了那個家伙。”
有一個儒生插嘴道:“屁的秦始皇,屎皇,死皇,孽種,大私娃。”
那第一個走上前來與我握手的儒生說:
“不要罵人,這有失禮儀。”
那咒罵秦始皇的儒生說:“他還能叫做人?惡魔、畜生一個。”
三
聽到儒生們對于秦始皇的咒罵,我想到的是,兩千兩百多年了,他們對于秦始皇的罪行并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減輕仇恨。他們冤魂不散,依舊盤旋在這里,難道說是為了等候著一個什么契機?而我又為何經常來到這里呢?我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直到我近四十歲了才落腳于西安這座城市,才有了在這座城市生活的條件,這才有了可以常來這里的機會。我的常來常往,早就被他們所關注了,這么些年算是對我考察吧,這才終于爬出泥土與我相會了。我的內心深處醞釀完整一個計劃,就是在這個夜晚來臨之后,在冤魂們爬出地面之后才成形的。我打算率領這支隊伍翻過驪山山巒,前往秦始皇陵,把這座陵墓崩塌,使它陷落,并把秦始皇的尸骨扒出來,焚燒,銼骨揚灰,清算他的滔天罪惡。過去了的所有時間從來沒有懲罰他的罪惡,但今夜一定要叫他的罪惡得到清算。我必須做出一個榜樣來。
我說出了我的想法。儒生們——實際上是他們的亡魂——立即歡呼起來。他們說他們在這片泥土下面為何沒有流散開去,即使閻王強迫他們托生為新的生命,他們也是迅速使自己死掉,不是自殺,就是有意進入危險地帶,自尋死亡,死后又都來到了這里。有的人反復輪回出生了上百次,還是無法忘記被秦始皇坑殺的恥辱。他們倒不是為了個人的恩怨。他們說我的出現使他們終于看到了希望。
“這么說,我們去把秦始皇陵崩了、挖了、炸了,把他暴曬于日光之下,他的罪行得到懲處了,大家能像真正的人一樣活著,然后像真正的人一樣死去。”
“好啦,我們堅決跟你走!”
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夜晚是這樣開始的,似乎真正的時間開始了,世間有了意義。他們一身秦朝衣裳,我則是當代人的衣著。服裝的不同,好像專門為了表示身份的不同,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唯一的帶路人,或者說我是還活著的人,而他們早已死了兩千兩百多年了,他們全是被坑殺了的可憐的亡魂。
我們朝著驪山方向出發了。
四
這里還要做一點兒說明。我和儒生們是抬著那通巨大的石碑走的。既然他們全部跟著我走,那坑儒谷就不再是他們的墓地,再把那樣的石碑栽在那兒就顯得不合適了。那既然是追念他們的石碑,他們說不把它抬上一同上路便仿佛缺了魂兒似的。他們本身已經是鬼魂了,再失去了魂,就會化為烏有,就會無法聚合,就會與大氣混同起來了。我聽了他們的建議后,覺得很有道理。再說了,我們這支隊伍抬上這樣一通石碑走在路上,它就宛若是我們的旗幟那樣起到凝聚的作用。它一被我們抬上就成了我們的核心,我們的行動不但沉重,而且因為這樣的沉重而意義重大了。或者說這是一出戲的道具,貫穿始終的道具。
夜色里山巒朦朧的剪影似乎是涂畫在深藍的夜幕上的。有山也就意味著有溝壑,山越高大,溝壑也就越發深邃、越發險惡。
山路在山谷蜿蜒著。
我們是跨過田野而進入山谷的。田野里的莊稼早已被農人收獲入倉,田地里的根茬在腳下發出的聲響刺耳而令心臟疼痛。一進入山谷,夜色里,茂盛的黃蒿遮掩著小道。我擔心會有蛇蠱。儒生們倒不用恐懼人間的毒物。他們先是兩個一起抬著石碑,后來又三個一起抬著石碑,有時候又換成四人一起抬著石碑,不管怎么說,那石碑的重量對他們并不造成太大的負擔,他們數百人輪番替換,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其實那通石碑是用載重卡車從外縣運輸來的,又用起重機把它吊起來才栽到坑儒遺址上的。我是一個人,活著的人,我根本就搬不動它,哪兒還能把它抬起來,可這樣的活兒對于這群儒生來說卻是輕而易舉的事。我不明白他們是如何克服重力的。這難道是死后的奇妙之一?人死后還有多少奇妙之處我是無法想象的。
順著山谷側畔走了一程,來到一座村莊的入口。雖然夜色朦朧,視野不是太廣闊,我還是通過村口這樣一個窗戶一樣的通道,看到了那溝壑里面的村莊的基本全貌。路從田野里開始的時候是尖細的、長長的、蜿蜒著的,在山谷一邊更是若斷若續,脆若游絲,命懸一線,可它畢竟不是有機體的生命,便就有無數條的命,是打不死、斬不斷的。即使斷了、沒了,過了某片荒野,它又會出現。它本來是沒有的,有了蹄足的踩踏,踩踏得多了,它就從荒蕪中顯現了,它便也就誕生了。這就是它的命,它的本質。
村口是它膨脹的一個場。這個場繼續深入,又變細了,到了農家又膨脹成了院子。時斷時續,時大時小,時寬時窄,長卻是它的稟性——永遠不會終止。
有一個儒生問道:“非要進入這個村子嗎?”
我又觀察了一番說:“山谷兩邊都是山崖,穿過村子的路是我們最佳的選擇。”
我走在前面,帶領著后面這群抬著偌大石碑的儒生。有了狗的叫聲。那狗不知是在哪個農家吠叫,只感覺到全村子的狗都叫起來了,一大片的汪汪聲撞到我的身上又彌漫開去。它們是因為我而叫的。儒生們的腳步是不會發出聲響的。也許那通巨大的石碑動靜太大,是它驚動了犬們。
剛才在村子外面看它時,它顯得還亮晃晃的,可我們一旦進入村子的內部,那絲兒亮光就消失了,村子黑魆魆的,萬物的輪廓幾乎都是模糊的。這真是一個黑洞洞的村子哩。村民已經睡了,狗的叫聲也沒有使他們爬出被窩摸出院子警惕來者,村子依舊還是宛若一泓秋水那樣安靜。我想沒有必要驚動村民,我們的行動沒有打擾他們的美夢,這是我想要的結果。我并不想叫他們看見我帶了這么一大群儒生,而且還抬著一個巨大的石碑,那碑上還銘刻著一大篇文字,況且儒生們的衣裳裝束會把他們嚇壞的。他們衣服上的泥土還沒有拍打干凈,依舊傳遞著大地的聲音。
這個村落是建造在這條溝壑的兩邊山崖上的,一排一排的窯洞仿佛死后百年的骷髏上的眼窩,腐朽而無光,它再不會看到人世間的景象了。我們這支隊伍無聲地行進著。村路橫過溝壑,從右邊山坡轉到左邊山崖底下了。山崖底下并非溝壑的底下,路是開在半坡上的。一種震耳的聲響隆隆而來,撲面而去。我立刻就分辨出它是什么發出來的。
一盞如豆的亮光從一口窯洞里面射出來。那隆隆聲便是從那里面傳出來的。石磨轉動的聲響,上下兩扇石磨夾著谷物把它壓爛磨碎流出面粉來,那聲音其實是谷物的慘叫和哭泣。植物也是生命的一種,它在死的過程中也會發出撕心裂肺的聲音。奇怪的是,這孔窯洞只有一口小小的天窗,沒有門和門旁的大窗戶。怪不得亮光如豆呢。天窗很小很小。那是一口封死了的窯洞。石磨聲越發隆隆了,好像要把我的心磨碎了。我們這支隊伍本來是應該無聲地走過去的,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事,可我的心難受至極,一心想知道是什么人在里面推磨。儒生們也停下了腳步,把石碑立到路上。
五
那孔窯洞只有天窗,如豆的天窗發射出來的一星光,如同一盞燒著羊脂的油燈。我走到天窗的底下,漆黑的墻壁把推磨聲阻隔到了里面,若不是這樣,它的聲響將是非常之大的。這樣的夜晚,終究是什么人在里面推磨?這叫我這樣一個人好奇。儒生們也著急想探個究竟。他們一個一個疊羅漢,使站在最上面的人透過天窗往里面看。他一看就嚇得跳了下來。他對我說:“是個瞎子!”
瞎子在夜晚推磨?這似乎也沒有必要恐懼。可他卻嚇得夠嗆。第二個站在頂上的儒生看過后,也嚇得掉了下來。
“那是一個讀書人!”
第三個跳下來的儒生說:“他的眼睛是被剜掉的!”
我的心里便有了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一個被挖掉了雙眸的儒生在夜晚推磨。
“他像驢子一樣被綁到磨杠上!”
我說叫我上去看看。儒生們把我架到他們的肩膀上,奇怪的是,無論他們疊了多高,只要我上去,他們就會矮下大截來,不知是我的體重他們無法承受,還是其他的原因,總之是我夠不著天窗。有個儒生說把那通石碑蹲到墻壁下,于是他們就把它抬了過來。我爬到石碑的頂上,晃晃悠悠站在頂上,看到了窯洞里面的情景。
那人的背影我搭眼一看,心猛然一驚,仿佛看到了我自己的背影。待他推著磨轉到面對我的方向時,我更是驚心動魄了。這個人確實長著與我一模一樣的身體,若是我的眼睛是瞎的,我們就沒有絲毫差別了。看到他有著凄慘傷疤的空空眼窩,我的眼睛也疼痛起來。我從石碑頂上摔到了地上。眾儒生及時地攙扶住了我。我沒有倒下去。
我睜開眼睛看到了儒生們。他們人數如此之多,把山路兩邊的空地和窯洞前面的空地填滿了,我有一種身陷群眾海洋的感覺。我清醒過來,意識到這無門的窯洞里被關押的推磨書生就是我自己。
我說:“朋友們,把石碑抬起來,把這墻壁撞透!”
墻壁發出巨大的聲響,透了,穿了,緊接著整個兒塌了。我帶頭沖進去,沖到瞎眼書生跟前,把他身體上的轡頭縲紲解下來,把他從那踩得沉陷下去的磨道里拉出來,這個時候那一直轟隆轟隆的推磨聲沉寂了,夜晚變得特別寂靜。
那儒生說:“你們是誰?干嘛救我?”
我向他解說了一切。他說:“唉,我都是瞎子了,解救我還有啥用呢。”
我讓他與我走在一起,我們和儒生們重新踏上了去崩陵的山路。這個被我們救助的書生說他已經被關押在那窯洞里推磨推了上千年了,對于他說的上千年我不好理解。我們在暗夜里,在漆黑的山谷里那山路的微白的光芒下挺進著,這個時候,后面有大隊人馬追趕上來,迅速把我們包圍了。我一看,包圍我們的隊伍是大漠上的游牧族類,他們的馬群和大漠裝束過于醒目,非常特別,一眼就認出了他們的所屬。他們是元朝的軍隊。
六
這個大漠種屬對于儒生們來說是陌生的,可對于我這種當代人來說,我在歷史書籍和電視上的元朝歷史故事片中常常看到,雖然導演與演員對于元朝古人的模仿還是有差別的,但我一眼就能把他們分辨出來。這個溝壑里怎么會有元朝的軍隊呢?并且還有被他們關押著推磨不止的賢哲。
騎馬的軍士仿佛風暴一般把我和儒生們包圍到了漩渦的中心,馬匹和軍士的眼睛噴射出來的綠光把山谷照亮了,他們盤旋了一層又一層,溝壑里升騰起濃濁的塵土之霧。馬眼的綠光射過塵粒宛若陽光穿過窗戶,塵粒翻滾著、飛躍著,達到了它們夢想的自由。
有一個將軍飛奔向前,叫道:“你們是什么人?報上姓名來!”
一個儒生說:“我是秦朝的儒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叫盧天商。我們這群儒生是被秦始皇活埋了的,我們現在去崩他的陵墓,聽這位壯士說他的陵墓就在驪山的那邊。”
元朝將軍揮舞馬鞭掄向那說話的儒生,瞬間,那包圍了我們的元兵向我們舉起了屠刀,密集地向我們砍殺而來。我對這突然出現的元朝軍隊覺得奇怪,我還沒有向他們解釋,他們就下手了。我左擋右抵,帶領儒生們突圍了。儒生們抬著那通石碑,抵擋著元兵的刀劍。當那游牧族的刀劍砍刺到石碑上,鐵與石的碰撞爆出了耀眼的火花。當那屠刀砍到儒生們身上時,要么是他的手掉了,要么是他的腿斷了,人撲倒在地,嘩嘩地流淌出了如同巖漿般的鮮血。石碑又被其他儒生抬起來,跟著我繼續向村后的高坡上突圍。
元朝軍士掄圓的刀劍從來不向我的頭上砍,我無論走到哪里,他們便迅速散開,那簡直就是專門留給我們一個穿越的走廊,我們迅速到達了村莊背后的山坡。當我往溝壑下面俯瞰時,發現那兒什么也沒有了。混亂中,那個被我們救助的瞎眼書生沒有了蹤影。元朝軍隊可能把他搶回去了,重新關押起來,強迫他繼續推磨,做那沒完沒了的功。
當我清點人數時,少了三十個儒生。我還沒有記住他們的姓名,他們就犧牲到了元朝軍隊的戰刀之下。我想那失散了的三十個儒生就在方才戰斗過的戰場上,我建議大家回去把他們找回來,可儒生們覺得我的建議不可思議。他們的理由是如果回去還會遭到屠殺,就有更多的人流血丟命。我想到了自己,他們的刀劍也曾刺砍到我的胳膊上,我卻沒有找到絲毫傷痕,更沒有鮮血流出。我想到了我帶領的這群秦朝儒生,又想那元朝軍隊對于我來說也是早已作古的古人,心中駭然的同時也就默然了。
我說:“我們下去把他們的骸骨埋葬了吧。”
儒生們說要下去你就一個人下去。
我想到儒生們一下子就犧牲了三十位,他們內心的恐懼我是能夠體諒到的,我便獨自摸下坡去。
夜色濃了,深了,重了,我的眼睛開始看不清黑暗里的物體,緩緩地就什么都能看得清晰了。我走到那窯洞前,敞開的窯洞里什么也沒有了。坡上也沒有任何人的遺體。空空蕩蕩,一片寂靜,似乎根本就不曾發生過剛才那場戰斗。
那方才升揚起來的塵土沉落下去了,空氣清新了。我看到我的衣裳上落了一層塵土。我腳下踩著的地面發軟,塵土日積月累,很厚很厚。
七
我好像明白人死了沒有留下骨骸是怎么回事,又好像沒有明白。儒生們的骨骸畢竟經過了兩千兩百多年泥土和各種元素的腐蝕,早把它們化作土壤的一部分,哪兒還會有什么骷髏呢?可他們不是分明被元朝士兵屠殺了嗎?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看見了他們被砍開的傷口里流淌出了黏稠的鮮血,連那泥地上也涂滿了,而且還迅速凝固了,像一種雕塑一樣展現著立體的效果。我下來尋找它們時怎么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呢?
我回身爬上坡來。還剩下的儒生在等候著我。我面對這四百三十六位儒生,凝視著他們的面龐和軀體,感到他們無疑還是活生生的人。假如說被砍殺死的是鬼魂,那么它們就不會死,就不會掉隊,我的隊伍仍然還會是四百六十六人。不管我找沒找到合理的解釋,我們經過與元朝軍隊的一戰,損失的人員再也沒有回來。隊伍人員減少了,這是鐵打的事實。我心里感到悲傷。我把他們帶出了坑儒谷,卻不能保障他們生命的安全,這怎么能不叫我揪心呢!我望了望通上山頂的山坡和坡旁邊的溝壑,預感到這通往秦陵的路上一定布滿了危險,我還得多加小心。
儒生們對于他們的減員表現出的是漠不關心,宛若從來就沒有那么回事一樣。這當然對我來說是好的現象,我不用擔心他們會半途而廢。我們出發了。
夜色中的驪山山頂與深藍的星空抵觸到了一起,山比天高,天比山低,但天卻永遠在山的頭上,這不知是什么樣的錯覺?分明知道天在山頂之上,怎么還會感覺到山比天高呢?感覺這種東西只能由感覺來解釋,文字是沒有能力表述它的。
其實,驪山并不是一坡到頂的,它在不斷地上升中起伏、跌落,又起伏……這樣逐漸地緩緩地攀升到與天平的天際。我們爬上了一面坡后,發現一大片洋洋的水。說它是汪洋有些夸張,說它是一大片水比較符合我的感受。這高坡上的一大片水,無疑是被堤壩堵截的結果,它有著一個死板的名字:水庫。把水保存在堵截起來的溝壑里,這就好像為水建造了一個庫房,把水存放起來了。這樣一個名字實在缺乏詩意,更沒有一點想象力。但它卻很實用,天旱時用來抗旱,澆灌干旱的莊稼,糧食產量會保持風調雨順時的水準。
我沒有料到水庫里面的堤坡上坐著一位老人。他的腳下便是水平線。水庫的水儲量達到了最高水平。夜色里,水庫的水平鋪展向溝壑的深處。由于水平線很高,溝壑基本被水淹沒了,只顯示出它的寬闊,而它的深是看不出來的。那水寬闊地洋洋灑灑地伸延到溝壑的里頭去了,那兒顯得深邃而神秘。忽然間,有千帆從那兒涌出,船舶一涌出來就在廣闊的水面上朝堤壩這兒風馳電掣,眨眼工夫,匯集到了那老頭兒腳下的水域里。這時,那老頭兒才轉身面向我們。我一眼看去,心涼了半截。這個老頭我認識!儒生們的眼睛宛若星空繁星,平靜而晶瑩,沒有絲毫驚異與慌亂。
這個老頭兒是大明皇帝朱元璋。
帆船上的士兵表情嚴肅,氣象肅殺,嚴陣以待,隨時出擊的態勢令目睹者提心吊膽。
朱元璋說道:
“我在這兒已經等待你們多時了。歡迎大家來到大明國。”
這樣一個水庫——我在它的壩坡上看到了“勝利水庫”四個仿宋體大字。這無疑是一座當代修建的水庫,如何成了大明皇帝的內湖和水軍基地,這實在是個無底之謎。朱元璋的下巴很長很長,向前伸著翹著,仿佛一個巨大的鐵勺,而那嘴巴正好可以盛大量大量的食物,我想這是個貪吃的皇帝。他的嘴與一種家畜的嘴是非常相像的。我沒有料到他帶領著他的龐大水軍會在勝利水庫等候著我們。
我說:“陛下,我帶領他們翻過驪山去是為他們報仇的。”
朱元璋說:“既然來到了我的大明,就得留下來為我們大明服務。這些儒生個個滿腹經綸,大明正是用得著他的時候。開國不久,百廢待舉,人才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叫大家上船!”
水庫兩邊是青黛色的山巒,嵯峨峭拔,崚嶒崔嵬,那起伏騰躍的形狀猶如虎蛇,氣象森嚴詭秘,暗含危機。溝壑中的路被漲起來的大水淹沒了,若想進山,只有乘船這樣一條進路。不管他是朱元璋,還是牛元璋,借用一下他的船舶并不是什么壞事。
我大聲說道:“好吧,咱們就上大明國的船吧。”
儒生們紛紛上船。船只很多,大家分散開來,其實四百三十位儒生,也就分別乘坐了十幾艘船只。朱元璋叫我與他上了一艘大船。那通石碑被幾位儒生抬著上了一艘相對大些的船。我沒有想到這座勝利水庫會有如此廣闊的水域,它開闊處延續了幾公里,山谷蜿蜒處伸向更深的山谷。強勁的大風吹著大帆,船舶行駛速度很快。眨眼工夫就到了一處港灣。勝利水庫感覺有了大海的規模。船舶進港停泊,兵士們把儒生們領上了岸。朱元璋與我同時下船登岸。岸邊一個偌大的坪地,坪場的北邊是高聳入云的宮殿。宮殿前面的彩色屏風上寫的是考狀元的試題。我心里深感詫異。朱元璋站在屏風前對我率領的四百三十位儒生說:
“考試是不能免的,大家都是才高八斗的儒生,秦始皇活埋了你們,可我大明國是愛惜人才的,只要大家答對了這屏風上的試題,我立即封官加爵,大明需要你們這樣的棟梁之材。我內心高興啊,正在我如饑似渴盼望人才之際,一下子來了這么多戰國時代培養出來的儒生賢哲,我的大明國真是幸運!”
我心里產生的是哭笑不得的想法,儒生們就這么要到大明國當官去了,他們曾經被活埋的屈辱也就隨風而去了嗎?我與他們所計劃的崩陵便也中止了?儒生紛紛坐到坪地上早就安排的桌椅上,攤開紙筆,工工整整地答題。那毛筆所寫的字是隸書體,十分圓潤漂亮。我有了一種嚴重的失落感,讀書人原來是這么容易滿足的,只要給他們官做,給他們衙門坐,有俸祿掙,他們便就放棄所有的理想。可他們畢竟不是一般的儒生,他們是從春秋戰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來的,飽受那個時代的爭鳴氛圍的滋養和浸潤,他們不會為了一碗飯吃就給大明國賣命的。試卷收上來了,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一一審視著,滿意地贊嘆著,嘴中念念有詞。忽然間,他嗯了一聲,又重新嗯了一大聲,然后他——
“這還了得!反了!賤坯!狗賊!竟然敢罵我歹朱,統統把他們抓起來凌遲!千刀萬剮!”
這真是一個瘋子!前一分鐘還喜笑顏開,下一分鐘就因為一個奇怪的用詞而大開殺戒。我看到他食指所指的一個字:殊。他把它分開來看便是“歹朱”了。
士兵們蜂擁過來,把儒生們包圍到坪地中心。
我大喊道:“朱重八,你不能因為一個字就殺這數百個頂尖級的人才吧!”
朱元璋命令道:“先把這個帶頭的壞蛋斬首!”
我縱身一跳,到了我們從坑儒谷一路抬上山來的那通石碑上。
“大家把石碑抬起來!”我大聲喊道。
儒生們盡管被包圍了,可他們并不恐懼,似乎連緊張的表情都不曾有。他們抬起了石碑,我坐在上面,指揮他們突圍。隨后,我站在石碑上。儒生把石碑高高地抬起來,我又站在制高點上,看到大明士兵揮舞著刀劍,砍殺著儒生。有的儒生被砍成了兩半,斷裂開的肢體還繼續跳躍著、奔跑著,很快就散落到荒地里去了。抬著大石碑的儒生在我的指揮下,沖開了一條血路。大明皇帝朱元璋試圖來阻擋我們,那石碑只把他輕輕一撞,他就一下子飛到勝利水庫的大水里去了。凡是撞上我們石碑的兵士沒有一個不即刻散裂,撲倒而化為齏粉。我們沖進了那巍峨的宮殿。因為沒有路可走。坪地其他方向全是陡峭的山崖和浩茫的深水。宮殿里擠滿了大明軍隊,可我們的石碑一路撞去,血肉橫飛,宮墻坍塌,開出了一條轟轟烈烈的通道,直穿過宮殿的后墻,我們爬上了更高的山崖……
八
當我們回首觀看時,下面除了勝利水庫的堤壩和蓄水外,山河隱現在夜色里,帆船和大明朝的軍隊與皇帝都沒有了涓埃的蹤影。假如說他們是幻覺的話,那么那堤壩里面的坪場上橫躺著的儒生們的遺體,那被砍殺的軀體斷的斷、裂的裂,失去了手和腳的,上半身與下半身斷離的,那流淌出來的血跡居然還宛若烈火一樣發光,把其自身的情景照耀得一清二楚。經過點數,這一次與朱元璋的遭遇,儒生們又死去了三十位,現在只剩下四百零六位了。這個夜晚,自從離開坑儒谷的田野,爬上驪山坡來,二次劫難,損失了六十名儒生,這樣的遭遇如果持續下去,將來還會有什么樣的可怕死難呢?
我汲取上次教訓,沒有拋離隊伍獨自下到水庫岸邊去埋葬那倒斃的儒生,可我也沒有馬上就通知儒生們開拔。我們站在勝利水庫左邊的高坡上,凝望著下方,以這樣的方式表達著我們的哀痛。忽然間,那水邊坪場地面開裂,那三十具尸體沉陷下去,泥土彌合,坪場恢復了原貌。
那正是我想象中自己想去做的事情,由這個夜里的不知的神秘力量完成了,這也算是對于我的心靈的至高安慰了。儒生們的眼睛里蓄滿淚珠,他們跟我一樣十分感動,那淚珠兒發出很大的聲響,滴答滴答掉到了山石上。
我們是慌不擇路而奔襲到這兒的。這是一片荒野。說它沒有路嘛,但荊棘灌木野草之間還是有縫隙可插足的,與其說那是荒野,還不如說它是路的原初概貌。路其實就是這樣開始的,從野獸的痕跡到人踩的長條狀。儒生們抬著石碑,我們就在這樣的荒山上爬行。說是爬行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只是把腰胯彎得更狠了些,宛若蜷縮著的爬行動物。
我的褲腿被長倒刺的植物枝條勾掛住了,我一用力,它就撕扯開來,那一聲斷裂聲十分刺耳。這兒的山坡上盡是荊棘。茂盛的酸棗樹布滿了荒坡。我身邊抬著那通石碑的儒生們對于酸棗樹上的倒鉤沒有反應,他們依舊行走如風。我看到夜色里,他們的長袍在荊棘上滑過,卻沒有一個被倒鉤掛住的。我想起曾經聽母親說過的一個傳說。母親是位不擅長言說的婦人,一生中與生人很少說話,但她對孩子們卻是說話如唱,她說“早已”——這是過去的意思,古代的意思——有個皇帝被攆得到處逃命,有一天他逃到了山上,衣服被酸棗刺倒鉤掛住了,他順手把那枝條上的倒鉤用手一捋,咒道:將來你永遠也不會長倒鉤刺!于是,那地方的酸棗樹就再也不長倒鉤刺了。這樣的傳說由我母親的口中說出,又是在童年的金色光芒里,它就特別亮麗。我不是逃亡的皇帝,無權說出那樣的咒語;儒生們的衣裳對于酸棗倒鉤如同虛空,那么他們是生存在那傳說中的皇帝說出那樣咒語的空間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是被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坑殺的,無法生存在第二第三個皇帝的世界里。他們是逝去的河流,新的水珠充滿了河床。
在這蒼茫的夜色里,驪山山巒在升上星空的同時,往遙遠的空間推進,它變得無限高和無限廣大了,我們翻越驪山的計劃和行動在這樣的擴展中使我的內心產生了畏懼心理。計劃還能完成嗎?這夜里的山脈不會成為我們的命運吧?這樣的翻越行動假如凝固成了永遠的山景,我們也就會成為這山野里的雕塑,雖說也不失為一種風景,為造訪者的眼淚落實了場所,可我們的愿望也就永遠地死去了,永遠駐足在了山路上。
好在我們在荊棘叢里走了沒有多久,就有一條小路的尾巴梢兒呈現在漆黑的夜色里,它發出的白色光芒把我們的目光引上了山頂。
九
爬過大山的人都有一種經驗,他們不會把眼前望見的山頭當作最終的山巔。可我們所爬的這座驪山,它畢竟不是那種特別高峻的山脈,它的高度是有限的。我們爬上山巔后,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這是說我們面前擺著的是下山的路了。下了山,越過田野,就會達到秦陵。由于距離還遠,夜色正濃,我們還一眼望不到山下去。我們把石碑放在山巔,大家圍繞著它,稍事休息。這個時候,就在山巔上,泥土和草木中憑空升起了一座龐大的宮殿。這座宮殿把我們圈到了它的勢力范圍之內,我們身陷宮殿的中心。我在博物館專門去看過秦咸陽宮的模型圖,把山尖削平挖低,把宮殿建筑在山頂上,拉薩的布達拉宮也是那樣建筑的。現在這座凌空升起的宮殿矗立在驪山的山巔之上,把荒草野木覆蓋在宮殿之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全是皇家的輝煌璀璨與壯麗。宮殿的中心十分寬大,仿佛我童年時山村里的打麥場,圓形的,周圍是還沒有收割的金黃的麥子。打麥場的中心放著一張巨大的桌子。桌子是長方形的,桌面很大,上面擺滿了線裝書籍。這樣的場面宛若專門為了迎接儒生們而擺設的。四百零六位儒生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紙質的線裝書籍,他們紛紛把它們拿到手里,驚叫道:
“這上面有字!”
“這是什么?”
我說:“這是書。”
“什么?是書?”
我腦子稍微一轉就明白了儒生們驚訝的原因。
“賢士們,你們在世時,書是用竹木等做成的竹簡、木簡,只有王公大臣會在絲綢上書寫文字,現在這紙書就仿佛是用絲綢做成的書。”
儒生們興奮地閱讀著。
有個儒生問道:“這樣的文章我以前可沒有讀過,這是哪個圣哲寫的?”
這個時候,從宮殿的長廊里走來一大群人。我一看就認出那走在核心位置上的是年號乾隆名叫愛新覺羅·弘歷的大清國皇帝。圍繞著他的一大群人里有一半是女性,都很年輕,個個面容如花似玉,更像剛剛冒紅的朝陽。那些男性大臣形容猥瑣,眼神如賊。弘歷大步走到書案前,往龍椅上一坐,哈哈哈地大笑起來。
儒生們有的還沉醉在書里,聽到大笑聲這才把埋在書里的頭顱抬起來,看到了弘歷和他的大臣與女伴們。
弘歷說道:“歡迎你們來到大清國!我早就得到信息說你們要來,就在山頂上建造了一座宮殿,專門迎接你們。這書案上收集了大量的書籍,治國方面的,詩詞方面的,應有盡有。你們是秦始皇時代的儒生,能為我們大清國所用,那就是大清國的幸運。”
我心里想他是怎么得到通知的,提前就在半道上攔截我們了,要是能把這群儒生收羅為大清國所用,對于大清國這個從邊地入主中原的荒蠻政權來說真是久旱逢甘雨。我把他們帶領出來絕不是為你大清國添磚加瓦的。此時,一股野風從宮殿外面強勁地刮了進來,把書籍吹得四處飄飛,紛紛掉落到了地面上,滾動著。儒生們手中的書籍也被吹落了,他們追趕著書籍,卻一本也沒有攆上。忽然間,滿書案的書籍一本也不見了。儒生們的面容上浮現出了全是悔恨的表情,長長地嘆息著。
弘歷凝視著儒生們,沉默著。
我順口說道:“清風不識字,何故劫詩書?奪朱非正色,蠻蠻也稱帝。”
愛新覺羅·弘歷拍案而起,大叫道:“殺!殺!殺!把這幫書賊全部斬殺!”
那些年輕貌美的女性忽然間脫掉她們身上的旗袍,赤裸著軀體,手里揮舞著青銅寶劍,向儒生們砍殺過來。她們仿佛是聯合收割機收割莊稼一樣,與她們遭遇的儒生應聲倒地,他們的腿齊刷刷地斷了,宛若真的瞬間變成了莊稼。當那些女兵向我們的石碑發起進攻時,她們的刀劍崩裂斷成了兩截,她們同時被巨大反彈力震得倒下,大口大口地喘氣,迅速失去了性命。這個時候,從宮殿深處涌出來大批八旗兵,把我們包圍到中心。我指揮著抬著石碑的儒生向宮殿后墻突圍。凡是撞上石碑的清兵沒有一個不倒地斃命的。我們用石碑把宮殿的后墻撞開了一個口子,大家山洪一樣涌泄而出。八旗兵剛從破洞里竄出,就像跳進鏹水里一樣,軀體火速熔化了,他們在極度的痛苦中慘叫著,熔化成了一攤黑水,黑水與黑夜融合,不見了。
后面的清兵看到這樣的情景都驚慌地退步。弘歷摸索著豁口,看了一眼外面的山野,說道:“這是哪兒?”隨后,他給破洞上掛了一個簾子,把它遮住了。那宮殿似乎便與我們所在的山野隔絕開了。
十
這兒無疑還是驪山,是它的北坡了。山巔上憑空出現的大清國宮殿跟勝利水庫里朱元璋的帆船水軍——這樣的噩夢消失了,可我清點人數后,還是出了一身的汗。有一百位儒生被弘歷斬殺了,我們現在的人數是三百零六,加上我便是三百零七。一百位賢哲被大清國滅了,他們的尸首留在了那些女兵的屠刀下,這使我的心寒了大半。前途不知還有什么樣的兇險,這樣下去,我們的崩陵大計還能否實現,這可能會成為一個未知數了。不管怎么說,總算翻過了驪山山巔,從東南坡到了西北坡,溪水便也朝北流了。溪流越過平原,最終會匯入更北邊的渭水,渭水向東匯入黃河,黃河向東匯入東海……這些地理知識我是知道的。儒生們抬著他們墳墓上的石碑,行走在下山的路上。盡管是下山的路,我們是在高處,但北邊的山并不是一坡到底的,它還有很多聳立的山頭,一個一個排列下去,山谷也是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的,是在多端的變化中逐漸落下去的。前面的視野還是山巒和山谷。我們抬著石碑一會兒走在山谷里,一會兒走在兩個山頭之間平滑的凹窩里,一會兒又要爬上一個小山頭,又從那上頭下來,往更低處的山谷走去。走著走著,我們前面的路上有了情況。這是夜晚嘛,天上沒有月亮,但空氣是透明的,視野也算開闊。那山路上坐著一個老婦人。她是背對我們這個方向的。其實她的軀體朝著我們所在的山上的方向,只是她把脖頸和頭扭到下山的方向去了。我們繼續走著,她把她的身體和脖頸擺正了。這個婦人,她的臉很大,富態,威嚴,高貴,一身的驕氣。我一看就認出了她是誰。她是慈禧太后。她怎么會獨自待在這兒?
她站了起來。她的身材高大,異族的狂野與開放似乎能從她的軀體上得到解釋。她攔住了我們。我走到她跟前,說道:
“慈禧太后,你這是西狩至此?”
她把我瞪著看了一會兒,臉上有了笑容。
“我知道你領了這支隊伍會從這兒過,專誠等候著。大清國的官員腐爛了,我需要新鮮的血液替換。”
“你不是帶著愛新覺羅·載湉一起西狩的嗎?”
她的眼神里閃出一束光來,并沒有轉動脖頸和頭顱,就命令道:“你還不出來!”
我正在納悶之際,山路上出現了一個年輕人。這個人是光緒帝,他臉上的表情是無動于衷的,宛若死去的人。他的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但他卻像是世紀老人,暮氣沉沉,垂垂老矣,奄奄一息。
偌大的空曠的山坡上就這兩個西狩的人,他們帶領的隊伍呢?我向儒生們介紹了光緒與慈禧,并把大清國的情況總結了一番,還有多國聯軍攻入大清的心臟的狀況。
慈禧太后說:“你們是跟著我走,還是跟這個年輕人走?”
儒生們對于光緒的新政抱有同情,明確表示跟著光緒走。慈禧太后立即翻臉,叫囂道:“你們這群死鬼,難怪會被活埋哩!把他們全部殺掉!”
老婦人的喊叫并沒有引來大清的兵勇,甚至連一個太監也沒有出現。她站在山路上,在夜色里顯得異常孤獨。我想這是一個歷史的機會,抓住時機,迅速利用。我叫儒生們放下石碑,捕捉住了葉赫那拉氏。儒生們用秦朝時的繩索把葉赫那拉氏捆綁到了那巨大的石碑上。我對光緒帝說:“我們抓住了這老妖婆,你可以實施你的新政了。”光緒帝臉色大變,他病弱的軀體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立即精神煥發,一臉的殺氣。
他高叫道:“你們這群儒生竟然捆綁了太后,這可是滅門的不赦大罪。兵勇們,把這幫暴徒全部斬首!”
我想這個年輕的大清皇帝真是瘋了,他的大腦早已混亂了,他長期在慈禧太后的重壓下變形了、變質了,翻轉成了他的對立面。我還在思索著,泥土下面鉆出來無數兵勇,他們全副武裝,沖向儒生們,揮舞著長矛和刀劍,一陣血肉與鋼鐵的撞擊和摩擦響徹了山野,擊穿了星空。混亂之中,我與還幸存的儒生們抬起石碑,向山下沖去。清兵的武器擊打到石碑上,冒出火星的同時,刀劍斷裂,清軍兵勇倒地,瞬間化為泥土,消失了。
十一
清點隊伍發現這一次損失了五十名儒生。光緒帝為了他的養母,殺掉了我們五十名儒生,這樣的罪惡也是滔天的。我意識到皇帝的本質無論是在什么情況下都是不可能改變的,他可接受太后太皇的虐殺,但卻絕對不能接受平民儒生對于太后太皇的處罰。平民對于皇族的僭越便是死罪一條。儒生隊伍只剩下二百五十六人了。這個夜晚還長著哩,就有幾乎一半儒生被殺戮,他們遺尸驪山,鮮血與骨肉散落在山野上,他們的第二次劫難竟然如此慘烈,而且是在我帶領他們走出坑儒谷的前提下。下山的路蜿蜒曲折,山頭與山谷九曲回環,遠古的造山運動沒有忘了自身的藝術追求。走了一會兒,我們這支隊伍走進了一場大戰。我們被裹了進去,身不由己,結果又有五十名儒生被殺。戰爭結束后,我們剩下的二百零六人,加上我是二百零七人,繼續下山。我們走進了一個村子。驪山山脈相當廣袤,在它的夾縫和皺褶里深藏著很多很多村莊,最有名的應該是那烽火臺村了。周幽王與褒姒的傳說綿延了數千年,還在繼續傳播著。還有一個傳說是周文王的媽有四個奶。確實想象力不凡。村子里正在舉行大會,讓一個人站在高臺上,前面的麥場上坐著的人密密麻麻,不時有人跳上高臺對那站在上面的拳打腳踢一頓。這是一種儀式。儒生們哪兒見過這樣的場面,他們蜂擁而上幫助那個被毆打的人,抵抗行兇的群眾,結果是出現了一支上百人的民兵,他們手持農具,直接殺向儒生。這一場混戰下來,儒生損失了一百人。村子簡直是瘋了,我們仿佛變成了糟蹋莊稼的害蟲。依舊是那通石碑挽救了我們,有它在,我們就能撞出一條活路。二百零七個人的隊伍大量減員,剩下了一百零七人。緊接著我們闖進一座農場。農場里全是讀書人。他們不是工人,更不是農民。那兒的狗的眼睛火紅火紅,見到活人也不會逃跑。我沒有料到我把儒生們帶進了這樣一個地方。進去容易出來難。高高的圍墻上架著電網,年輕人在站崗,氣象森嚴。儒生們被勒令像那些早到者一樣勞動。勞動強度難以想象,儒生們很快就汗流浹背,渾身濕透,接著有人就昏倒了。我帶領他們抬著石碑越獄,撞塌了農場的厚墻,逃到了山下的小溪邊。我大眼一過,心中駭然:儒生們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十幾個人了。我們從河溝里爬出來,進入另外一個山村。驪山山川深邃廣闊,山勢地形千變萬化,自從褒姒名揚四海,名人輩出,楊玉環李隆基,一曲長恨歌似乎還在天地間旋繞,至今沒有落地。這個村子的村道上趴著一片片餓殍,與我一起抬著石碑的儒生也陷進了饑餓之中。當我拖著石碑爬出村子時,一個活的儒生都沒有了,他們全部喪生在中途。我拖著石碑蹣跚經過平原,到了秦陵下。我也不知道我為何有了拖動石碑的力量。我看著它高聳入云的陵頂,對于自身的孤零和渺小,狂笑起來。笑聲中,那高大的陵墓猛然倒塌,陷進了大地的深處。如同夢境,我把坑儒石碑豎立到塌陷的陵頂上。它站直了,穩穩當當地扎根在了陵頂。它與大地是在同一水平線上。東方冒紅了,新一天的朝陽爬出了地平線。這一夜宣告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