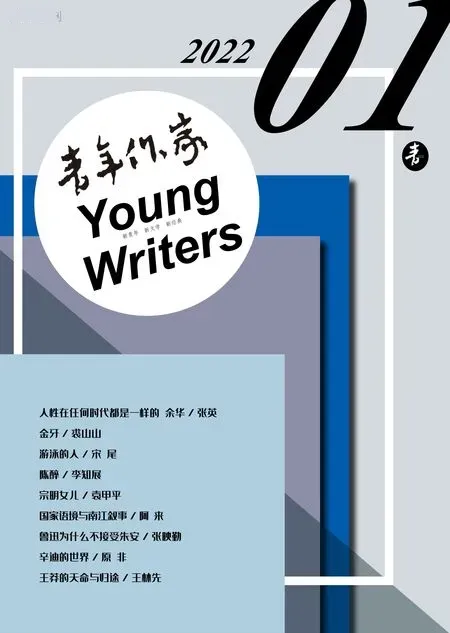飛蛾之死
楊 道
星期三是藍(lán)蛾最喜歡的日子。她選擇在這一天的凌晨三點(diǎn)從31 層高的樓頂跳下,是經(jīng)過(guò)近半年的精心設(shè)計(jì)和計(jì)算的。落地的點(diǎn)她早已選好,樓下圓形花壇里的花一直開(kāi)得甚艷,姹紫嫣紅的,茉莉、七彩鐵、千里香、月季……她喜歡花,她希望她的身體被花托著進(jìn)入天堂。
這個(gè)城市的凌晨三點(diǎn),霧氣在半空懸著,藍(lán)蛾的身體以飛蛾撲火的姿勢(shì)匍匐在樓下花壇的中央,臉埋在一叢黃玫瑰中,仿佛她耗盡了半生活著的福氣,終于捕到了那一點(diǎn)火光。
她的追思會(huì),她的家人選在四月的第一個(gè)星期三舉行。從殯儀館的入口就鋪展著白色的菊花,來(lái)的人垂著頭,合著手,手里握一支白菊。四月的早晨,有一些微涼的風(fēng),像飛蛾扇動(dòng)翅膀的褶子。來(lái)的人隨著褶子的皺依序進(jìn)入館內(nèi)。藍(lán)蛾像一個(gè)天使,靜靜地在橢圓形的花叢中躺著。這橢圓形花叢,類(lèi)似于小說(shuō)里美滿(mǎn)的墳?zāi)梗I(xiàn)花的人從門(mén)口進(jìn)來(lái),繞著藍(lán)蛾一圈,把手里的花插在離藍(lán)蛾最理想的一個(gè)位置,仿佛就表達(dá)了最美滿(mǎn)的悲哀。她的朋友做著哀痛的陳述:
“……藍(lán)蛾是一個(gè)稀有的美好的女孩子……她在美麗的潯陽(yáng)出生,她有著和陶淵明一樣淡泊的心志,她九歲來(lái)到海南島,22 歲畢業(yè)于楚地名校,50歲逝于抑郁癥。……她愛(ài)讀書(shū)、愛(ài)音樂(lè)、愛(ài)插花、愛(ài)吟詩(shī)、愛(ài)品茶、愛(ài)看畫(huà)展、愛(ài)美、愛(ài)靜、愛(ài)女兒、愛(ài)父母……無(wú)盡的愛(ài),無(wú)盡的惋惜……她趨雅向美,冰雪聰明……她是沉睡在花梗上的天使。”
的確,她一直把自己置于一個(gè)冠著風(fēng)雅名號(hào)的玻璃器皿中。她美麗、安靜,穿著旗袍,輕聲細(xì)語(yǔ)地說(shuō)話(huà),隔一些時(shí)間辦一場(chǎng)讀書(shū)沙龍,在種著綠植的露臺(tái)煮茶,水汽噗噗地從陶制的茶壺中冒出來(lái)。圍坐在露臺(tái)品茶的,都是風(fēng)雅之人,談笑皆鴻儒,往來(lái)無(wú)白丁。
藍(lán)蛾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長(zhǎng)大的。被富養(yǎng)的女孩子天然地有一股嬌憨之氣。藍(lán)蛾還長(zhǎng)著一張娃娃似的圓臉,年輕時(shí)可謂面若銀盤(pán),眉不畫(huà)而翠,眼含一汪盈盈秋水,看人時(shí)充滿(mǎn)一種深邃的智慧與哲思。
在一眾朋友中她算不得最美,但她嘴角隱隱的笑讓她獲得了好人緣。她的丈夫耳丁是她大學(xué)的校友。大一時(shí)耳丁對(duì)她一見(jiàn)鐘情,大學(xué)一畢業(yè),兩人就結(jié)了婚。婚后第三年,女兒出生。藍(lán)蛾對(duì)于新出生的女兒并沒(méi)有特別親近,面對(duì)孩子時(shí),她甚至生出一種煩躁和恐懼來(lái)。對(duì)于藍(lán)蛾的情況,耳丁有些擔(dān)憂(yōu),帶她去醫(yī)院,醫(yī)生言之鑿鑿:這是產(chǎn)后抑郁癥,要及早治。
藍(lán)蛾對(duì)醫(yī)生的話(huà)嗤之以鼻,她認(rèn)為自己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她從單位請(qǐng)了假,產(chǎn)假和年假,加起來(lái)足足一年。
藍(lán)蛾本來(lái)覺(jué)得自己也不過(guò)是一個(gè)普通的女孩,但自從生了孩子,得了這樣一個(gè)病,終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意識(shí)漸漸地膨脹起來(lái)。下腹一道剖腹產(chǎn)后留下的疤痕,像一條恣肆爬行的死去的蜈蚣,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背靠著背,拴在一起,沉沉地往下墜。
她身體的每個(gè)部位都開(kāi)始疼痛。她害怕醫(yī)院里冰冷的儀器。她到處收羅可以通過(guò)按摩來(lái)減輕甚至治愈身體痛苦的民間偏方。她遇見(jiàn)了很多神醫(yī),在神醫(yī)供職的各類(lèi)國(guó)醫(yī)館辦了卡,卡里的金額十分充足,把卡撐得滿(mǎn)滿(mǎn)的,仿佛這樣就能把她身體里的病毒驅(qū)除出去。
她找每一個(gè)認(rèn)識(shí)的人說(shuō)話(huà),一說(shuō)就說(shuō)上兩個(gè)小時(shí),話(huà)題都寬泛,從上古時(shí)期的神話(huà)人物盤(pán)古到如今的當(dāng)紅女作家賈賈。后來(lái)認(rèn)識(shí)的人見(jiàn)了她就避。避之不及,就假裝不認(rèn)識(shí),與她擦肩而過(guò)時(shí)目不斜視,仿佛要前往的是一條通向羅馬的金光大道。
藍(lán)蛾并不是沒(méi)有眼色之人。在認(rèn)識(shí)的人都昂著頭從她面前走過(guò)之后,她發(fā)奮地寫(xiě)作,寫(xiě)詩(shī)歌、寫(xiě)散文,有時(shí)候,覺(jué)得精力還足夠充沛,就寫(xiě)小說(shuō)。以她過(guò)于豐富的想象力,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極有可能成為一位杰出的小說(shuō)家。她想通過(guò)小說(shuō)來(lái)創(chuàng)造自己的存在。她給自己取了個(gè)很好聽(tīng)的名字,叫“清泉”。
2015 年6 月,她以清泉的名字從電子郵箱開(kāi)始進(jìn)入我的生活。作為一個(gè)負(fù)責(zé)任的文學(xué)副刊編輯,我告訴她,我們不刊載小說(shuō),她的下一封郵件就換成了七篇散文。她的散文里一次又一次,重復(fù)不斷地積累著日常瑣事,記錄下她頭腦中的一切想法。她的每一篇散文都很長(zhǎng),內(nèi)容包羅萬(wàn)象,仿佛她的世界里有著廣闊的森林。她的行文散漫,如同在跟隔壁的鄰居聊天。溫著炭火,火苗一簇一簇地跳躍,林間小路上是斑駁的樹(shù)影,空地上人影交錯(cuò),忽隱忽現(xiàn)。她逮著文章里的每個(gè)人說(shuō)話(huà),話(huà)題也散漫,無(wú)法匯集成一個(gè)整體。但小說(shuō)里的人不會(huì)避了她,她于是滔滔不絕,不知疲倦,讓所有人都生活在她的存在之中。
為了同更多的人說(shuō)話(huà),她加入了教會(huì)和各種協(xié)會(huì)。她的一個(gè)教會(huì)姐妹告訴她,她的丈夫耳丁出軌了,出軌的對(duì)象是他的合作者葉銀。他們?cè)谒{(lán)蛾生下孩子沒(méi)多久的時(shí)候就認(rèn)識(shí)了。耳丁在初見(jiàn)時(shí)就愛(ài)上了葉銀,中間因?yàn)槿~銀劈腿了另一個(gè)男人,把耳丁甩了。但耳丁一直對(duì)葉銀癡情守望。在葉銀甩了另一個(gè)男人的時(shí)候,耳丁迅速補(bǔ)上。此時(shí)的葉銀離了婚,有一個(gè)乖巧的女兒。離了婚的葉銀顯然更加迷人,即使耳丁在電視臺(tái)里見(jiàn)過(guò)無(wú)數(shù)美女,這么多年來(lái)一直對(duì)她牽腸掛肚。
知道耳丁出軌的那個(gè)早晨,藍(lán)蛾正坐在自家的客廳里剪枝、插花。這是她難得不想說(shuō)話(huà)的時(shí)光。她嫁給耳丁有十五年了。耳丁性情溫和,喜歡熱鬧,經(jīng)常無(wú)緣無(wú)故地放聲歌唱。但他們之間缺乏理解,一個(gè)喜靜,一個(gè)好動(dòng),這樣的兩個(gè)人配成一對(duì),并不十分和諧——然而,她還是喜歡他并不十分溫暖的擁抱。她在他抱著她的時(shí)候,可以多說(shuō)十多分鐘的話(huà),他臉上也不顯出十分的厭煩。——為了這十多分鐘,她就老老實(shí)實(shí)地愛(ài)著他了。
茶幾上擺著一瓶玫瑰,她手中的剪刀在她愣神的時(shí)候無(wú)知覺(jué)地剪去了幾片卷曲的花瓣,發(fā)出干枯嘶啞的響聲。她急切地想說(shuō)話(huà)。她把身上的蕾絲花邊睡衣攏緊,往黑暗的臥室走去。她伸出胳膊,摸到床頭的位置,在床邊躺了下來(lái)。她的已經(jīng)出軌的丈夫就躺在一邊。她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睜大眼睛看著頭頂上潔白的墻,感到自己的心在劇烈地疼痛。
月光透過(guò)藏綠色的百葉窗,一道一道橫切屋里的黑暗。他背朝她躺著,她看見(jiàn)他一腦門(mén)的青光,在月光中有些分外的白。她想把他搖醒,她儲(chǔ)著一肚子的憤怒和恐懼需要發(fā)泄。她的手伸出去,在對(duì)著他鼻尖的空中晃了晃,又緩緩地放下。她生來(lái)就軟弱,從身體到個(gè)性。她給每一個(gè)遇見(jiàn)的人以溫柔的微笑,說(shuō)話(huà)語(yǔ)調(diào)也是軟的。大家說(shuō)起她來(lái),就都異口同聲地感慨:咳,這真是一個(gè)好女人。
她被“好女人”的圈箍著。在發(fā)現(xiàn)丈夫出軌之后,她沒(méi)有像普通女人一樣一哭二鬧三上吊。她把自己蜷縮進(jìn)一個(gè)角落里。她在黑夜中聽(tīng)著男人震耳欲聾的呼嚕聲,感覺(jué)心里有什么在坍塌。她想象自己是古代的浣衣女,在最繁忙最滿(mǎn)足的時(shí)候放下手中的衣服。丈夫一周換下來(lái)的衣服、床單和睡衣,在她的手中粉身碎骨。她想用語(yǔ)言去聲明這一點(diǎn),但除了她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休息,不受任何打擾。頭頂?shù)娜K蓮花形燈也悄無(wú)聲息,仿佛所有的一切都身處曠野之中,目之所及,一望無(wú)垠,蕭瑟的冬沒(méi)有繁殖綠的能力。一切都是靜止的。
她的意識(shí)越來(lái)越清醒。她發(fā)現(xiàn)了蓮花燈上匍匐著的那只飛蛾。飛蛾其實(shí)在做展翅欲飛狀。像野鳥(niǎo)掠過(guò)高聳的群山,繼續(xù)充滿(mǎn)野性力量地飛行。
南邊的窗戶(hù)被風(fēng)吹開(kāi)了,一些風(fēng)帶著潮氣進(jìn)入她的身體。她感覺(jué)胸腔里有一些火開(kāi)始滋生,漸漸地熊熊燃燒起來(lái)。那火苗仿佛落滿(mǎn)灰塵的光,虛弱無(wú)力卻又倔強(qiáng)地想要逃脫耀眼的陽(yáng)光帶來(lái)的尷尬壓力。
她在天蒙蒙亮的時(shí)候把耳丁叫醒。他們是那天民政局開(kāi)門(mén)后的第一對(duì)顧客。民政局的人都沉默,他們見(jiàn)慣了離婚時(shí)男女雙方的丑態(tài),已經(jīng)沒(méi)有欲望去探究結(jié)婚證上的這對(duì)男友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guò)些什么。
不到十分鐘的時(shí)間,離婚證就辦好了,藍(lán)蛾和耳丁各持一本。沒(méi)有什么財(cái)產(chǎn)分割,為了不讓女兒察覺(jué),兩人決定離婚不離家,依舊在一個(gè)院子里居住,生活照常。只是女兒不在家時(shí),就可各自找尋幸福,誰(shuí)也管不著誰(shuí)。
從民政局出來(lái),藍(lán)蛾提議走路回家。回去的路程很長(zhǎng),一路上兩人誰(shuí)也沒(méi)說(shuō)一句話(huà)。耳丁后來(lái)拐了道,把藍(lán)蛾帶到一家名為“意外”的小酒館。酒館里外的裝飾都有一種文藝腔調(diào),是藍(lán)蛾喜歡的。
那晚他們都喝得酩酊大醉。藍(lán)蛾從耳丁的眼睛里看到愧疚,做了十五年的夫妻,對(duì)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通過(guò)緩慢的符號(hào)傳達(dá)給他有關(guān)的信息。
酒醒后的耳丁搬離了他們共同的臥室。藍(lán)蛾靜靜地坐在床上,守著幾本舊影集。影集的一頁(yè)掉出來(lái)一張,是她大學(xué)時(shí)站在櫻花樹(shù)下朝耳丁羞澀地微笑的照片。后來(lái)他們結(jié)了婚。再后來(lái)他們開(kāi)始吵架,記不清每一次吵架的具體內(nèi)容,但這期間她對(duì)于生活漸漸地恐懼起來(lái),腦子里成了一團(tuán)亂麻。她感覺(jué)渾身都疼,各種幻覺(jué)有條有理地互聯(lián)起來(lái)。她完全不能像正常人一樣思考。她到處找名師按摩身體,她急切地想把胸腔里淤堵的這些氣盡快地排出去。對(duì)于和人類(lèi)之間的語(yǔ)言上的交流,她已經(jīng)徹底感到絕望。她急需一個(gè)出口,一個(gè)能容下她所有秘密的樹(shù)洞。她想到了匍匐在蓮花燈上的飛蛾。飛蛾窄窄的雙翼如同一片枯草,翼梢如流蘇,點(diǎn)綴著同雙翼一樣的枯草色。她不知道這飛蛾是不是曾經(jīng)來(lái)過(guò)的那只,它一直用同一個(gè)姿勢(shì)在親近蓮花燈。它在燈影中來(lái)回穿行,讓她不由得生出一絲愛(ài)憐。這個(gè)夜里,她發(fā)現(xiàn)生命的快樂(lè)在飛蛾身上體現(xiàn)得十分完滿(mǎn),宏大寬闊而又千姿百態(tài)。飛蛾的生命過(guò)于短暫,但它卻盡情地享受著任何一點(diǎn)微不足道的快樂(lè)。
藍(lán)蛾覺(jué)得自己找到了知音。她連著幾天幾夜和飛蛾待在一個(gè)密閉的空間里。夜里的飛蛾充滿(mǎn)熱情,生機(jī)勃勃地從領(lǐng)地的一角飛到另一角,爾后,繼續(xù)飛向第三個(gè)、第四個(gè)角落。她注視著它,喋喋不休。沒(méi)有人會(huì)對(duì)她喊停,她說(shuō)得神采飛揚(yáng),仿佛整個(gè)世界巨大的能量化作一根細(xì)絲,注入她柔弱而驕傲的身體中。每當(dāng)它在燈影里扇動(dòng)翅膀,她便設(shè)想著有一絲生命之光亮起,群山壯闊,天空浩瀚,炊煙遼遠(yuǎn)。
離婚一年后,她在一次讀書(shū)會(huì)上遇見(jiàn)了新的愛(ài)情。她像一只瘦小羸弱的飛蛾,在黑暗中尋著那一絲光,尋著了,便以簡(jiǎn)單直接的形式從敞開(kāi)的窗戶(hù)撲過(guò)去,不管窗外是懸崖還是深淵。她的奮不顧身在我和其他人腦中那逼仄復(fù)雜的盤(pán)廊中沖擊而過(guò),令人擔(dān)心和唏噓。
她的新男友是個(gè)有婦之夫,這使得這份愛(ài)情從一開(kāi)始就不對(duì)等。除了她自己,沒(méi)有人見(jiàn)過(guò)這位神秘的新男友,他像是她出于必要的局限臆造出來(lái)的人物,生活在一個(gè)自由的世界中。所有的故事情節(jié)由創(chuàng)作者本人來(lái)證實(shí),其真實(shí)性完全屬于作者的想象。但這想象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作者本人。她開(kāi)始變得活躍,感覺(jué)這花花世界充滿(mǎn)了各種愉快的東西——櫥窗里的華服、精裝本大菜單上的珍肴、最文藝范兒的房間,里面空無(wú)所有,除了高齊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她在大玻璃窗下鋪設(shè)暖調(diào)的地毯,地毯上隨興散落幾個(gè)五顏六色的軟墊。——后來(lái)我在一個(gè)夜晚陪她回家時(shí),發(fā)現(xiàn)這個(gè)文藝房間也許也是她臆造出來(lái)的。她的家里,是暗沉的中式家具,沙發(fā)扶手上的雕花都有著分外的講究。家里的飾品和茶具堆得滿(mǎn)滿(mǎn)當(dāng)當(dāng),兩三本書(shū)翻開(kāi)在某一頁(yè),偶有風(fēng)來(lái),在沙發(fā)上沙沙作響。
她的睡眠一直很差。不管多累,與意識(shí)分離的痛苦都會(huì)引起她無(wú)法言說(shuō)的反感。她發(fā)現(xiàn)即使天天詛咒睡眠之神也并無(wú)任何改善,這是一個(gè)兇殘的黑臉劊子手。對(duì)此,她毫無(wú)防衛(wèi)之術(shù)。她與人類(lèi)的交集本來(lái)不多,因而,每一個(gè)夜里同飛蛾的交談,就成了她唯一能依賴(lài)的微弱光亮。她在徹底的黑暗中會(huì)感覺(jué)頭暈,如同靈魂會(huì)在昏暗的睡眠中消解一樣。
她的工作壓力越來(lái)越大。新調(diào)來(lái)的上司與原來(lái)的上司矛盾不可調(diào)和,又不能直接開(kāi)撕,兩人都選擇在夜深人靜時(shí)找她吐槽。她誰(shuí)也不能得罪,就打哈哈吧。后來(lái)打哈哈也不行了,無(wú)論如何也得說(shuō)出個(gè)子丑寅卯。她于是閉著眼睛說(shuō)一些不著邊際的話(huà)。她感覺(jué)自己正處在一場(chǎng)大病之中,每天白晝黑夜都在感受著痛苦。她的痛苦比跳天鵝舞的演員彎曲低垂的蒼白胳膊更接近藝術(shù)真實(shí)。
她給自己放了一個(gè)多月的假。回到我們身邊時(shí),歲月的刻針把她的圓臉刻成了輪廓分明的瓜子臉。臉龐變小了,眼睛里有一種迷茫的親近。她的話(huà)變得更多了,仿佛噴壺嘴,瑣碎繁雜,絮聒叨叨。但她說(shuō)話(huà)的語(yǔ)速很慢,語(yǔ)調(diào)聽(tīng)起來(lái)也是昏昏沉沉的,仿佛她的嘴懸在另一個(gè)世界里,在慢慢地往下沉。
新的春天來(lái)時(shí),她的新愛(ài)情夭折了。
她受不了這痛苦。她想早一點(diǎn)結(jié)果她自己。
她的病也越來(lái)越不耐煩。她整日整夜地在床上躺著。有幾次她想撐著爬起來(lái),也許撐著撐著就過(guò)去了。
耳丁帶著她去了幾次醫(yī)院。醫(yī)生們的診斷分毫不差:患的是抑郁癥。夜里,耳丁搬回他們?cè)?jīng)同床共枕的臥室,在藍(lán)蛾的床邊支起一張軍用旅行床。耳丁按照醫(yī)生的要求,天天給藍(lán)蛾按摩。每逢他的手輕輕地按到她胸肋上,微涼的手指的碰觸,讓藍(lán)蛾忍不住戰(zhàn)栗。她知道自己這病根在于這雙手,她以為可以執(zhí)一生的手,卻去觸碰了別的女人。
從藍(lán)蛾的少女時(shí)代起,世人就能在她眼中看到“愛(ài)情似乎是永恒的可能”。愛(ài)耳丁幾乎成了她人生的信仰。直到他們離婚,這愛(ài)情依然“存在”,像一個(gè)來(lái)去無(wú)蹤的幽靈,一直在尋求永恒。她像個(gè)誤墜人間的天使,對(duì)于世間轉(zhuǎn)瞬即逝的事物毫無(wú)概念,無(wú)數(shù)的苦難和煩惱困擾著她。她用歡樂(lè)和悲傷給她的愛(ài)情幻象織就了一個(gè)溫暖的繭。鏡花水月轉(zhuǎn)瞬成空,她心頭枯敗的愛(ài)情,卻在遇見(jiàn)縫隙里的一絲光就能明亮而持久地燃燒。
我去看她的時(shí)候是黃昏。她躺在客廳的絨布沙發(fā)上,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客廳里的燈暈黃著,和窗外的夕照一樣,有一種沉沉老去的暮氣。她的圓臉愈發(fā)地尖了,卷發(fā)蓬散著,看起來(lái)像一株枯敗的海棠,凋是凋謝了,花的底子形狀還在的,薄薄的一片,風(fēng)一吹,卻也就落了下去,總要打幾個(gè)轉(zhuǎn)的,依依復(fù)依依。
她一天一天地瘦了下去。我握著她的手,感覺(jué)她的肉體就從我指底溜走了。病了半年,她成了骨癆。她吃不下任何東西,偶爾吃進(jìn)去一點(diǎn),就在胃里梗著,身體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就整張臉都得憋著,人都憋得變了形。
她影影綽綽地感覺(jué)到了耳丁面對(duì)她時(shí)的不耐煩。她知道自己如今已經(jīng)是個(gè)拖累,對(duì)于整個(gè)世界都是個(gè)拖累。
她的愛(ài)情已經(jīng)徹底地死了。在她的肉身枯朽之前。
死的欲望越來(lái)越強(qiáng)烈。她把自己關(guān)在臥室里的時(shí)間越來(lái)越長(zhǎng)。她在與蓮花燈上的飛蛾進(jìn)行對(duì)話(huà)。她所要的死是詩(shī)意的,可以讓人長(zhǎng)久銘記的死。可是對(duì)于病人,人們的眼睛里沒(méi)有悲憫,他們可以陪著電視劇里的林黛玉流淚,但不會(huì)對(duì)身邊的肺癆病人有一絲親近的想法。人們總是更易于接受戲劇化的悲哀、虛假的悲哀。
可是有時(shí)候藍(lán)蛾也有一些樂(lè)觀。逢到好天氣,小鳥(niǎo)在窗外啁啾,也能暫時(shí)沖淡死亡籠罩在她身上的陰影。把厚重的簾布拉開(kāi),枕頭在太陽(yáng)里曬過(guò),也能留一些香氣。窗外的天,到底與過(guò)去是不一樣了。想起剛和耳丁結(jié)婚時(shí),每天夜里,他抱著她,一起站在窗前看星星。有流星劃過(guò),耳丁就大聲嚷嚷:快,快許愿……她其實(shí)比他更早發(fā)現(xiàn)那顆流星,早早地在心里許了“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愿望。但走著走著,這樣美好的兩個(gè)人,終究還是走散了。
有那么一陣子,以前的生活就像一幕幕戲劇在藍(lán)蛾眼前浮現(xiàn)。到了夜里,這些場(chǎng)景被燈盞籠罩,更顯出異樣的剪影。藍(lán)蛾心里的感受會(huì)疾速膨脹,如同被注入空氣的氣球。當(dāng)這美麗的幻象膨脹到最飽滿(mǎn)緊張的時(shí)候,一根針刺了下去,它轟然坍塌。
這個(gè)星期三其實(shí)很平靜,太陽(yáng)沉下去后,黑夜和往常一樣迅速蔓延。藍(lán)蛾把植著蘭花和海棠的瓷盆從客廳搬到臥室,一一擺放在淡青色的窗臺(tái)上。她清楚地知道,當(dāng)她從樓頂下墜的時(shí)候,會(huì)經(jīng)過(guò)這個(gè)窗臺(tái),她會(huì)帶著它們驚詫的目光進(jìn)入另外一個(gè)世界。
她把臥室里的書(shū)都收到書(shū)柜里,給自己換上一襲真絲白底青綠繡花旗袍,披上她最喜歡的繡著大紅玫瑰的流蘇披肩,然后安安靜靜坐在窗臺(tái)邊的藤椅上,看蓮花燈上新來(lái)的一只飛蛾。這只飛蛾弓背凸肚,粉雕玉琢,踽踽獨(dú)行,仿佛知道這是一個(gè)特殊時(shí)刻,每一步都充滿(mǎn)極致的慎重與莊嚴(yán)。
飛蛾繞著蓮花燈飛了一圈又一圈,進(jìn)行一場(chǎng)一演員一觀眾的落寞的獨(dú)舞。片刻后,它顯然是舞累了,停在了燈影里的窗格上。藍(lán)蛾看著它,面帶凄涼的笑。似乎為回應(yīng)藍(lán)蛾的殷切,飛蛾嘗試著重新起舞,但因?yàn)檫^(guò)于疲累,它的身子十分僵硬笨拙。它在窗格間拍打著翅膀掙扎著想要飛起來(lái),但每一次都失敗了。大約在第九次嘗試過(guò)后,它從窗格上滑了下來(lái),撲騰著翅膀,仰面倒在了窗臺(tái)上。仰躺著的飛蛾奄奄一息,但它的細(xì)腿還在努力地掙扎。然而此時(shí),死神如期降臨了。它的身體松懈下來(lái),隨即變得僵直。它毫無(wú)怨言地接受了死亡。
藍(lán)蛾安安靜靜地目睹了這只飛蛾短暫的一生。她走過(guò)去,擺正飛蛾的身體,讓它安詳高貴地躺在那里。而后,她把窗戶(hù)打開(kāi),雙腳并攏,雙臂張開(kāi),縱身一躍……如同飛蛾獨(dú)舞,片刻之后,夜空里空空如也,路過(guò)的車(chē)燈照在一樓院里樹(shù)籬上的一朵紅玫瑰上,越來(lái)越細(xì)弱,直至變成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