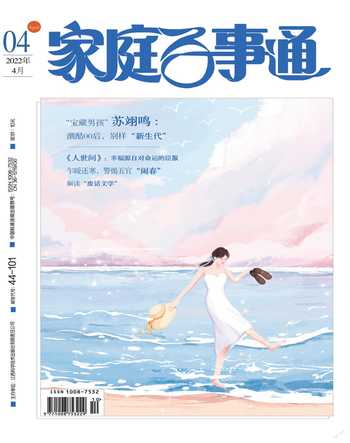責任,生命的壓艙石
于世忠

父親有勞動的習慣,在他接近八十歲的那一年,才真正撂下農具,從田地里走了出來。我們做兒女的都替他高興,他辛苦了一輩子,該好好歇歇了。可是,清閑下來的父親,變得無所適從,整天魔魔怔怔,像掉了魂一樣。有一段時間,他還心情煩躁,無來由地經常發脾氣。我們擔心他的健康出了問題,就帶他去醫院檢查,結果鑒定為中度阿爾茨海默病。我們也沒多想,就把父親一反常態的種種表現,統統歸罪于病情所致,除了監督他吃藥,再沒采取其他措施。
有一天,母親對我說:“看樣子,你爸也不光是病的原因,可能是不干活有點受不了。”我想,也有可能。父親干了一輩子活,乍一閑下來,會不會和城里剛退休的干部一樣,不適應呢?母親說:“我有辦法。明天我就交給他一個任務。”
第二天,母親搬來一筐棉桃,放在父親的面前,用抱怨的口氣對他說:“你老了也不能一點活不干,孩子們都很忙,你得替他們做點事,分擔一點責任。”父親很聽話,乖乖地坐在筐前剝起了棉桃。父親老了,手不聽使喚,剝得很慢,但他終究沒有閑著。就這樣,父親剝了一筐又一筐,我家的棉桃剝完,母親又從弟妹家弄一些過來。這份看似不是很重的“責任”陪伴了父親整個秋冬。剝棉桃需要活動手指,活動手指對腦血管健康有好處,這樣一來,父親的情緒不但穩定了,還讓他的病情有了好轉。
無獨有偶。一位關系甚密的朋友對我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也證實了這一點。朋友有位親戚,十幾歲的時候因一次醫療事故致殘,胸部以下全部癱瘓,吃喝拉撒全靠著侄子照顧。
年輕的時候,思想單純,他對身體、對生活還抱有一線希望。可是,等到上了歲數,所有的希望都看不到的時候,他開始產生絕望、厭世的念頭。在規勸他的過程中,善于察言觀色的侄兒找到了解開叔叔死結的方法。于是,他靈機一動,給叔叔制造了一份責任:看家望門。
他先是借口家里的大門壞了,在院子里的一根木桿上掛了一個鈴鐺,把牽連鈴鐺的線繩引進屋里,拴在叔叔的床前。然后,他在炕上加了一張床面,把叔叔睡覺的地方加高,使其與窗臺處在一個平面上。最后,他在臥榻北面的墻上,面對窗戶鑲上一面大鏡子,讓躺在床上的叔叔無須抬頭扭身,就能通過鏡子看清院子里的情況。農家小院養雞養鵝,堆放農具,還兼帶著晾曬一些糧食或雜物。這樣一來,叔叔就成了一個看家的人。
侄兒對叔叔說:“這個家就交給您了。”
有了看家的責任,從此,叔叔不敢懈怠,躺在床上時刻關注著院子里的動靜。誰家的雞狗進來,他一拉繩索,院子里叮鈴一聲,嚇得雞狗趕緊跑走了;有不認識的人進來,他也拉鈴通報,別人知道家里有人,就不敢胡來。
有了這份責任,叔叔活得不但心安理得,還覺得很有意義。從此,他沒有了厭世的情緒,一直活了很大歲數,直至壽終正寢。
生命需要一份責任。不管這份責任是大是小,是沉重還是輕松。責任,之于生命,就像一塊壓艙石,有了它,生命才有分量、有動力,才能行穩致遠。
編輯|郭緒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