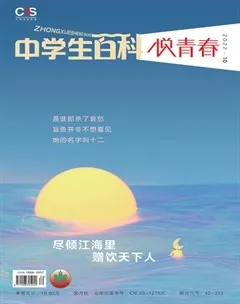自由職業真的自由嗎
碩士一畢業,我就回家做了自由職業者。幾年來,一天班都沒上過,僅靠版稅和稿費來養活自己。有時閑有時忙,收入不多也不穩定,但我對自己的職業非常滿意,因為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而且真的輕松自由。
經常有人問我每天都做些什么,是不是特別規律,給自己規定每天寫多少字,不完成不睡覺的那種。不知道別的作家是什么習慣,反正我在創作上很認真,但并不勤奮,不會每天都工作,工作日真正坐下來打字的時間也很短。主要還是看狀態,狀態好的時候下筆如有神,沒靈感的時候就不寫,因為硬著頭皮寫出來的東西要么粗劣,要么平庸,何必浪費時間精力?
仔細想想,我大部分時間好像都在生活——認真生活。比如清晨散步曬太陽,買菜做飯,讀書思考,運動,陪伴家人朋友,傍晚出去看看樹,看看花,看看日落,諸如此類。享受生活,這本身就是意義,即便從功利的角度說,這個過程也可以搜集素材和靈感。多數年輕人偏愛去快節奏的大城市打拼,而我更喜歡且更適合慢節奏的生活方式,這沒有好壞之分,純屬個人選擇。
回想畢業那年,我在北京等城市找到幾個很不錯的工作,最后卻都拒掉,選擇回家做自由職業者。我的想法是,先試一試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堅持不下去的話就再出來找工作,反正我有這樣的簡歷,底氣十足。當時親朋好友幾乎一致反對,在思想保守的小城市,我免不了承受各方面的輿論壓力,甚至害得家人也受到牽連。鄰居路上遇見,親戚過年串門,單位同事閑聊,都會互相詢問和攀比孩子的狀況。得知我畢業后沒找工作,他們無一例外地露出不屑鄙夷或擔憂憐憫的眼神。對此我早就習慣了,篤定從容地走自己的路,一句都懶得解釋。
“去單位上班”“找個鐵飯碗”是上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他們看來,體制內、穩定工資和“五險一金”比什么都重要,“自由職業者”等于“無業游民”。時代不同了,老一輩的固有觀念或許很難改變,但自由職業確實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追捧。
《韋氏大詞典》對自由職業者的定義是:獨立工作,不隸屬于任何組織,不向任何雇主做長期承諾而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很多人都對自由職業抱有美好的想象:收入高、時間支配自由、工作場所自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項目,是最具幸福感的職業。事實上并沒有那么完美:首先你必須要有一技之長,并為此付出長久的努力;其次是收入不一定高,但一定不穩定;時間和工作場所也不是總能隨心所欲;壓力并不小,每時每刻都面臨被淘汰的危險,不安、焦慮、迷茫、孤單,是自由職業者常有的情緒。不過,具體情況怎樣也要分人。
我有個朋友是出版社編輯,業余搞創作,我問她為什么不做職業作家,她說因為不敢,“收入太不穩定,一天收不到稿費就會坐立不安……”她勸我畢業后別做自由職業者。現在我做了職業作家,發現根本沒她說的那種焦慮。一方面是我目前生活壓力很小,只要能養活自己就行,不需要供養家庭;另一方面是沒什么野心,不給自己太大壓力,寫得開心就好,不怕窮也不怕被人罵“不求上進”。
每當有人抱怨“自由職業根本不自由”的時候,我都在想,自由與否,關鍵看你怎樣理解“自由”。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只要活著就一定會面對壓力和束縛,而且很多枷鎖其實都是自己給自己戴上的。對我來說,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自由的,可以保持最舒適的工作節奏,身體疲憊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撂下一切休息放松,不喜歡的工作就干脆果斷地拒絕,不用管對方是什么惹不起的大人物,也無所謂錯過的機會有多好——就是這么任性。但是,假如我事業心很重,給自己規定必須出多少本書、賺多少版稅,那么現在的職業可絕對是一點都不自由。
從某種程度上說,決定職業自由與否的,不是職業的性質,而是自己的心。我發自內心地喜歡現在的工作,并為自己畢業時的勇敢冒險慶幸不已。
高源
筆名蜜蜂聽雪,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洛陽文學院簽約作家;在《兒童文學》《讀者》等數十家刊物發表作品;曾獲“小十月”文學獎,《兒童文學》金近獎、“溫泉杯”大賽獎,徐志摩微詩歌大賽獎等;出版《長安夢》《秋安》《藍莓日記》《無法長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