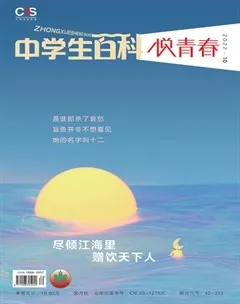打開盲盒時,你打開了什么
莫笑君
“盲盒經濟”是前兩年的一個熱詞,風靡大街小巷的盲盒有種要成為年輕人“社交硬通貨”的趨勢。原以為兩年下來差不多該冷靜了,結果一條新聞冒出,讓人意識到:原來盲盒還這么流行啊!只是,這次送盲盒上頭條的不是什么好事。
買的不是盲盒而是盲目
讓“盲盒經濟”走上巔峰的公司是一家專注于潮流文化的娛樂公司,其品牌玩偶,那個噘著尖尖小嘴、姿態嬌憨的女孩形象,這兩年不知道收割了多少年輕人的錢包。這不,該公司今年又秀了一波新操作,與一國外餐飲品牌聯名推出盲盒套餐,只要購買一份指定套餐,就贈送盲盒一個,里面裝有特殊造型的娃娃。
海報上顯示,娃娃的造型一共有7種款式:有坐在巧克力圣代杯里的,有身體造型是一根粟米棒、一杯可樂或一只漢堡的,還有頭頂全家桶或開著玩具飛機的,這些小可愛直戳盲盒愛好者的“粉色少女心”。看了新聞你會發現,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有錢人。有人為了集齊這套盲盒,一次性花費上萬元,購買了百余份套餐。
很快,中國消費者協會直接點名批評:這種做法已經超出了“創意營銷”的邊界,是妥妥的食物浪費。在“萬物皆可盲盒化”的風潮下,這大概是“盲盒經濟”迎來的當頭棒喝。盲盒的“拆法”本質上和“賭博”“博彩”相近,帶有非常明顯的讓人“沖動消費”和“盲目消費”的色彩。只是年輕的我們,很少有人愿意承認自己花錢買的不是盲盒而是盲目。
我們就是在“看臉”
“盲盒”的玩法說來也不新鮮。我還記得自己上小學的時候,流行一種今天已經銷聲匿跡的“集卡”游戲。當時,一群小學生就能把超市貨架上的“小浣熊干脆面”洗劫一空,只為集齊里頭附贈的“一百單八將水滸英雄卡”。一包面,一張卡,要拆開了才知道是哪個人物,這算得上是最早的國產盲盒游戲,而從成本上和規模上看,要比今天的盲盒來得更劃算,也更龐大。
雖然一包干脆面只要五毛錢,但事實就是,這反而更容易導致“糧食浪費”。我的鄰居阿姨就經營過社區超市。小時候,我去她店里買東西,經常看到里屋堆著一大堆一口都沒吃就被隨手丟棄的干脆面。阿姨有時會把那些被孩子們丟棄的干脆面送給乞討者,雖說惠及了這個弱勢群體,但浪費依然無法避免。
在集卡規模上,干脆面比今天的盲盒也更具挑戰性。今天的一套盲盒套裝也就六七種款式,而當時的“一百單八將”可是真的需要實打實集齊108張。后來,聰明的商家又在普通卡片的基礎上推出了升級款——銀卡和金卡,全套數量直接翻倍成了324張。這種規模的盲盒,放在今天也是難以想象的。那么,為什么它能夠流行呢?
當初的“水滸英雄”是基于古典名著《水滸傳》創造的,每一張卡片人物背后都關聯著波瀾起伏的歷史故事和千轉百回的英雄傳奇,這是那套卡再難集齊也深深吸引人的“靈魂”所在。古典文學大師為我們提供了現成的人設和故事,名著就是當時這個游戲最大的IP。
而今天,很多“盲盒人物”形象基本是“憑空產生”的。公司先邀請一眾設計師、藝術家,共同發揮靈感進行人物設計。接著,專門的運營團隊給人物取名、設定身份背景,完成“人設”塑造。最后,營銷人員將盲盒進行鋪貨銷售,同時還會推出一些線下展覽,打造“沉浸式”購物門店。整個流程下來,無不圍繞著互聯網社交特性開展,力求打造“網紅景點”,方便大家“拍照打卡”。這些標簽是不是耳熟能詳?
換句話說,相比當初的“水滸英雄”,如今的“盲盒人物”是速成的,沒有廣為人知的人物故事,也沒有復雜豐滿的人物形象,全靠商家一張嘴營造“人設”。從這一點來看,我們還真是疑惑:我們愛盲盒,到底是在愛它的什么呢?
別不承認,我們就是在“看臉”。
窺見真正的價值與美
盲盒給我們的警醒還不止這一點。“盲盒經濟”展現的,是一種非常古老卻又經久不息的商業套路:包裝,再直白點就是,換湯不換藥。
你會發現,很多年前流行過的東西,總能改頭換面一下,再流行一次。除了盲盒,還有許多其他類型,比如“螞蟻森林”。猶記得,曾風靡一時的“偷菜”游戲,讓好多人為之瘋狂,有人甚至設了鬧鐘,半夜起床去“偷菜”,簡直叫人哭笑不得。“螞蟻森林”遵循的也是同一個玩法,只不過“菜”變成了“能量”,“能量”又和我們的支付行為聯系在了一起—— 形式改變,套路不變。
人類本質上是熱衷于沉迷同一種游戲模式的,這和我們嗑瓜子越嗑越停不下來的心理如出一轍——因為簡單、重復的動作就能給大腦帶來正向、愉悅的反饋,我們的大腦會不斷釋放刺激信號,讓我們繼續重復甚至加強那個動作。只是每個深陷其中的人,都拒絕承認人類確實是臺“復讀機”。
“喜新厭舊”算是貶義詞,但在某些語境下,倒也值得發揚。比如說,在復雜的社會萬象里,我們不能輕易沉迷于一些徒有其表的老套路,而是要時刻提醒自己看清本質再理性選擇,如此,才可能看到這個世界的豐富與多彩,看到真正的價值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