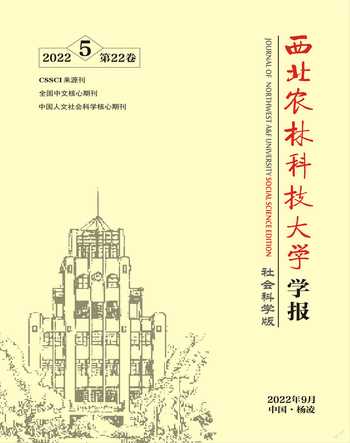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機理闡釋與典型模式比較



摘要:鄉村旅游在帶動農戶增收、促進產業升級方面的正向作用日益實現,已成為助推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通過構建“資源-結構-功能”演變的理論框架,就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作了系統解析。指出資源能力的不斷進階激發出鄉村旅游的發展活力,促成鄉村發生深層次變化,尤其是鄉村的空間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得到重構,促使鄉村功能逐漸優化,進而帶動鄉村全面振興。通過對四川成都兩個鄉村旅游典型模式的比較,解構了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動態過程,進一步印證了由“資源能力生成”到“鄉村結構重構”再到“鄉村功能優化”的理論框架的適用性和解釋力。
關鍵詞:鄉村旅游;鄉村振興;內在機理;“資源-結構-功能”理論框架
中圖分類號:F590-05;F590.7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5-0082-09
一、問題的提出近年來,鄉村旅游得到快速發展,在提升農民生計水平、促成農業多元經營、助推農村全面發展等方面發揮出重要作用,成為鄉村振興的實現載體和可行路徑之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農林牧漁業休閑觀光與農業農村管理服務實現增加值6 213億元,占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的3.7%[1]。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以時間短、距離近、頻次高為主要特征的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率先復蘇,成為旅游業恢復性增長最為突出的領域[2]。從既有研究來看,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互融互促已然成為廣泛共識[3]。一方面,鄉村旅游帶來資金、政策、技術等外部性資源的集聚,并與土地、勞動力、組織等鄉村本土性資源融為一體,產出的復合效益直接紓解了鄉村在經濟發展、文化保護、生態修復、自主治理等方面的危機困局[4];另一方面,鄉村全面、持續的振興發展也有效破解了鄉村旅游所面臨的市場開發、服務増質、產品供給、資源整合等方面的制約梗阻,使發展鄉村旅游的內外環境得到雙向優化[5]。基于以上共識,學者們從理論解析和經驗凝練兩個層面,圍繞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6]、作用機制[7]、耦合機制[8]、分配機制[9]、評價體系[10]、路徑選擇[11]、實施策略[12]等展開了豐富研究。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從政策、理論、實踐等層面對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間的關系作了詳細解讀,為發展鄉村旅游、助推鄉村振興提供了一定參考,但以上三條研究進路相對獨立,使得鄉村旅游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間理論解析和經驗凝練的系統性程度有待提升,特別是缺乏將政策、理論、實踐納入同一研究框架,未能破解鄉村旅游究竟如何引導鄉村振興的“黑匣子”密碼。故而未來研究至少需實現兩個層面的跨越:一是突破以往運用個案研究法來記敘鄉村旅游發展案例“故事”的局限,深入挖掘并提煉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一般機制和內在規律;二是突破以往以靜態分析方式來解讀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過程機理的不足,從動靜結合的角度賦予理論解析以更大的適應性,從而使發展鄉村旅游與推進鄉村振興之間的學理解釋更具現實指導意義。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是一項由小到大、由點及面、由散至合的整體性復雜工程,涉及到多元主體參與、多類要素聚合、多種機制協同,并根據情境變化作出相應調適,進而實現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等五大振興目標的融合發展。因此,本文嘗試構建基于“資源-結構-功能”演變的理論框架,通過典型模式的比較分析,闡釋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為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實踐提供理論指引。
二、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機理闡釋
有研究指出,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是一個“螺旋上升、層次推進”的動態過程[11]。換言之,在鄉村旅游的帶動下,產業黏性得到增強、人才回歸加速實現、本地文化重煥活力、生態保護開發趨于平衡、組織建設邁向規范[13],進而助推鄉村振興。按照資源基礎理論的解釋,優質、異質的本地資源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力保障,但能否將其轉化為穩定、持續的輸入性驅動力,則更是關鍵所在。資源轉換效度主要取決于鄉村旅游參與主體的自主行動,本文將其稱為資源能力,即參與主體聚焦內外部資源進行理性決策、作出合適行動的能力。隨著鄉村旅游效益顯化,各方主體的行動趨于正式化和規范化,發展鄉村旅游所必需的資源能力得到培植、生成和鞏固。同時,由鄉村旅游發展而帶來的裂變增殖效應、磁場吸引效應、燈塔導向效應、能人帶動效應、迭代修復效應逐漸疊加,直接作用于鄉村結構的調適和優化,具體表現為鄉村空間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協同重構。而鄉村結構的正向調整也使鄉村功能不斷完善,尤其是在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鄉村經濟效率得以提升,鄉土特色文化有效傳承,生態保護開發更趨平衡,人才吸引能力明顯增強,鄉村治理基礎不斷鞏固。進一步而言,盡管不同村莊的鄉村旅游資源稟賦、具體形態及發展歷程不盡一致,但總體上仍體現出“資源能力進階-鄉村結構重構-鄉村功能優化”的發展路徑,最終實現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根本目標。具體如圖1所示。
(一)資源能力激發鄉村旅游活力
發展鄉村旅游的首要任務是采取資源識別、資源挖掘、資源整合等系列資源獲取行動,實現資源要素的在地重聚[4]。每個村莊均擁有著一定數量的資源,包括自然稟賦、人文景觀、基礎設施、產業積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類型。豐裕的旅游及配套資源固然有利于鄉村旅游的順利啟動,但既存資源更多表現為鄉村旅游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特別是旅游資源匱乏型的農村,亦可以通過培育、嫁接、轉化等方式來生成新的特色資源,彌補前期劣勢。此外,資源并不會自發地整合為一體,要形成推動鄉村旅游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量,離不開主體的能動性參與,將資源占據的優勢轉化為資源利用的能力。需要說明的是,鄉村的資源能力涉及到多個方面,如資源識別能力、資源拼湊能力、資源捕獲能力、資源整合能力、資源培育能力等。鄉村旅游主體的資源行動是村莊采取的聚焦內外部資源的組織行為,在不同的資源情境下,村莊通過采取不同的資源行動推動旅游資源能力的重塑。
換言之,鄉村旅游主體的資源行動關鍵在于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并逐步轉移到資源延伸、資源再構等更為高階的能力面向上來。具體來說,村莊首先要識別既有和潛在的資源規模,進而作出是否適宜發展旅游以及選擇何種細分業態的判斷。由于缺乏前期經驗,大部分村莊發展鄉村旅游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演進過程,從而決定了村莊需要借助小規模試驗來規避風險,因而采取資源拼湊的行動策略更為常見,即通過促成小范圍內的資源簡易聯結,完成旅游資源的初步整合。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壯大,拼湊方式逐漸不能滿足資源投入的需求。此時,資源獲取的邊界相應向外延伸,村莊更加主動地捕獲地方政府、旅游企業等外部主體所掌握的扶持政策、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資源,以滿足擴大旅游產業規模所需。但隨著單純依靠資源累加投入所產出的效益出現邊際遞減,實現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必然要向著質量為本轉型,也就需要重新構架旅游資源系統的體系結構、利用方式,將內外資源進行一體化再構,優化資源配置,依托更高階的資源再構動態能力培育新的優勢,一方面增強其在鄉村旅游市場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使休閑旅游業成長為支柱產業,持續激發鄉村發展的活力。
(二)旅游繁榮促成鄉村結構重構
鄉村旅游的繁榮所帶來的顯性效應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鄉村人居環境普遍改善,大多數旅游村莊為增強游客體驗、塑造服務口碑,往往會優先解決村莊的綠化、亮化、硬化等基礎設施配套問題,加之當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廁所革命”的刺激帶動,旅游村莊的“面子”更為干凈整潔;二是鄉村產業格局更趨優化,鄉村旅游相較于一、二產業有著更高的附加值,也為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可靠載體。得益于鄉村旅游的發展,農村打破了對以農產品種養殖和初加工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的依賴,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村產業鏈條延伸不足、風險抵御能力偏弱的劣勢;三是農民就業選擇更加多元化,鄉村旅游的發展必然開發出一批非農就業崗位,農民在家門口即可就業,同時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工資性或經營性收入占比,進一步增強以“半耕半工”為主要特征的農戶家庭生計結構的穩定性。
鄉村旅游不僅重構了村莊的產業格局,也在空間布局、勞動就業、家庭生計等領域產生了連鎖效應,推動鄉村空間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協同演變,為村莊可持續發展夯實結構性基礎。首先,村莊通過對旅游資源的拼湊、捕獲、整合與培育,鄉村旅游由弱至強,為科學調整村莊規劃布局、完善公共基礎設施、補齊公共服務短板、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鄉村旅游直接面向目標消費群體提供服務,大部分利潤留在了村莊,使村莊在城鄉要素市場中獲得相對公平的競爭地位;同時鄉村旅游帶來的“人氣流”“信息流”“資金流”,也為其他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利好條件,增強了農村經濟的韌性[14]。最后,鄉村旅游還能潛移默化地推動鄉村社會結構轉型。一方面,鄉村旅游將現代化的消費文化、經營理念、生活方式帶入鄉村,還有不少地方探索出“農戶+合作社+龍頭企業”“土地入股、股權分化”等模式,推動了村級組織治理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壯大,人才、資金、信息、技術等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渠道進一步暢通,相應地鄉村化被動為主動,引導更多資源流向鄉村,進而在縣域乃至更大范圍內形成鄉村旅游服務供給共同體[15]。
(三)結構重塑助推鄉村功能優化
鄉村不僅是滿足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間場域,也是農村經濟發展、鄉土文化傳承、鄉村公共服務建設及農民社會交往的平臺載體[16]。換言之,鄉村是一個發揮著多重功能的復合系統,表現為生產功能、生活功能、生態功能“三位一體”式地嵌套疊加[17]。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針,實質上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優化鄉村功能的綱領性要求。關于鄉村功能的演化機理,學者們提出了“空間推動論”[18]和“要素牽引論”[19]兩種解釋思路:前者認為工業化、現代化的推進賦予鄉村更多的空間意涵,鄉村在保留作為生產空間的傳統屬性基礎上,不斷向著消費空間轉變,進而使鄉村功能由內至外地得到極大擴展;后者則強調在資源要素流入或流出的作用下,鄉村功能相應地增強或衰退。而在結構功能主義看來,社會系統的各部分均遵循著某種既定結構來運行,并發揮特定功能以維持社會系統的穩定性[20],在典型化行動和創新型行動的影響下,社會系統的結構與功能二者間一直處于交互形塑的狀態[21],從而在結構調整與功能優化之間達成動態平衡。
按照結構功能主義的解釋,鄉村旅游在重構農村空間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必然使農村的生產功能、生活功能、生態功能發生新的變化,在多元主體參與、多類資源聚合、多方利益協調的綜合作用下,單維散點的功能變化轉向更緊密、更互補的功能協變。空間結構的重構使得農村的生產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之間形成了更為清晰的區域劃分,從而在空間布局上鞏固了鄉村多重功能協調發揮的基礎;農村經濟結構的重構不僅進一步理順了鄉村一二三產業間的關系,使生產功能得到強化,還為補齊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的短板提供了物質保障;而鄉村社會結構的重構既為實現共同富裕、擴大民主參與、增進社區團結等多維發展目標凝聚起廣泛共識,也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綠色生產、綠色生活的一致行動中構建起鄉村的生態保護屏障。最終使鄉村功能完成由“補齊”到“疊加”再到“黏合”的遞進式優化。鄉村在順利完成由資源能力進階到鄉村結構重構再到鄉村功能優化的完整過程后,鄉村產業振興、鄉土文化傳承、生態系統保護、資源可持續利用等多重目標得以協同實現,進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三、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資源-結構-功能”演變的理論框架可以發現,旅游村莊崛起的前提在于是否具備資源能力,關鍵在于能否實現資源能力的進階提升[22]。結合村莊內外旅游資源的多寡,以休閑旅游為主導產業的村莊可劃分為資源豐裕型和資源匱乏型兩種典型模式。自2019年起,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已推出三批共計1 199個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有學者在研究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基礎上,證實了其作為行業標桿和培育重點的代表性[23],意味著在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中選擇比較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同時,考慮到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基礎設施狀況可能造成的差異影響,增強案例間的可對比性,本文從同在一市的空間尺度選擇旅游資源相對豐裕的明月村和相對匱乏的五星村兩個村莊作為分析對象。明月村和五星村同位于四川成都,在2012年前后開始啟動鄉村旅游,并分別于2019年、2020年成功入選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盡管兩村的旅游資源稟賦不同,鄉村旅游發展起點有著極大差別(詳見表1),但從結果來看,兩村基本同步實現鄉村旅游的發展壯大,并在助推鄉村全面振興上取得良好成效,表征著兩條方向一致但方式有別的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實踐進路。
(一)識別整合內外資源,逐級鞏固鄉村旅游的競爭優勢
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縣甘溪鎮西部,地處大五面山淺丘帶,距縣城約20公里。轄12個村民小組,1 383戶4 086人。明月村生態本底優良,擁有6 000畝雷竹、2 000畝茶田,森林覆蓋率接近50%。歷史上,明月村一直是邛窯陶器的重要產地,制陶技藝傳承了300余年。2012年民間陶藝師李敏到訪明月村,意識到陶藝、古窯不僅有著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價值,更是開發潛力巨大的旅游資源。于是明月村便利用李敏的人脈,吸引一批工美大師、文化創客來到明月村成立工作室,以陶藝為主題的文創集群雛形開始顯現。隨后,當地政府決定重點發展明月村文化產業,聯合社會資本投資2.45億元推動明月國際陶藝村項目落地。2014年修繕后的明月窯正式接待游客,迅速成為集陶文化展示、陶藝體驗、陶器生產銷售、田園度假為一體的“網紅打卡地”。隨著旅游熱度激增,當地政府與村委會共同組建國際陶藝村項目工作領導小組,系統性地整合編排土地、人才、資金等要素。首先,將187畝國有建設用地優先用于新建文創項目,并引導村民出租閑置林盤,以緩解土地供給難題;其次,堅持筑巢引鳳的人才策略,在縣級部門選派當地干部,引進規劃運營專業人才,同時吸引100余位知名藝術家、建筑師、設計師入駐明月村;最后,統籌政府專項財政資金,并通過土地招標、拍賣、掛牌等方式,經評估論證有序引入優質項目,以滿足旅游核心區建設的融資需求。
五星村位于成都市崇州市白頭鎮南部,緊鄰崇州中心城區,路網發達、交通便捷。轄16個村民小組,878戶3 066人。五星村原是純農業村莊,以水稻、小麥、油菜等農作物種植為主。因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效益不高,五星村在2013年時仍被列為貧困村。因而對于旅游資源匱乏的五星村而言,發展鄉村旅游必須彌補兩大短板:一是開發旅游景點,實現游客引流;二是完善配套服務,提升游客消費意愿。為此,五星村主要采取了資源改造的靈活方式,來解決缺景觀、少配套這兩大痛點。其實早在2010年,五星村率先試點農業共營制,即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導土地流轉并實行規模化經營,引入職業經理人實現專業化管理,培育農業服務組織提供農業產銷一站式服務[24]。在多元主體共同經營下,五星村高標準農田建設快速推進,除建成近千畝的水稻種植大田外,還打造了草莓種植基地、稻田養蟹養魚示范基地等一批現代農業項目,前來體驗農事、觀光農田的游客日益增多,形成了五星村的第一個鄉村旅游增長點。隨著客流量的增加,五星村鄉村旅游業態單一的局限愈發明顯,游客引得來卻留不住。為此,五星村抓住獲批為成都市深化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的機會啟動新村建設,重新規劃村內閑置林盤,集中建設了800多套特色民居,為后續發展民宿、餐飲、文創奠定了良好基礎。
綜上可見,鄉村旅游發展的關鍵在于村莊能否聚焦內外部資源采取有組織的行動。明月村借助村莊制陶技藝傳承的資源優勢,在鄉村旅游發展初始期順利完成了由自發識別到自覺整合再到自主再構的資源能力進階,以識別歷史文化遺產為契機,依托政府財政扶持和社會資本加盟,破解明月村發展文創旅游面臨的資源束縛,形成多方主體強強聯合的有利局面。而五星村盡管缺少先天旅游資源優勢,但其早期做法表明,相較于資源豐裕型村莊,資源匱乏型村莊在鄉村旅游發展初始期借助資源拼湊能力,最大程度、最優效率地將現有資源賦以旅游價值,塑造特色旅游項目,同樣可以形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二)借力鄉村旅游效益,系統重構鄉村發展的結構體系
在激發村莊旅游資源能力后,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旅游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進而實現村莊經濟、空間、社會結構的重構,成為擺在不同旅游資源稟賦村莊面前的重要難題。如前所述,文創旅游的發展為明月村帶來的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游客流,促成了產業鏈條的延伸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明月村先后成立明月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雷竹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出制陶、印染、農事、民宿、餐飲等系列服務項目,以品牌化策略包裝當地手工藝品和農產品,衍生開發出明月陶、明月染、明月筍、明月茶、明月果酒等系列高附加值產品,使產業結構趨于優化。經濟活力的激發和經濟效益的累積也為明月村其他領域的結構轉型打下良好基礎。一方面,村民家庭生計不斷改善,村民既可出租房屋,也能自主創業,還能通過合作社提供的崗位實現非農就業,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近3萬元。另一方面,科學規劃村莊空間,改造院落、營造景觀時注重保護保留生態本底和文化本底,按照點狀供地的方式將新建建筑與田間山林融為一體,形成了“一核、四區、一環線”的空間布局。此外,明月村還構建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和收益共享方式,包括專門劃定村民創業區,支持創業成功的村民帶動群眾共同致富,合作社分紅時更多向村民傾斜等。
隨著大田景觀和民宿條件的成熟,五星村的鄉村旅游邁上正軌,對鄉村的結構性影響也愈發深刻。首先,農旅融合的產業結構漸趨定型。外來投資者進入五星村,創辦了五星春天酒店、一滿文旅、悅漫花園餐廳等特色項目,逐步覆蓋到餐飲、住宿、購物等多元業態。其次,田園濕地的空間布局開始成型。五星村集體經濟的壯大也為環境治理提供了資金保障,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河道整治、黑臭水體治理,把榿木河打造成為占地達五千余畝的濕地公園,并按區域經營方式將濕地公園與林盤民宿、農田景觀有機融為一體,使生態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實現統一。再次,兼農兼業的生計結構更加明顯。鄉村旅游帶來大量本地就業機會,不少村民返鄉創業。而為解決村民粗放經營、盲目競爭的弊端,五星村借鑒農業共營制的經驗,組建五星村旅游合作社,實行“五統一分”運行模式“五統一分”運行模式即統一資源收儲、統一規劃設計、統一招商引資、統一共享客源、統一管理服務、分戶經營。,以抱團發展的方式增強分散農戶的抗風險能力,提高其經營收入的穩定性。2022年,五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萬余元。最后,集體經濟的分配結構逐漸優化。隨著村級集體經濟體量不斷擴大,五星村把重點放在調整紅利分配、平衡個體利益和集體收益上,創新實施了“3322”新型集體經濟分紅方式“3322”新型集體經濟分紅方式即在當年集體經濟收益中,拿出3成用于全體成員分紅,3成用于擴大生產、升級農旅服務產品,2成用于獎勵先進個人、幫扶困難群體,2成用于基礎設施改擴建等公共事業。,既發揮出有效的激勵作用,也為帶動村民共富、加快村莊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歸結而言,明月村主要通過村莊結構升級,實現村莊產業多元化布局到鄉村一體式發展,即明月村在發展文創旅游的同時,能兼顧到村莊各領域的結構協同調整,一方面延伸產業鏈條,不斷增強鄉村經濟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另一方面克服資本的盲目逐利性,減少對鄉村原生生態、文化、空間的擠壓風險,使內外主體共享鄉村旅游發展紅利。與明月村相類似,五星村主要通過村莊結構調整,實現村莊單一結構布局向復合結構融合,即五星村在鄉村旅游發展成效初顯后,也有意識地引導鄉村結構的多維調整,一方面引入并整合社會資本,拓展鄉村旅游的業態類型,形塑一二三產業復合一體的鄉村經濟結構,另一方面聚焦空間結構、機會結構和分配結構的動態調適,具體包括通過改造生態濕地凸顯特色農旅主題,依托合作社統一管理賦以村民參與鄉村旅游并獲利的平等機會,借以紅利合理分配釋放鄉村旅游對產業提質、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激勵和保障作用。
(三)協同優化核心功能,全面助推鄉村振興的多重目標
鄉村振興的五大目標實質上指向了鄉村功能的一體化,進而打造復合疊加的功能共同體。明月村的發展成效集中展現在鄉村功能的持續強化上。首先,明月村以補齊公共基礎設施短板為重點,投資建成2 300余平方米的文化廣場、1 000平方米的綜合文化站、9公里的旅游環線、8公里的觀光步道,修建明月書館、明月畫室、明月鄉村研究社等公共空間,實現生產功能、生活功能、生態功能的協同優化。其次,明月村瞄準村莊軟實力的提升,以社區教育為抓手,豐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開創鄉村文化傳承的新局面。如培育舞隊、琴社、詩社、樂隊等6支群眾文藝隊伍,引進公益組織定期舉辦明月講堂、明月夜校,推動鄉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互動融合。最后,明月村依托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來助推村莊善治。如成立“五老”調解會、鄉賢理事會、道德理事會、村民議事會,激發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主動性;開展模范家庭評選活動,以良好家風涵養文明鄉風。
同樣,五星村在發展鄉村旅游之前,長期是以農業種植為主的傳統村落,農業生產效益不高,農民生活條件相對簡陋,農村生態環境受損明顯。而鄉村旅游的發展成為五星村多元功能互補強化的黏合劑。首先,借助資源改造,五星村將傳統農田轉化為特色景觀,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的附加值,也拓寬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使農業生產的效率得到提升。其次,五星村引導村民從散落林盤中搬遷出來,既實現林盤資源的活化利用,也改善村民的生活居住條件。最后,五星村整合多方資金治理河道、打造濕地公園,持續投資基礎設施改擴建,既增強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提升了生態品質和公共環境,將生產功能、生活功能與生態功能銜接起來,并促成功能間的疊加黏合。
總的來說,無論是明月村還是五星村通過激發村莊資源能力和重構村莊多重結構后,在很大程度助推了村莊生產、生活、生態等功能的優化,從而有力地推動村莊全面振興。概括而言,明月村主要依托文創旅游,從不斷補齊村莊顯性短板功能到提升村莊隱性公共治理功能,進而實現村莊全面振興。其關鍵做法主要有三:一是捕捉特色資源,整合內外力量,打造以“陶文化”為主題的品牌核心;二是依托鄉村旅游合作社,拉動相關產業發展,形成復合協同的多元產業結構;三是引導各類發展要素有序回流、合理配置,平衡政府與鄉村、集體與個人、新村民與老村民間的利益關系,優先保障鄉村長遠效益。由此,明月村達成了城鄉融合、文化傳承、經濟增長、生態保護、利益共享、治理改善的內在統一。五星村主要通過“田園變景區、林盤變民宿、農產品變禮品”的策略,從傳統農業村落的功能失調到現代產業社區的功能黏合,從而實現村莊旅游持續提質增效,發揮出推動鄉村振興的引領作用。其核心做法也主要有三:一是轉變對資源的認知局限,主動拼湊既有資源并推動資源旅游化;二是以鄉村旅游品牌建設為中心,逐步增強對外來資本的吸引力;三是注重引導鄉村旅游的經濟效益向社會效益、生態效益轉化,促成鄉村合理結構的生成和綜合功能的發揮。兩村的典型模式比較見表2。
四、結論與討論
作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有效載體,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必將成為未來熱點,而鄉村旅游助推鄉村振興,既是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更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以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重在理順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關聯,以鄉村旅游的點激活鄉村產業的線,進而輻射鄉村建設的面,經由鄉村結構的重塑和鄉村功能的優化,達致鄉村振興的多維目標。區別于以個案描述與經驗反思為主的已有研究,本文的貢獻在于建構了一個基于“資源-結構-功能”演變的理論框架,從邏輯演繹的角度論證了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并通過典型模式比較的方式驗證了該分析框架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就不同資源稟賦村莊的發展成效而言,無論是資源豐裕型村莊,還是資源匱乏型村莊,都有機會通過發展鄉村旅游來推動鄉村振興。兩類村莊的發展差異更多體現在初始階段,即根據擁有的旅游資源和面臨的內外情境,采取相匹配的資源行動,以促成資源能力的生成,并在資源能力進階提升的同時帶動鄉村結構重構、功能優化,最終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資源稟賦的村莊需要引導鄉村旅游所帶來的結構性影響和功能性變遷始終保持在可控范圍和正確軌道,才能真正實現從產業繁榮跨越到鄉村振興。
基于“資源-結構-功能”理論框架進一步審視不同資源稟賦的旅游村莊發展過程,還可得出以下四點有益啟示。(1)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實踐過程具有鮮明的系統性特征。不僅需要鄉村重點抓好旅游這一主業,培育起鄉村振興的突破點和著力點;更需要堅持系統思維、做好規劃設計,將鄉村旅游的發展置放于鄉村振興的全局中予以統籌安排。(2)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實踐過程并非是自動形成的,需要各方行動主體協同參與。既要發揮關鍵行動者的比較優勢,也需不同主體達成合作共識并付諸具體執行。(3)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雖離不開資源稟賦,但更依賴及時合理高效的資源行動,整合資源存量、促成資源轉換、創造資源增量。對于旅游資源匱乏型村莊來說,一系列資源行動可以加速旅游資源的初始開發,進而完成由無至有的轉變。(4)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需從長遠角度處理好二者的銜接問題,特別關注對鄉村結構、鄉村功能的內在影響。要使鄉村旅游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推動力量,重在釋放鄉村旅游對鄉村結構重構、鄉村功能優化的正向效應,讓農業增效、農村賦能、農民獲益,為鄉村旅游、鄉村振興不斷注入活力。總而言之,從“資源-結構-功能”演變的理論框架解析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不僅能夠有效回答鄉村振興戰略對鄉村旅游理論研究提出的時代之問,所梳理的經驗啟示也能為以提質增效為核心的鄉村旅游地方實踐提供有益參考。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20年全國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16.47%[EB/OL].(2022-01-12)[2022-01-3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1/t20220112_1826175.html.
[2]侯馨遠.鄉村旅游提質升級,路在何方?[N].農民日報,2021-12-22(03).
[3]盧俊陽,鄧愛民.鄉村旅游助推鄉村振興的實現機制與社會支持研究[J].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8(06):51-60.
[4]孫九霞,黃凱潔,王學基.基于地方實踐的旅游發展與鄉村振興:邏輯與案例[J].旅游學刊,2020,35(03):39-49.
[5]何成軍,李曉琴,曾誠.鄉村振興戰略下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耦合發展機制研究[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6(02):101-109.
[6]向延平.鄉村旅游驅動鄉村振興內在機理與動力機制研究[J].湖南社會科學,2021(02):41-47.
[7]傅才武,程玉梅.文旅融合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機制與政策路徑:一個宏觀框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60(06):69-77.
[8]李志龍.鄉村振興-鄉村旅游系統耦合機制與協調發展研究——以湖南鳳凰縣為例[J].地理研究,2019,38(03):643-654.
[9]盧祥波,鄧燕華.鄉村振興背景下集體與個體的互惠共生關系探討——基于四川省寶村的個案研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8(03):30-42.
[10]殷章馨,唐月亮.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評價與障礙因素分析:以長株潭城市群為例[J].統計與決策,2021,37(14):54-57.
[11]銀元,李曉琴.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旅游的發展邏輯與路徑選擇[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05):182-186.
[12]劉安全.省際民族聚居地區鄉村旅游集群發展的競合策略——以武陵山龍鳳示范區為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39(04):54-58.
[13]賈未寰,符剛.鄉村旅游助推新時代鄉村振興:機理、模式及對策[J].農村經濟,2020(03):19-25.
[14]陳佳,張麗瓊,楊新軍,等.鄉村旅游開發對農戶生計和社區旅游效應的影響——旅游開發模式視角的案例實證[J].地理研究,2017,36(09):1709-1724.
[15]戴學鋒,楊明月.全域旅游引領縣域治理的實踐探索——以江蘇省溧陽市為例[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8(06):91-99.
[16]李繁榮.中國鄉村振興與鄉村功能優化轉型[J].地理科學,2021,41(12):2158-2167.
[17]陳錫文.充分發揮鄉村功能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J].中國鄉村發現,2019(01):1-15.
[18]劉燕.論“三生空間”的邏輯結構、制衡機制和發展原則[J].湖北社會科學,2016(03):5-9.
[19]張強,霍露萍,祝煒.城鄉融合發展、逆城鎮化趨勢與鄉村功能演變——來自大城市郊區城鄉關系變化的觀察[J].經濟縱橫,2020(09):63-69.
[20]PARSONS T.The Social System[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1:25.
[21]ALEXANDER J C.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312.
[22]魏超,戈大專,龍花樓,等.大城市邊緣區旅游開發引導的鄉村轉型發展模式——以武漢市為例[J].經濟地理,2018,38(10):211-217.
[23]劉宇杰,周勇,劉小東,等.中國“鄉村旅游重點村”空間分布格局及影響因素[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56(01):211-220.
[24]羅必良.農業共營制: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探索與啟示[J].社會科學家,2015(05):7-12.
Explan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Lea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ypical ModelsLI Yige WU Shang
(1.Department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Nanning530007;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Abstract:Rural touris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which becomes a major force to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gui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evolution of “resource-structure-function”.It points out that resource ability constan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vitality,contributed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rural area,especially the rural space structure,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promoted the gradual optimization of rural functions,and then rural revitalization will be promoted eventually.In addition,the comparison of two typical rural tourism models in Chengdu and Sichuan province,destructuring the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gui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e applicabi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resource capacity generation” to “rural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and then to “rur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Key words:rural tourism;rural revitalization;intrinsic mechanism;a framework of “resource-structure-function”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