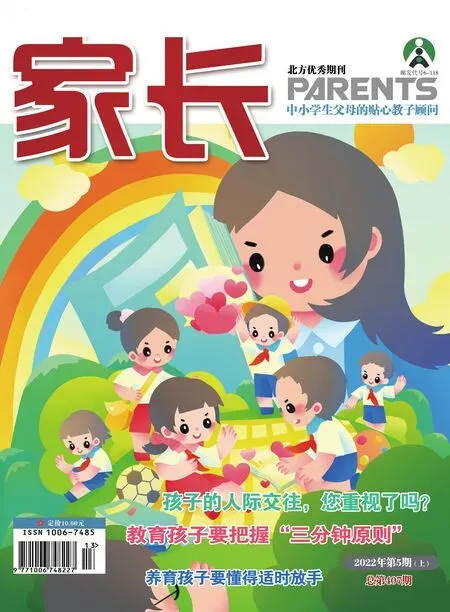視點
1 孩子上網課 家長莫焦慮

因為疫情防控需要,近期很多孩子又面臨居家上網課的情況,而一些企業也選擇居家辦公,于是,家長和孩子們長時間待在一個屋檐下,你嫌我網課不認真,我嫌你管得太多,相看兩相厭的情緒就又出現了,有些還鬧得雞飛狗跳。“家長居家辦公也可以專心做自己的事情,通過自己的專注去給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樹立起孩子學習模仿的榜樣,而不是緊迫感十足的人盯人。”有心理專家建議,家長應是孩子學習的輔助者,最好讓孩子自己去制訂居家學習生活的計劃,家長指導和修改即可,給孩子可以自由安排和喘氣的時間。家長把自己從“人盯人”中解放出來,才能從焦慮的情緒泥潭里走出來。
(摘自《揚子晚報》)
點評:孩子在家上網課,時不時做些小動作,抑或走神開小差,是難免的,也是正常的。家長適時給孩子提醒即可,切不可盯得過緊,指責不斷,搞得親子關系緊張。在這特殊時期,父母和孩子都居家,正是親子親近、溝通、交流的好時機,一起做飯、做家務,一起娛樂、健身,一起看書學習,在其樂融融的港灣里養精蓄銳……這些內容堪比上網課!利用好這難得的“同一屋檐下”,增強家庭軟實力,生活、工作、學習大有裨益。
2 校園門口抽獎游戲專坑小學生

今年中央電視臺的“3.15晚會”上曝光:在不少小學周邊,有很多文具店、小賣店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抽獎游戲,吸引一些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們一次又一次地掏錢抽獎。一家小店的66枚金蛋里面,只有7 個蛋設置了現金獎,5 個一元錢,2 個五元錢,中獎金額僅僅15 元錢。這種金蛋還可以重復利用,中獎率和中獎額度完全由店家說了算。集郵這種玩法套路更深。八十元錢買一整版共八十張獎券,得到320個卡通形象,但湊不齊任何一個中獎組合,每一個組合都差一張。其他幾款集郵抽獎玩具,同樣都是中獎組合只差一張。這樣的騙局,讓更多的孩子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摘自央視網)
點評:不諳世事的未成年人很容易被那些形狀新穎顏色花哨的貨品和誘人的“花小錢中大獎”廣告語所吸引,此類商品常常為逃避監管而“打擦邊球”,專門騙小孩,賺昧心錢。戳穿不良商家的把戲其實并不難,除了需要學校老師的提醒外,出資的家長也要關心孩子消費的去向,告誡孩子:這種“店家說了算”的花錢游戲掛上“抽獎”就是陷阱!發現了要遠離,誤入了快逃離,切莫讓血汗錢打了水漂。
3 “藝培熱”需要“冷思考”

“雙減”后,學生告別了學科類培訓,藝術類非學科培訓在不少地方開始走俏。然而,惡意漲價、夸張營銷、制造焦慮卻使得這種“熱度”有走偏之虞——剛剛“找回”的周末、假期,明明是為了讓學生回歸興趣、回歸“五育并舉”,卻出現了新的“趕場”。北京的王女士,為了孩子藝術考級可沒少花錢。“鋼琴一節課400元,舞蹈今年考到四級了,還有繪畫,也要考,都是錢。”“女兒今年初一,由于學習緊張沒時間再學舞蹈了,她從幼兒園大班一直跳到5年級,考到8 級。盡管她喜歡舞蹈,然而每次考級前都要集訓,買考級服、交錢,真不知道這些證對她讀初高中有幫助嗎?”一位山東家長也表達了困惑。
(摘自《光明日報》)
點評:藝術考級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檢驗學習效果的一種手段,然而,一些家長功利意識作祟,送孩子參加藝術培訓只是為了考級,或為升學增添一塊敲門磚。教育部早已明示,社會藝術考級或比賽不得作為學校美育評價指標,學校美育評價也不承認藝術考級結果,這就阻斷了家長功利化追求和作為應試籌碼的念想。“雙減”后,孩子出于興趣愛好、陶冶情操,參加藝術培訓、藝術考級并無不妥,但如果只是體現家長單方面的意愿,錢花了,累受了,孩子并未提升“幸福指數”,那又何苦呢?
4 小學霸為何是班里的“不卷”族

毛毛的同學和從前的好朋友平日與周末都忙于各種補習、各種考證,“雙減”后補習時間從周末調至周中,授課從線下調至線上。問毛毛那些同學是否真的喜歡補課,她一下子給出否定回答:“誰喜歡補課啊,誰不喜歡玩啊,但老師和家長一天到晚嘮叨——‘你們長大后,競爭一定越來越激烈’。”毛毛的成績在班上長期排第一第二,性格開朗,落落大方。她是怎么做到不用補習就成為學霸的呢?她說她有一位酷愛閱讀的媽媽,耳濡目染,言傳身教,讓她逐漸喜歡上了閱讀。她課堂上專心聽講,積極思考和回答問題。她喜歡徒步、攀巖等,每周與爸媽一起看一部迪士尼電影,表面上在玩,其實在“玩中學”。晚9點睡,早6點起,每日作息規律。
(摘自《中國青年報》)
點評:“雙減”后,有些家長還是擔心孩子的學習,躲開敏感時段敏感方式,線下改線上,大班變小班,想方設法為孩子學習“著想”。而為什么有的同學(如上文中的毛毛)不參加補習,成績卻總能拔尖兒呢?除了天賦外,看來家庭氛圍、父母影響、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有興趣、性格、情緒情感、意志品質等非智力因素也是有助推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