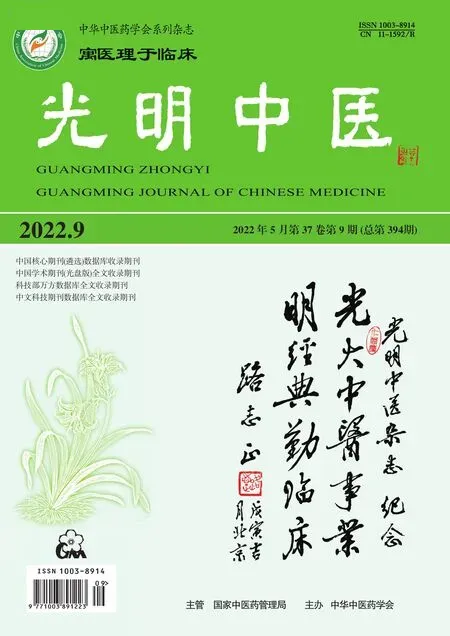淺議瀉必用方 補必用員的象與理
安麗娟 魏連海
《素問·八正神明論》中言:“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針,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針,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針。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針也。故員與方,非針也”。原文以“補瀉”開篇以明其意,并明確指出:“員與方,非針也”。《類經》[1]云:“非針之形,言針之用也”。即不言“方”“員”具體之針具的外形,是以推其蘊含補瀉之理也。筆者借助“取象比類”的思維方法,結合“天人合一”中醫學的整體觀念,對“瀉必用方,補必用員”背后的補瀉理論進行探析。
1 指導針刺補瀉時機
1.1 瀉必用方原文中云:“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類經》[1]中釋為:“方,正也,當其正盛正滿之謂”。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記載:“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意為“方”指相并的兩只船,字形下部像兩個“舟”字省略合并而成,字形上部像兩只船總纜在一起的樣子,可理解為運動中的兩舟達到持衡的瞬間,因此“方”在此可充當一個時間概念,即一個準確的時間點。故在此強調實施瀉法需要把握準確的時機,同時也說明實施瀉法的時間宜短,類似于能量的釋放,并且瀉法在短時間內就能取得療效。除此之外,結合《素問·八正神明論》中前文言及:“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故原文中“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這兩句暗示實施瀉法的時機,不僅與患者身體狀況及精神狀況相關,也需要考慮當時季節、氣候變化等外界因素的影響,體現了“因天時而調血氣”的治療思想,這是其一。其二,《素問·五常政大論》中有云:“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后,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這里強調了臨床中脈診的應用,醫者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對患者體質及現階段疾病狀況整體評估時,脈診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脈診既能反映全身臟腑功能、氣血、陰陽的綜合信息,又對外界環境因素對機體產生的影響反應靈敏。而“診法常以平旦”,在把脈時要求患者的狀態平和,其原因也在于此。脈診反映的是患者當下此時此刻的身體狀態,它足夠準確,但也容易受非病理因素影響。選擇好時間診脈,盡量避開非病理因素的干擾,就能診查出完整準確的病況。
1.2 補必用員《后漢書·張衡傳》中言:“員徑八尺”“員”,即園形,后作“圓”,可引申為使其圓滿、使其充盛之意,而其充盈的目的在于使經氣流通,即“員者行也,行者移也”。王冰注:“行,謂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移,謂移未復之脈,俾其平復”。經氣流通,移至病所,則病邪即祛而痊愈。“行者行其氣,移者導其滯。凡正氣不足,則營衛不行,血氣留滯,故必用員以行之補之”。這與《類經》[1]所注意思相近。另一方面,結合《素問·八正神明論》前文所述,通過取象比類,又可把“員”看作月亮,月亮從缺損到圓滿,從朔月到望月,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2]。因此,與“方”相反,“員”指的是逐漸圓滿、逐漸充盈,是一個持續的運動的過程。故補法類似于能量的蓄積,需要長期的投入,不能一蹴而就。《素問·八正神明論》中言:“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故“補必用員”之“員”也暗示隨著月亮的盈虧變化,人體的氣血、衛氣、肌肉、經絡也會隨之改變。因此醫者對患者的治療也需要隨著季節、氣候、患者經脈氣血盛衰的變化而改變,亦合乎前文之“因天時而調血氣”。這與《素問·八正神明論》中云:“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相契合。后世所創立的針刺“子午流注”與“靈龜八法”其理論依據也源于此[3]。由此看來,①“瀉必用方,補必用員”指出了運用補瀉時應掌握的具體規律,即把握補瀉的時機。有關這一點,除《素問·八正神明論》外,在《黃帝內經》中其他許多篇目都有相關論述。如《靈樞·九針十二原》中言:“粗守關,上守機”“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發,不知機道,叩之不發”。指出粗工與上工的最大區別在于是否掌握針刺補瀉的時機。上工能掌握經氣氣至的時機,并根據邪正盛衰的情況,施予恰當的補瀉。由此可以看出時機的重要性。②“瀉必用方,補必用員”還強調其補瀉的時機與季節、氣候等外界因素相聯系,治療宜“因天時而調血氣”。《難經·七十難》中有云:“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氣節變化、地理環境,乃至時間流轉都對人體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影響。空氣、光線、濕度、海拔、高度、電磁、音響、氣味、衛生等,都會對人體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背后也是中醫學整體觀念的體現,強調人與環境之間存在聯系性與統一性,并將其貫穿于中醫學的病機、診斷、辨證與治療中。
2 推理針刺補瀉手法
歷代針灸醫家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創造和總結出了許多針刺補瀉的手法。包括捻轉、疾徐、提插、呼吸、迎隨等單式手法,以及燒山火與透天涼、陽中隱陰與陰中隱陽、子午搗臼、龍虎交戰等復式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其背后的補瀉原理均與“瀉必用方,補必用員”相關。
論及手法,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理解“瀉必用方,補必用員”中的“方”與“員”。《素問集注》中言:“天包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4]。考《淮南子·本經訓》記:“戴圓履方”,即指頭戴天,足履地。又如漢班固的《西都賦》中有:“據坤靈之正位,放大紫之方圓”一句,唐呂向注釋此話:“言建宮室,方圓取象天地”。中國古代的傳統觀念中也有“天圓(員)地方”一說。“天圓(員)地方”出自《尚書·虞書·堯典》,這不是簡單地把天看成是圓形,地看成是方形,而是一種融合陰陽學說的哲學思想,其本質上是《易經》陰陽體系中對天地生成及其運行的解讀。古人把天地未分,混沌初起之伏稱為太極。《易·系辭》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生兩儀,劃分出陰陽,陰陽而生天地。古人把眾多星體組成的茫茫宇宙稱為“天”,立足其間賴以生存的田土稱為“地”。由于日月等天體一直在周而復始、永無休止地運動,仿佛一個閉合的圓周,無始無終,故稱為“天圓(員)”,屬陽,好動;而大地靜悄悄地承載著人類,仿佛一個方形的物體靜止、穩定,故稱為“地方”,屬陰,喜靜。孔子說:“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故“天圓(員)地方”講的是天地之道、陰陽之理。因此,“補員瀉方”可以引申為“補陽瀉陰”,由此可以推理出許多針刺補瀉手法的操作規律。
2.1 左升右降在《太極圖》中左白魚為陽,右黑魚為陰;其上(外)為天(陽),其下(里)為地(陰)。天氣從右而降、降者為陰地;地氣從左而升、升者為陽天,這是天地陰陽之氣升降變化的總則[5]。天陽在左主升,故左轉捻針“行陽”為補,應合“員天”之象;地陰在右主降,右轉捻針“行陰”為瀉,應合“方地”之象,這是捻轉補瀉的依據所在。在針下得氣處拇食指捻轉針柄,拇指向前食指向后時用力重,指力沉落向下,還原時用力較輕,此為“左轉”,為捻轉補法;拇指向后食指向前時用力重,指力浮起向上,還原時用力較輕,此為“右轉”,為捻轉瀉法。子午補瀉亦與之類似,《針灸大成·經絡迎隨設為問答》中有云:“故左轉從子,能外行諸陽;右轉從午,能內行諸陰”。除此之外,楊繼洲根據病證性質不同,以左右來區分補瀉:“假令病熱,則刺陽之經,以右為瀉,以左為補;病寒則刺陰之經,以右為補,左為瀉。此蓋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通變之法也”。見圖1。

圖1 太極圖
2.2 陽進陰退古代醫家常把腧穴的針刺深度分為深、淺兩層,淺者為上層,應天,屬陽;深者為下層,應地,屬陰。或將其分為淺、中、深三層,即天、人、地三部。因此可依據針刺腧穴的深淺、進入與退外動作的快慢,及出針與按穴動作的快慢,以區別補瀉的針刺手法。例如,在進退針時,徐入疾退,即為從天陽引地陰,為“補陽”,以應“員天”;疾入徐退,即為從地陰引天陽,為“瀉陰”,以應“方地”,這是疾徐補瀉的理論由來(見圖2)。在針刺得氣處,做先淺后深、重插輕提的手法,即緊按慢提,由上向下,引天陽下向地陰,此為“補陽”,以應“員天”;相反,針刺緊提慢按,由下向上,引地陰上向天陽,此為“瀉陰”,以應“方地”,這是提插補瀉的理論緣由。許多復式手法,如燒山火、透天涼等,也是在此基礎上,融合疾徐、提插、開闔、呼吸等單式補瀉手法而成。竇默在《標幽賦》中對冷熱補瀉手法的論述也一定程度上與之契合:“推內進搓,隨濟左而補暖,動退空歇,迎奪右而瀉涼”。意指熱補法即先針刺入穴內淺層后,緩慢推入深層,同時配合搓捻手法,沿經脈循行方向刺入補氣,并使針體左旋,此即補法,至針下有熱感而奏效;涼瀉法即逆經脈方向進針,刺入較深后進行提插,再將針提起后稍作停歇,再行提插,并配合右旋搓提,此為瀉法,至針下有涼感為度。

圖2 疾徐補瀉圖
3 總結
“瀉必用方,補必用員”既能指導針刺補瀉時機,又能推理針刺補瀉手法的操作規律。正所謂理從象出,法由理來。對“瀉必用方,補必用員”的解讀關鍵在于對“方”“員”之象的理解,這種“象思維” 在針灸的起源、形成與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從對“象”的認知過程中往往能尋找到中醫理論研究的突破點。
“象”的概念起源于《周易》,而《系辭下》中言:“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象”有物象、形象、意象之分,物象側重一個“物”字,強調客觀實在,指事物本身的形狀、特性等,形象則更側重于可視化,此兩者均屬于表象,而本研究所談及的“象”以及《黃帝內經》里面提及的“臟象”“脈象”“氣象”等“象”的概念更近似于意象或抽象,即主體以表象為原材料,經過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等加工,按照主體的目的重新構建起來的形象,是一種能動的理性形象[6]。中國學者王樹人[7]在談論中西思維差異時提出,所謂“象思維”就是指運用帶有直觀、形象、感性的圖像、符號等象工具來揭示并認知世界的本質規律,從而構建宇宙統一模式的思維方式。“象思維”是提出和發現問題的思維,是原創的母體、原創性的源泉,其目的是把握認知世界的聯系。“象思維”是中華文化的主導思維,也是中醫學的重要思維方式。《黃帝內經》有言:“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中醫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并非以物質實體為直接依據,而是構建了一個間接與物質實體相聯系的系統——臟腑經絡氣血系統,其核心就是“象”。“理”從“象”出,“法”由“理”來。“象”構成最基本的層面,是“理”與“法”所依賴的基礎;“理”與“法”則是“象”的應用。“象”“理”“法”三者相輔相成,由此建構而成了中醫學極具特色的“象思維”方式,貫穿于中醫診療的全過程,如司外揣內、見微知著、以常衡變的診察方式以及“增水行舟”“提壺揭蓋”“釜底抽薪”“揚湯止沸”等具體治療思路。
于本文而言,《素問·八正神明論》開篇即云:“黃帝問曰:用針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方”“員”之象充分體現了中醫學重視天、地、人合一的宇宙觀,“瀉必用方,補必用員”也是基于對“天人相應”理論的理解而提出的補瀉之法。《素問·寶命全形論》中言:“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的生命來自自然,同時也受自然界規律的制約。因此無論是補是瀉,人體功能狀態的調整都要和自然天地的變遷相適應,遵循“法天則地”的中醫治療原則,切不可因急于獲得療效而違背人體自身的自然規律。此乃“瀉必用方,補必用員”背后之真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