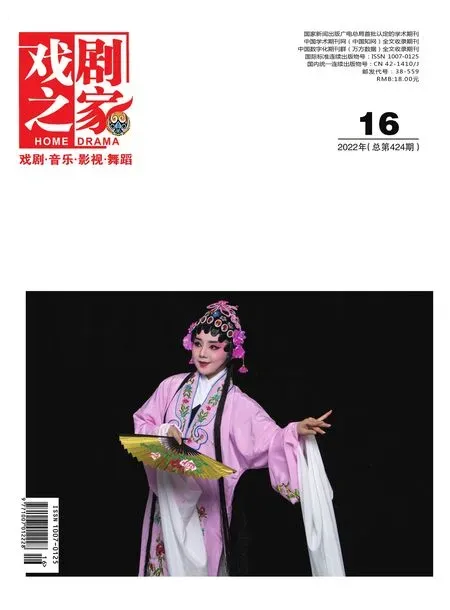韋伯恩《多么快樂》音高組織研究
張欽銘
(鄭州大學 河南 鄭州 450000)
一、韋伯恩《多么快樂》創作背景
安東·弗雷德里克·威廉·馮·韋伯恩(Ant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Webern)是奧地利作曲家,出生于1883 年的維也納的一個小貴族家庭,從小接觸并學習鋼琴和大提琴。在孩提時代他便接觸到了大量的詩歌,受德國哲學家、詩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現代德國派畫家以及德國浪漫主義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的影響。1902 年韋伯恩進入維也納大學開始了正統的音樂課程學習,在那里他學習了音樂學理論、和聲、對位等作曲相關課程,于1906 年完成了音樂學博士課程的學習并取得學位證書。在他的學生生涯里,曾跟隨數位著名的音樂家學習音樂知識,包括圭多·阿德勒和阿諾爾德·勛伯格。勛伯格對韋伯恩的影響是巨大的,他開創的十二音作曲技法激發了韋伯恩對序列音樂的強烈興趣。
韋伯恩生平創作經歷了晚期浪漫主義的有調性音樂,以及中后期他成為勛伯格的學生后開始探索的無調性音樂與十二音音樂。勛伯格的十二音作曲技法放棄調性的運用導致音樂材料無法得到充分擴展,而韋伯恩作為他的學生,可謂站在老師的肩膀上,在勛伯格的十二音音樂創作基礎上對序列音樂進行擴展延伸,最終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對序列音樂的發展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韋伯恩晚期的藝術作品已經能成熟運用后調性音樂的創作技法,他的十二音音樂創作對后世的作曲家產生不小的影響并為西方音樂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韋伯恩的音樂在旋律上具有間斷性的特點,無流暢的旋律線條,以及更多地使用大跳等特點;織體十分節儉,采用不同的樂器和不同的演奏法突出音色的變化;他的音樂主題很少重復。韋伯恩認為:“主題一旦開始,就表現了它所要說的東西,接著就必須出現某些新的東西。”這是延續二十世紀現代派音樂的表現特點。韋伯恩的音樂創作的很多文本都來自詩歌,比如他曾選取斯特凡·喬治的十四首詩進行音樂創作。而《多么快樂》是韋伯恩與詩人希爾德加德·瓊恩(Hildegrad Jone)的友誼的見證。這首以詩歌為文本的聲樂作品是韋伯恩運用十二音符的作曲技術創作而成的。
《多么快樂》創作于1935 年,是安東·韋伯恩《三首歌曲》(Op.25)中的第一首聲樂作品。這是一首通過鋼琴和女高音表達的藝術歌曲,歌詞采用的是希爾德加德·瓊恩的一首詩歌。歌詞的第一部分內容是:“多么快樂!綠色再次圍繞著我,陽光照耀著我!”(How happay I am!Once more all grows green around me,And shines so!)。希爾德伽德·瓊恩的詩歌表達的是一種內向的現代抒情自然詩歌,它充滿了光明、春天和花朵等大自然的景象。韋伯恩將所有這些都轉化為人類的情感和對上帝的幻想。當聽眾仔細聆聽該音樂作品時會發現該作品與傳統音樂作品的音色和織體幾乎完全不同。與傳統有調性的音樂作品相比該作品的音色飄忽不定,織體零散,旋律聲部無連貫性,可聽性較弱。這一特點被后世認為是典型的韋伯恩的作品特點,即“點描法”。“點描法”這一名詞最早來源于19 世紀末繪畫上的一種筆法,即用斑點、圓點來表達明暗對照的效果。由于韋伯恩藝術作品中的旋律、織體在視覺上和聽覺上呈現出零散狀態,像是用點、線、塊兒連接而成,這與美術上的“點描法”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他的這種創作技法被稱為音樂上的“點描法”。
二、《多么快樂》節拍、節奏分析

在韋伯恩的這首聲樂作品中他將傳統意義上的“主題”與“旋律”改變為單音、單個或多個和弦以及多個音級組成的“旋律線條”,產生的音色效果具有切割感,形成點描的藝術特點。營造出這樣的藝術特點可以與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中大量使用半音音階相聯系。
在韋伯恩的《多么快樂》,選自《三首歌曲》(Op.25)的鋼琴伴奏中,從宏觀的角度上看貫穿其中的基本節奏型是由一個十六分三連音,一對八分音符和一個四分的和弦組成。但在微觀的角度上進行分析發現整個節奏進行中每小節都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即節奏型以及節奏型的位置順序發生了變化。譬如在譜例鋼琴伴奏的譜例的第1 小節和第2 小節,緊隨三連音其后的是一對八分音符;第3 小節的這個音型之后不是那對八分音符,而是一個單音。第4 小節中出現兩次十六分三連音,并且開頭的十六分三連音后出現的不僅是一個單音,而且是在一個八分休止符之后;而第4 小節的結尾處與第5 小節的開頭處出現一個長時值的休止,這個長時值的休止加重了音樂的切分感;第6 小節出現兩個四分的和弦;而后第10、11、12 小節的節奏型出現方式也都有不同的變化。整首作品中節奏型位置的不斷變化使鋼琴部分產生了輕微的切分感和不確定感。韋伯恩使用節奏的不穩定發展和不確定進行為音樂附上一種迷離、黑暗的意象,與希爾德伽德·瓊恩的詩歌形成對稱的意象感覺。
三、《多么快樂》的音高材料
(一)音程級
音程級也可以稱為無序音級音程,簡而言之指的是音級之間的最短距離。根據前文談到的節奏型分析,筆者觀察到整首作品中的十六分三連音這個基本音型中的音程級關系有一定的規律,如:開頭第一個十六分三連音是F—F—D,它所形成的音程級是1、3、4,而后第2、3、4、5、7、9、10、12 小節中出現的十六分三連音所形成的音程級都是1、3、4。根據此規律筆者認為《多么快樂》這首作品的創作核心是音程級1、3、4。因此筆者嘗試在整首作品中尋找這種核心凝聚力,發現該作品中每一小節的旋律音與同小節鋼琴伴奏的各音級中都可以構成1、3、4 的音程級。
(二)音程級向量
音程級向量是用來表示音程級出現的次數的一種統計方式,通常指使用一連串無間隔的六位數字來表示具體的音程及含量。根據該作品中出現的音程級1、3、4 可得知其音程級向量是101100。筆者認為在音程級向量101100 中音程級1、3、4 的排列組合總共是24 種,分別是C—C—A、C—D—B、D—D—B、D—E—C、E—F—C、F—F—D、F—G—D、G—G—E、G—A—F、A—A—F、A—B—G、B—C—G、C—C—E、C—D—F、D—D—F、D—E—G、E—F—G、F—F—A、F—G—A、G—G—B、G—A—C、A—A—C、A—B—D、B—C—A。在韋伯恩寫作的《多么快樂》這首歌曲中,他將這24 種排列組合的形態運用到每一小節中,并以交替、重復的形式出現。例如:第2 小節所有的音級中旋律與鋼琴伴奏之間的音程關系是G—E—D,E—D—F,F—F—D,C—D—F,D—B—B,在這一小節中每個音級都按照以上的24 種固定形態出現在屬于自己的排列組合方式中。再如:第11 小節的A—G—C,G—B—B,C—A—B 的三音形態。而《多么快樂》整首歌曲中不只是這兩個小節的排列方式如此,每一小節的每個音級都可以與另外兩個音級構成音程級向量101100 的形態。
研究到此時,筆者發現所有的三音音型構成的都是相同的音程級和音程級向量,并且無論是橫向發展的旋律音和鋼琴伴奏音還是縱向混合的旋律音與鋼琴伴奏音,它們之間的音程級關系都與101100 這個音程級向量密不可分。在韋伯恩的《多么快樂》中,以每小節為單位,其中任意一個音級都可以在以音程級向量101100 所構成的24 種排列組合形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筆者認為研究后調性音樂有一種趣味性,后調性音樂的魔力在于可以通過運用數學計算、設計出音高,并且通過相對科學、嚴謹的排列組合與嚴格的結構方式推動整首作品的發展進行,使用十分理性化的思維進行音樂創作。這樣的創作技法雖然令觀眾暫時捉摸不透音樂的下一步該如何發展,但是作品的內部形態卻存在其潛藏的嚴謹規律。這種寫作方式也為此音樂欣賞添加了一種神秘莫測的色彩。但若只通過音程級與音程級向量對后調性音樂作品進行分析,難免不能同傳統音樂一般做到具體、完善的分析,因此下文筆者將以序列為單位,以十二音音樂體系的創作技法對《多么快樂》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三)十二音序列
上述通過后調性音樂理論中概念性的音程關系對韋伯恩《多么快樂》的音高進行了簡要分析,接下來筆者將從十二音序列音樂的層面對該藝術歌曲進行邏輯分析。十二音音樂也可以說是序列音樂的一種,通常由12 個半音組成,其原型在每個半音全部出現之前不重復任意一音。構成十二音音樂一般以原型(P)、逆行(R)、倒影(I)、逆行倒影(RI)四種形式出現。任何序列音樂都是由48 種序列形式組成,即由12 個原型、12 個逆行、12 個倒影、12 個逆行倒影組成。在本文的圖表2 中,筆者使用十二音計數的方法對作品中的十二音序列進行標記,使讀者對于韋伯恩的十二音作品排列有更直觀、清晰的了解。
在《多么快樂》,選自《三首歌曲》(Op.25)作品中,韋伯恩使用了48 序列矩陣中的其中一種原型及此原型的倒影、逆行倒影進行排列其音高的結構。該作品的原型(P)是從旋律音開始的第一個音至第十二個音所構成,即:G、E、D、F、C、F、D、B、B、C、A、G,該序列是從G 音開始,G 的音級是數字標記7,因此它的原型用P來表示。從《多么快樂》的伴奏音列來看,第一個音至第十二個音分別是:F、F、D、E、E、C、A、C、G、B、B、G,由該序列中各音級之間的有序音級音程可得出此序列是P的逆行倒影(RI)。此外,該作品中使用的倒影序列(I)是:G、B、B、G、C、A、C、E、E、D、F、F。十二音作品的結構與傳統音樂的曲式分析的結構方式不同,筆者通過十二音序列對韋伯恩《多么快樂》進行結構上的分析。在這首簡短的聲樂作品中,韋伯恩在旋律線上采用P、I、RI的順序,在鋼琴伴奏上的結構運用RI、P、RI的順序進行寫作。該作品的主要核心凝聚力來自P序列。
四、結語
韋伯恩的音樂創作共經歷了三次改變,分別是從他完全放棄調性音樂的創作,開始使用無調性的音樂方式創作簡短的作品;將歌曲的創作與他的樂團分散部分的結合;完全掌握十二音作曲技術的手法,開始對作品進行擴展創作。
本文通過對安東·韋伯恩的聲樂作品《多么快樂》,選自《三首歌曲》(Op.25)的分析,筆者認為后調性音樂中存在眾多理性因素,作曲家使用無調性音樂、序列音樂、后調性音樂理論中的音程關系構建出的音樂作品,其內部形態是無比豐富的。在這首簡潔、短小的聲樂作品中,韋伯恩使用了無序和有序的方式,在此的無序指的是音程級與音程級向量等,有序指的是十二音序列體系。十二音序列確定了這首作品的結構輪廓,而音程級與音程級向量更能凸顯音程之間的相互關系。韋伯恩在這首作品中的核心凝聚力運用了音程級1、3、4,音程級向量101100 和十二音序列P。音程級向量101100 確定了整首作品的旋律與鋼琴伴奏的音高,P序列明確了該作品的結構,加之韋伯恩運用他典型的“點描派”方法為其創建獨特的節奏,由此展現出韋伯恩自己成熟的創作風格。
注釋:
①David Ewen:The World of Twentieth Century Music,Prentice Hall Inc.,New Jersey,p.894.轉引自鐘子林《西方現代音樂概述》第23 頁,人民音樂出版社。
②約瑟夫·內森·施特勞斯.后調性理論導論(第三版)[M].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