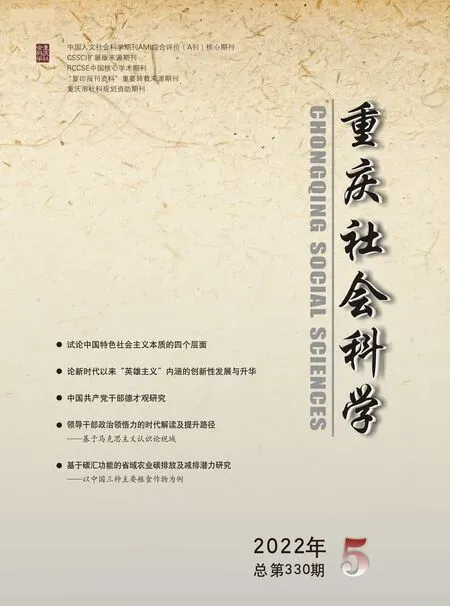制度邏輯理論建構:基本原則與整體模型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yōu)勢……把我國制度優(yōu)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證。”
要將國家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最關鍵的是把握制度邏輯的理論建構。在一個多重制度系統(tǒng)中,個體與組織行動者是如何被制度影響的,尤其是當他們身處于國家、市場、社會、家庭的多重制度秩序之下時,他們又是如何被多重制度場域所影響的,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作為一個分析框架的制度邏輯,可以用于分析制度、個體和組織在社會系統(tǒng)中的相互關系。本文主要闡述制度邏輯視角的核心構想,以期引導具有共同興趣的學者們開發(fā)出新的理論性與經驗性研究成果。
2.2 兩組患者的盆腔疼痛緩解及復發(fā)情況比較 聯合組患者的盆腔疼痛緩解率顯著高于單獨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5.02,P<0.05),復發(fā)率顯著低于單獨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7.38,P<0.05)。見表3。
一、相關研究綜述
制度邏輯視角(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是組織和管理學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視角之一。尤其是近年來,基于制度邏輯視角的學術研究數量呈指數型增長,并且被跨學科地應用于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多個領域的學者從不同層面,如場域層面、組織層面和個人層面持續(xù)進行研究
。已有研究在概念內涵上逐步形成了共識:制度邏輯作為指導場域行為者的基本規(guī)制,涉及在組織場域中占優(yōu)勢的信念系統(tǒng)和相關的實踐活動
。追本溯源,制度邏輯這一理論視角發(fā)跡于新制度主義理論,卻又截然不同于新制度主義理論,從而翻開了制度分析的新篇章。這一理論視角批判新制度主義理論未能將“行動者”(actors)置于社會語境,并對理性選擇理論進行重新解讀,揭示出“理性的意義將根據制度秩序而變化——在市場的范圍內,人們通過自利(self-interest)構建意義;但是在專業(yè)(professions)的影響下,自利不完全是意義構建的透鏡,還需考慮個人名譽、專業(yè)能力以及技藝的水平”
。由此,學者們普遍將制度邏輯定義為“一種由社會構建的、關于文化象征與物質實踐(包括假設、價值觀和信念)的歷史模式”
。
基于現有對制度邏輯的界定和認知,研究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組織所處場域的制度邏輯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邏輯共存或互相競爭主導權的事實。在此基礎上,一些研究者圍繞多重制度邏輯對組織行為的影響展開了研究。多重制度邏輯視角可以揭示出:社會網絡理論為什么無法解釋人們?yōu)楹伪舜寺摻Y,以及資源為什么不具備普適的效應。可以說,資源將根據多重制度秩序(institutional orders)而變化,而自利與理性并不能普遍適用于各種制度環(huán)境。究其根本,制度邏輯所關注的正是自利與理性如何被抵消或調節(jié),從而使人們意識到,盡管市場是一種制度,卻不能完全支配專業(yè)性。而且,個體或組織可以感知到(哪怕是在潛意識里)不同制度秩序下文化規(guī)范、象征與實踐的不同之處,并將此多樣性融入自身的思想、信念與決策。換言之,“不同制度邏輯之間具有兼容性和互補性及其作用邊界”
,行動者的能動性(clynamic role)將根據多重制度秩序而變化。隨著制度變遷和場域結構變化,組織原有的結構、文化和行為可能不再適用于現有的制度邏輯要求,而競爭性邏輯的出現致使組織采取不同的戰(zhàn)略響應行 為
。
多重制度邏輯理論把組織所面臨的制度環(huán)境視為由兼有互補與沖突關系的多種制度邏輯構成的復雜制度環(huán)境
,社會被看作多重制度秩序的建構,這一視角可以幫助更廣泛地理解各種組織形式。作為一個理論模型,多重制度系統(tǒng)(multiple institutional system)
中的每一項制度秩序都展現出獨特的組織原則、實踐和象征,進而影響著個體和組織的行為。制度邏輯為行動者們提供了參考框架,這影響著他們對意義的構建,影響著他們用來激勵行動的語匯(vocabulary),并對他們的自我感覺(sense of self)和身份(identity)有調節(jié)作用。每一項制度秩序的原則、實踐和象征都以不盡相同的方式塑造著個體和組織演繹推理、感知與體驗理性的路徑,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遵循制度理論到制度實踐再到制度理論的發(fā)展規(guī)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于我國社會的實際,在不斷吸收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治理智慧與借鑒世界優(yōu)秀制度文明成果的基礎上而形成。可以說,“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以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探索為基礎,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理論成果,并以此推動中國的持續(xù)性發(fā)展”
。
二、制度邏輯視角的基本原則
制度邏輯視角的四項基本原則:社會結構與行動的定向戰(zhàn)略,制度既有物質性又有象征性,制度的歷史權變性,以及制度具有多重分析層級。
塌陷區(qū)淺部巖溶較發(fā)育,自然狀態(tài)下巖溶地下水水位埋深一般為1~3 m,地下水與地表水的水力聯系較密切,地下水動態(tài)受降水影響,隨季節(jié)變化,變幅1~3 m。2017年10月14日塌陷區(qū)西北角礦硐(約200 m)內發(fā)生透水事故,導致塌陷區(qū)域地下水在短時間內快速下降,破壞了原有的平衡狀態(tài),是形成地面塌陷的誘發(fā)原因。
近些年,高中單親家庭子女的數量有大幅增長趨勢。單親家庭子女在學習、品德方面不乏有出類拔萃者,但大多數表現較落后,成為班級工作的難點。如何做好單親家庭子女的心理教育工作,已經成為學校、家庭乃至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
(一)社會結構與行動的定向戰(zhàn)略
制度邏輯視角的一個核心假定是:個體與組織的使命、性質、價值觀都嵌入(embedded)制度邏輯。這一假定使得制度邏輯視角既與那些強調結構凌駕于行動之上的宏觀結構視角區(qū)分開來,又與那些把制度與經濟或技術割裂開來的帕森斯式視角劃清界限。社會科學史上有一項歷史悠久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強調社會結構束縛了行動;另一方面,關注個體與組織如何通過他們的行動創(chuàng)造、維護并改變制度。這里用行動(actions)這個詞指代了“能動性”這個概念。能動性是行動者對這個社會產生一定影響的能力,例如,改變規(guī)則、社會關系或資源分配的能力。正如實踐所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領導一切、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線的國家制度”
,一方面,可以保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最大限度地代表和體現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提出明確的現代化目標,制定科學的現代化規(guī)劃,實現資源優(yōu)化配置,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yōu)勢。
在探討制度邏輯視角之前,有必要強調那些曾促進理論發(fā)展來解決社會結構和行動這一理論性兩難困境的定向戰(zhàn)略。所謂定向戰(zhàn)略是一種元理論結構,它由一系列有關行動者、行動與秩序的相互關聯的假設和概念所構成。制度邏輯視角作為一種定向戰(zhàn)略,解釋了行動者在社會結構中的關鍵性差異在于“部分自治性”(partial autonomy)。而正是這種“部分自治性”解釋了制度如何既約束又促進個體與組織的行動,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關于制度穩(wěn)定性與制度變遷的理論,這也是制度邏輯視角的核心議題之一。
制度邏輯視角的關鍵原則之一在于,社會中的每一項制度秩序都具有物質元素以及象征元素。所謂制度的物質元素,指的是結構與實踐;象征元素,指的則是思想與意義。象征元素與物質元素是互相交織、相互構成的。象征元素是在結構和實踐中體現的,而結構和實踐則表達和影響了象征元素。這并不意味著二者無法在分析層面上互相分離,實際上,即使相同的結構與實踐可能涉及著不同的行動者,并因此產生不同的效應。例如,雖然市場一般不被認為是文化領域的一部分,但它是直接被社會關系網絡、權力、地位等文化和社會結構所塑造的。同樣地,雖然家庭或宗教通常不被認為是經濟領域的一部分,但二者直接牽扯到了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再分配與消費。而且,象征元素并不是恒定的,其思想與意義從來不曾為一個既定的語言系統(tǒng)所完全決定。恰恰相反,象征元素總是能夠打破語境,獲取不同內涵。
第二種定向戰(zhàn)略來自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涉及社會結構與能動性的二元性。根據結構化理論,社會結構由規(guī)則、資源和實踐構成,同時是社會生活的實施(enactment)和繁衍的產物與平臺。這一理論構建了遞歸相互依賴模型(recursive interdependent model),這一模型同時將社會結構的根源和社會變革的起源理論化。
當掃描到塊px,y時,已經完成了對塊px-1,y-1、px,y-1、px-1,y的初步標記,假設其標號依次為Label[x-1,y-1]、Label[x,y-1]、Label[x-1,y],則塊px,y的標號Label[x,y]可表示為式(3):
盡管結構化理論闡釋出行動者具有見識、反思意識和自主性,但卻并未闡明什么影響了行動者對于自利性與理性、權力和癖性的認知框架。既然行動者采納的規(guī)則和資源并不單一,那么什么樣的規(guī)則會被他們選擇,什么樣的資源又會被他們關注呢?行動者會對自身或他人的行為賦予什么樣的意義?總而言之,結構與行動相互塑形這一觀點的界限并不清晰。為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系統(tǒng)之下理解結構化理論,結構化理論中缺少對社會系統(tǒng)的概念化,而且,這一理論僅僅假設資源被用于增強和維護權力。相比而言,制度邏輯視角則闡明:個體在多重制度系統(tǒng)中的位置,將影響他們使用權力來表達自身利益的目的、方式以及含義。盡管結構化理論的某些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即實踐理論的必要性,以及能動性與結構的二元性,但這一理論并未通過系統(tǒng)的經驗性研究而跨越抽象層面。相比而言,制度邏輯視角則在社會系統(tǒng)的三個層級中,即組織場域、制度場域和社會場域,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作為對新制度主義理論中所缺乏的能動性理論的回應,可以把觀念與利益相聯系,進而開發(fā)第三種定向戰(zhàn)略∶“制度創(chuàng)業(yè)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或譯為“制度創(chuàng)業(yè)”)。“制度創(chuàng)業(yè)者”在塑造文化的制度化過程中表達自身能動性。例如,制度創(chuàng)業(yè)者會通過講故事、修辭戰(zhàn)略,以及宏觀的文化話語來操縱文化象征與實踐。然而,關于“制度創(chuàng)業(yè)者”的研究者們因為過度使用案例研究來描述那些不受約束的制度創(chuàng)業(yè)者如何恣意操縱制度而廣受詬病。而且缺少相關理論研究來解釋制度創(chuàng)業(yè)者如何認識到自身利益,又如何嵌入(或獨立于)那些促使他們產生文化象征與實踐的社會系統(tǒng)之中。
第四種定向戰(zhàn)略來自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的“文化工具箱”概念,即個體如何把文化當作“工具箱”(toolkit)來使用。從“文化作為工具箱”的角度來思考,便不難理解為什么人們的觀念如出一轍,行為選擇卻各不相同,因為行為選擇取決于行動當下的緊迫程度、個人價值觀以及多重制度系統(tǒng)。“文化工具箱”解構了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唯意志行動理論(theory of voluntary action)。按照此理論,社會系統(tǒng)由價值取向構成,而個體則通過社會化過程將價值取向變成內在特質。由此,價值觀便得以引導個體做出相應的選擇。文化通過價值觀影響了行動;價值觀使行動者轉向某些特定的目的。然而,文化或價值觀并不一定是行動的預期。實際上,“文化工具箱”包含一種對行動困境的不同解釋,其認為文化是支離破碎的,并非如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認為的那樣鐵板一塊。而問題在于“如何將工具箱概念與制度邏輯的元理論相聯結,而這樣做又有什么意義”
,對此,多重制度系統(tǒng)提供一種具有可分解性的文化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個體和組織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獲取文化的片段或類別元素(categorical elements),將之運用于新的社會情境,從而滿足特定的局部環(huán)境中的實際需求。從這個意義看,“文化工具箱”也有局限性,相較于制度邏輯視角,它未能較好地解釋規(guī)范與價值觀是如何塑造行動的;對于使用“文化工具箱”概念的學者而言,價值觀所扮演的角色無非是為行動提供正當理由(justification)而非道德動機(moral motivation)。
從各個方面來考慮,nRF401集成度比較高,實際問題上研究起來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芯片內部集成的高頻發(fā)射、高頻接收、PLL合成、FSK 調制、FSK解調、多頻道切換等功能,我們可以通過軟件將其實現的更好。
(二)制度的物質性與象征性
第一種定向戰(zhàn)略來自結構性同構理論,涉及三種同構形態(tài)(即模仿性同構、規(guī)范性同構和強制性同構)。其中,模仿性同構、規(guī)范性同構符合結構主義的觀點,即社會關系是模式化的,并且束縛著個體與組織的自主性;強制性同構蘊含著某種能動性理論(比如監(jiān)管機構),而非僅僅關乎一致性或習慣性行為。實際上,新制度主義理論主要強調了社會結構的連續(xù)性及其對行動者的束縛。這一觀點與經濟學和政治學中基于理性的博弈論模型截然不同
。因此,新制度主義理論無法解釋能動性,而制度邏輯視角則解釋了個體和組織如何能夠掌握并依據不同的理性觀念來行動,以及行為戰(zhàn)略如何在根本上與這種行動能力相關聯。多重制度系統(tǒng)中各項元素的近似可分解性(near-decomposability)就是一個答案(盡管并不完善),即每一項制度秩序都有屬于自身的理性觀念。
武器系統(tǒng)的各組成單元(指控車、雷達、導彈發(fā)射車等)使用高穩(wěn)定的晶振作為本地時鐘源,利用北斗、GPS秒脈沖來同步這個本地時鐘,實現了整個武器系統(tǒng)的時間統(tǒng)一和同步。文中所述同步設計有借鑒意義,可推廣應用至對時間有同步要求的系統(tǒng)和設備。所述抗干擾措施,在工程設計中具有普遍參考價值,其中首次應用的秒脈沖時間軸開窗保護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有效地解決了秒脈沖抗干擾保護,擬推廣應用于新型號雷達的時間同步設計。
制度邏輯視角同時考量了物質層面和象征層面的動態(tài),這便是制度邏輯視角與早期新制度理論的關鍵差別。但是,這并不是要倡導一種將文化象征與物質結構混合在一起的研究話語,抑或是在元理論的層面上把兩者混為一談。恰恰相反,制度邏輯視角開發(fā)一種理論和方法論工具,使得研究者們能夠把象征效應從結構效應中分割出來,從而更好地理解因果順序與運作機制。在同時考量物質元素和象征元素時,還有一個方面很重要,那就是,如果忽視制度的象征層面,將很難對制度的異質性和制度變遷進行理論化,因為社會實踐的制度化正意味著其獲得了集體意義(collective meaning)
。這是因為“物質實踐首先是通過象征的形式表現出來并傳播開來的,理論化(theorization)便是一種播散(diffusion)機制”
。但是,如何把理論的各個片段和各個層級聯結起來呢?制度邏輯視角通過結合象征元素與物質元素,把有關文化和認知的研究綜合在一起,進而提供了一種定向戰(zhàn)略,以支撐這項關于文化如何塑造行動的理論。
(三)制度的歷史權變性
制度邏輯視角假定制度是具有歷史權變性的。許多關于社會或經濟現象的相關研究結論,僅僅是在某一特定時期確鑿有效。對此,約翰·撒頓(Sutton,John R)等人根據大量樣本數據研究結果,做出了制度具有歷史權變性的判斷,并指出“利潤與債務這些常用術語的定義會隨著會計程序與稅法的改變而變化,因為這些概念都受到更廣闊的社會變革的影響”
。這一研究所使用的有關規(guī)章制度的案例,不僅提到新的立法,還提到現有法律的內在靈活性——這在各個歷史時期內對同一法律的不同解讀上得以體現。“許多法律是模糊的,甚至是具有爭議的,但也因此為集體性的意義建構留下了機會”
。例如,法律解讀的動態(tài)變化已經在制度理論中被廣泛記載。正如一項關于申訴程序法(grievance-procedure laws)的研究所表明的,“法律的內容和含義是由它理當監(jiān)管的社會場域所決定的”
。
正如經驗性研究所指出的,多重制度系統(tǒng)中各項制度秩序的重要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的演化而變化的。在現代社會中更具影響力的通常是國家邏輯、專業(yè)邏輯、公司邏輯和市場邏輯。尤其是市場邏輯,其影響在過去幾十年里日益突出。但是,任何一項制度秩序的相對重要性都不總是受到科學化(scientization)或市場理性化(market rationalization)的驅動而漸進地、線性地前行。雖然只有很少的研究關注這一話題,但初步證據顯示:“一項制度秩序的影響力并不一定完全地替代另一項制度秩序的影響力。”
學者們通過案例研究分別在會計行業(yè)和建筑行業(yè)發(fā)現了“制度邏輯在歷史變革中的周期模式和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
。沿著這個思路,制度邏輯研究考察了反邏輯(counter logics)如何在相互競爭的制度秩序間制造對立的張力、遏制整體性的制度變遷,從而建立起一個新的平衡或系統(tǒng)穩(wěn)定期。例如,一項對銀行業(yè)的研究發(fā)現,舊的制度秩序——社區(qū)邏輯再度興起,制造了一種針對市場邏輯的反抗力量
。其他領域研究中也涉及歷史權變性的周期模式,例如,在基因科學領域,我們看到人們如何在互相沖突的學術邏輯(專業(yè)邏輯)和商業(yè)邏輯(市場與公司邏輯)之間行動;在醫(yī)學教育領域,人們如何面對科學邏輯與護理專業(yè)邏輯之間的矛盾。可見,制度邏輯在變遷過程中的歷史權變性是相對新穎且亟待探索的議題。為了構建關于制度變遷與制度穩(wěn)定性的理論,在元理論層面闡釋清楚制度的歷史權變性是必不可少的。制度邏輯視角的研究目標并不在于開發(fā)有關行為和結構的普適理論,而在于發(fā)展在理論中連接因果并隨著時間展開的關鍵性元素——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s)。任何對社會機制的研究都必須建立在既跨越歷史時段又跨越分析層級的長期觀察基礎之上。
(四)制度的多重分析層級
制度邏輯視角假定制度在多個分析層級(包括個體、組織、場域和社會)上運作,而行動者嵌套在較高的層級之中。這一假設符合經驗性研究結論,即制度既是互相沖突的,同時又為行動者帶來約束和機會。如果接受這一假設,研究者就必須在構建理論時闡明社會機制如何既在分析層面上具有差異性,又在一定的條件下允許行動者與情境結合或分離。換言之,到底是行動者改變了,還是結構改變了?什么是跨層級的相互作用?如果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那么研究者必須識別那些連接因果的社會機制,以及這些社會機制如何在不同的多個分析層級(包括個體、組織、場域和社會)之中運作;一旦把這些分析清楚,這一理論就會變得更精確且更全面。
2.3 拔管時間與術后睜眼時間 兩組拔管時間、術后睜眼時間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3。
社會機制可以被定義為研究者所構建的一種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用以考察、理解和構建一項有關現實(reality)的理論。至于虛擬與現實之間的擬合優(yōu)度(goodness of fit),可以通過比較社會機制的推論與事實來決定。為了進行這一比較,相關研究者在構建理論時,制造了一種被稱為機制的裝置,用以推斷將來的結果。機制具備兩種抽象的元素:其一是對行動者的具體說明(specification);其二是對行動者所在的結構的具體說明。例如,關于能動性的機制可以體現行動者的差異;反之,其也可以體現社會結構中不同位置的差異,如此一來,行動者就具有相互替代性了
。
自從制度邏輯理論構建以來,組織身份與實踐成為重要概念。對于許多社會理論學者來說,組織身份與實踐將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包括制度邏輯)與個體或組織的行動聯系起來。
三、整體模型:組織身份與實踐的動態(tài)分析
新制度主義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文化轉向”時代。當新制度主義傾向于研究組織系統(tǒng)(例如行業(yè)與場域)時,關于組織身份與實踐的相應研究開始蓬勃發(fā)展。盡管如此,雖然關于新制度主義理論的研究中經常出現組織身份和實踐的概念,但是這些概念通常都是“黑匣子”。組織身份主要限于集體身份,并被視為靜態(tài)且具有約束性的特征,以此來區(qū)分各種組織形態(tài)。同樣,實踐主要被作為在組織群體中制度化的靜態(tài)元素。基于此限制性,許多學者呼吁研究行動者在創(chuàng)造與傳播組織身份和實踐方面的作用。對此,制度邏輯視角提供了一種嵌入能動性方法,用于在更廣泛的文化結構中確定行動者的組織身份和實踐,而這些文化結構同時也推動和約束著行動者的組織身份和實踐。例如,與商品和服務交換相關的組織身份與實踐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這取決于它們是否更多地被市場、國家或社區(qū)邏輯影響。鑒于組織身份與實踐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不斷變化和更替的,研究組織身份與實踐的動態(tài)性對于理解制度邏輯的穩(wěn)定性和變遷非常重要。
(一)制度邏輯理論構建的微觀基礎
支撐制度邏輯視角的元理論圍繞著多重制度系統(tǒng)這一概念而發(fā)展:元理論假設制度是在多個分析層級中運轉的,因此可能具備跨層級的相互作用。制度邏輯視角將多重制度系統(tǒng)展現為一個理想型(ideal type),這有助于研究者把社會科學的經驗性觀察轉變?yōu)闄C制,從而在分析層面上使機制之間的結合和分解變得截然不同。這一點是關鍵的,因為研究者對分析層級的選擇往往是先行的,這將決定他對研究問題、分析工具的選擇,因此決定著最終研究結果。由此,那些結合多個分析層級的研究者們更可能觀察到準確的圖景,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機制的運作,以及制度邏輯之間的固有矛盾。多重制度系統(tǒng)和相互嵌套的分析層級的意義,就在于抵抗當時在社會學、經濟學與組織理論中盛行的功能主義和共識論。
1.組織身份與實踐
制度邏輯視角為行動者提供了在社會互動中用來改變組織身份的象征元素。當然,即使存在一系列可獲取的多重制度邏輯,由于行動者的經驗以及所處的制度場域不同,某些制度邏輯在認知上更易于(或更難于)為行動者所利用。一個關鍵前提在于,制度邏輯與組織身份在根本上是相互關聯的。組織身份的變化可能是由特定環(huán)境中的多重制度邏輯的不穩(wěn)定所引發(fā)的,并導致對組織身份的模糊性,進而匯集行動者的注意力并催生旨在解決模糊性的社會互動。如何引導注意力聚焦集體身份、角色和基模,社會互動提供了催生組織身份改變的關鍵動力。然而,這種社會互動往往相當復雜,并且涉及三種動力機制,如前文所述,社會互動的動力機制包括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決策聚焦于注意力如何被引導的過程,以及如何與決策情境中的解決方案相匹配;意義構建是指持續(xù)進行的、回顧性的、理性化組織行為的過程,其通過交流與敘事來解決組織身份的模糊性
;集體動員涉及一系列機制,行動者通過這些機制產生共同承諾。制度邏輯視角構建了兩個過程模型來指導對組織內和組織間的實踐和身份的動態(tài)分析。在此基礎之上,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這三個機制發(fā)揮著關鍵作用,從而將社會互動與更廣泛的重構或變革組織身份的實踐聯系起來。
在制度邏輯視角中,實踐是指相對有條理的且確定的、具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形式或行動集合。對此,要將實踐與活動(activity)進行區(qū)分。活動指的是更普通的行為或日常工作,而實踐指的是由更廣泛的文化信仰所塑造的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活動涉及的行為通常缺乏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或反思,比如釘釘子;而實踐,例如專業(yè)木工,為一系列平常的活動提供了秩序與意義。”
雖然許多關于實踐的相關研究聚焦于人類學領域,但許多從組織和管理學角度展開的社會動態(tài)方面的實證研究,也聚焦于個體行為、制度工作等實踐領域。
迄今的大多數研究成果都未能有效地分析制度如何塑造行動者的組織身份與實踐,以及如何又被行動者所塑造。制度邏輯視角則強調了分析層級的嵌套性,并認為個體和組織的行為總是嵌套在社會環(huán)境中且受其影響。例如,政治儀式既是人們建立象征系統(tǒng)的方式,也是一種制度化的手段。制度邏輯也為組織、團體和個體的身份與實踐提供了重要基礎。盡管制度邏輯為特定情況下如何行動提供了指導,但組織身份的概念更側重于“我們是誰”。
關于制度邏輯與組織身份之間關系的研究文獻主要聚焦于兩個研究分支。一個研究分支主要側重于組織內部動態(tài),強調單個組織的身份是獨特的,并可以通過識別持久的組織屬性來理解。當然,組織由多樣化的個體、群體構成,因此,對組織身份的深入研究在多重制度層級上認識到身份的復雜性。相關研究闡釋了行動者如何修飾或改變身份,從而解決所面臨的多重制度層級之間的張力。另一個研究分支更具宏觀性和關系性,強調組織如何通過共享認知和規(guī)范導向而變得相似。組織身份是指圍繞著共同目標戰(zhàn)略性地構建和組織起來,且具有靈活性的行動者群體或行動者類別。行動者提出對組織身份的具體理解,將這種理解與特定制度邏輯或實踐聯系起來,并努力吸引潛在的支持者。
2.三種動力機制∶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
“文化工具箱”并沒有為動機提供深刻的理論依據,相關闡釋也缺乏動力機制。雖然“文化工具箱”概念可以與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聯系在一起,并考察行動如何依賴于環(huán)境中的情境線索(situational cues),但這卻往往把關于行動的動力機制排除在個體之外。而從制度邏輯視角來看,研究社會結構與行動的關鍵并不是把理性行動者與非理性行動者進行二分對立。相反,研究目標應是考察行動如何依賴于不同制度秩序對個體和組織進行定位和影響。這是因為每一種制度秩序都有其獨特的理性觀念。關于社會結構和行動,以及嵌入能動性(embedded agency)的話題一直是研究焦點。對此,制度邏輯視角深入討論如何通過多重制度系統(tǒng)中各項制度秩序的互相依賴性和“部分自治性”來將結構和行動理論化,并不斷對其進行測量。
在社會互動中,行動者依靠制度邏輯來繁衍及轉變組織身份和實踐。組織身份和實踐是如何產生、繁衍或轉變的?以往研究中考察過社會互動的三種動力機制∶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這三種動力機制直接參與了從微觀到宏觀形成組織身份與實踐的過程。
第三,法治觀念、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意識較為薄弱。因受法律法規(guī)宣傳力度不強因素的影響,一部分單位、部分、個人對生態(tài)建設的認識程度有待強化,尚未將生態(tài)建設深入到自身的思想觀念當中,使得執(zhí)法不嚴、有法不依的現象屢見不鮮。
一是關于決策。卡內基學派在傳統(tǒng)組織研究中將決策置于闡釋管理過程(例如決策規(guī)則、績效計劃和常規(guī))的中心位置。這一視角主要是側重用人類處理信息的注意力局限性來解釋行為
。但是,卡內基學派忽視了社會行動者的文化(和結構)嵌入。實際上,通過分析集體身份、角色和基模如何調控注意力焦點,可以把制度邏輯視角納入決策模型當中。制度邏輯能夠影響關于運營、高管更替、收購、公司結構以及董事會改革的決策。這一研究視角能夠闡釋行動和行為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影響可能超出了決策所涉及的社會互動。例如,選擇M型組織結構會對整個管理過程產生影響,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進而影響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互動。但是,決策具有模糊性,最初的決策只是部分地決定了由諸多決策交織而成的復雜網絡。因此,決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對于管理過程也產生很大影響。
二是意義構建。意義構建是社會行動者將環(huán)境(circumstances)轉化為可以用語言明確理解的、作為行動跳板的情境(situations)的過程。意義構建是一個持續(xù)的、回顧性的過程,其合理化了組織行為。但是,意義構建也具有前瞻性,通過交流和敘事,它體現了使組織和制度得以存在的身份和類別。可以說,“意義構建是通往自愿共建和協調的行動系統(tǒng)之路上的一個停靠站”
。制度邏輯是意義構建的構成要素,而意義構建也是制度邏輯得以轉型的機制。在某種程度上,語言和語匯在意義構建中具有一定作用。制度邏輯制定了一套用于理解環(huán)境的專門語匯。語匯的變化也表明了制度邏輯的變化。例如,在醫(yī)療衛(wèi)生行業(yè)中,通過意義構建的過程,曾經代表一種組織形式的“管理式照護”一詞逐漸描繪出整個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的一個特性
。
三是集體動員。集體動員是行動者獲取象征性和物質性資源并激勵人們實現團體或集體目標的過程。集體動員這一概念最初來自社會運動學派,所關注的是一種被剝奪感或不平等感驅使的群體。在此之后,集體動員被視為由集體行動所驅動。更廣泛地說,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影響使得社會行動者在實現集體目標的過程中共同抵制現狀。對集體動員的相關研究借鑒了社會學中廣泛且成熟的社會運動文獻,從而發(fā)展出一種研究能動性的、理解行動者及其行為的制度嵌入的精妙方法。對集體行動的研究從聚焦單一的、強有力的行動者,轉向了聚焦制度語境如何促使行動者質疑現有制度安排,或者促使行動者催生變革思想或采取行動,以及場域內的多重制度邏輯如何催生集體行動。組織身份轉變是由更廣泛的集體動員所推動的。集體動員往往被視為制度變遷的機制。行動者通過批判組織身份的約束性,以及采取一系列方法來提高行動自主權,并促進制度邏輯的轉變。集體動員為特定場域中的行動者提供了可獲取的新制度邏輯。可以說,集體動員是將制度邏輯與實踐的動力機制相連接的關鍵機制。
四是加大了找水、打井的力度。西南五省新打抗旱水源井1.8萬眼,購置運送水車7615輛,應急調水6000多萬m3,累計為群眾送水941萬t,新建抗旱應急調水工程4307處,新建五小水利工程7萬多處,鋪設輸水管道2萬多km。
3.社會互動與組織身份變化
雖然制度邏輯塑造了集體和個體的組織身份,但是組織身份的轉變也可以催化制度邏輯的變遷,二者往往是同時發(fā)生的。研究社會互動的影響和動態(tài)性(mutability)需要同時關注二者。實際上,制度邏輯與組織身份是松散耦合的。至于制度邏輯如何變遷,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與組織身份的變化相關聯?組織身份的改變將如何促進制度邏輯的變遷或重構?關于復雜的社會互動(包括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是如何調解制度邏輯與組織身份動態(tài)之間的關系的?這都是有待研究的理論問題,也需要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
例句:I used to come home and act out the movie for the kids.
阿東忙碌時,阿里便坐在一張小凳上看著。他問:“姆媽呢?”阿里每年都是這樣坐著看母親收撿,他不明白,今年做這些事的怎么是阿東?
(二)多層級制度中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分析
制度邏輯理論構建對于組織內部或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分析具有實用性,這體現在可以揭示特定組織如何在多重制度邏輯下影響行動者的實踐與身份。關于此方面的相關分析,仍然是一個前景廣闊的研究領域。
1.組織內部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分析
制度邏輯視角勾勒出一套研究方法,可以用于研究組織內部的實踐和身份動態(tài),且不忽視塑造組織內部行為者的能動性。舊制度主義理論聚焦于單個組織的影響力、同盟、權力、非正式結構和價值觀,新制度主義理論關注于外部的制度化過程,而忽視了組織的獨特性,以及對特定組織的深度分析。當前,一些學者開始要求新舊制度主義的融合,這種方式闡釋了制度語境以及行動者的重要性。例如,羅蘭·蘇德比(Suddaby,R.)與羅蘭·格林伍德(R.Greenwood)構建了一個研究組織變遷的框架,并強調“不僅需要考慮組織外部的制度壓力,還需要考慮與利益、價值觀、權力依賴和行動能力相關的組織內部的內生動態(tài)”
。這需要關注行動者(組織與個體)及其在官僚結構、地位差異、非正式網絡,以及職業(yè)和專業(yè)承諾的語境下的社會互動。簡言之,“邏輯不是純粹自上而下的。行動者在真實語境下,如果自身擁有過去的經驗,便會考慮它們,質疑它們,將它們與來自其他領域的制度邏輯相結合,從它們當中取得他們所能獲取的,并使它們適應他們的需求”
。
以上研究成果為更系統(tǒng)的制度邏輯理論構建提供了良好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可以建構一個理論導向的過程模型(圖1),揭示出制度邏輯如何與組織內部的實踐和身份動態(tài)相關聯,并得出結論:組織內部的實踐和身份都受到該組織在(一個或多個)制度場域中所處的情境的影響。每個制度場域都包括一個或多個可獲取的制度邏輯,以及一系列組織身份與實踐。換言之,每個制度場域可能都有一條獨特的X軸表示制度秩序的集合和一條獨特的Y軸表示象征元素的集合。一個組織隸屬于多個制度場域的復雜程度決定了實踐與身份的特性,并催生對更多樣化的制度壓力進行管理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具有多重制度邏輯的特定制度場域中,組織之間的差異程度會更大,而組織身份與實踐更有可能是獨特的。

制度邏輯具有復雜性,也就是“制度復雜性”(institutional complexity),在這樣一種制度環(huán)境中,行動者受到來自多重制度邏輯的各種信號和壓力的影響。為此,應該關注行動者如何應對這種復雜性,以及多重制度邏輯(比如國家、市場、社會、家庭)如何差異化地影響了不同行動者。學者們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分析框架,強調需要理解制度場域的結構維度(碎片化、正式結構與理性化以及集中化)和組織屬性(場域位置、結構、所有權和治理以及身份)如何影響行動者對“制度復雜性”的回應
。這項研究成果有利于將制度邏輯視角運用于研究組織內部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方面。簡而言之,制度邏輯這一研究視角聚焦于局部與整體之間,以及物質元素與象征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或相互滲透,可以突破“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對立局面。
2.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分析
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都是社會互動中連接制度邏輯與不同組織之間的實踐和身份的動力機制。盡管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在相對成熟的制度場域中頗為穩(wěn)定,但制度變遷依然存在,可能是來自外生沖擊的結果,也可能是組織內部動態(tài)演化的結果。
第一階段,預處理程序。將來自不同感受器上不同數量形式的輸入信息轉換成一組模糊類比信號,振幅與數量大小成正比。比如呈現一系列數量圖形,視覺注意從一個客體依次掃描到其他客體,直到所有的客體都受到掃描,于是產生一組模糊類比信號,按正態(tài)曲線分布。該過程發(fā)生在感覺加工的早期階段,來自視覺、聽覺和觸覺等不同感受器上的數量信號在相應大腦區(qū)域產生模糊正態(tài)函數信號。不同感覺通道中數量類比信號經過瞬息整合后產生輸出信息。
對于特定制度場域來說,多重制度邏輯的存在可以制造組織身份的模糊性,也可以產生對制度變遷進行意義構建的需要。而行動者可以采取行動來應對或解決與多重制度邏輯相關聯的張力。當一個新的制度邏輯在一個場域中產生時,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發(fā)生。特定制度場域的行動者將不得不決定到底是堅持舊的制度邏輯,還是采納新的制度邏輯,抑或是構建出一套混合不同制度邏輯的機制。羅維特·勞恩斯伯里(Wry,T.,Lounsbury,M.)與格林(Glynn,M.A)研究了“場域層級”
,并主張同時關注更廣泛的制度變遷過程。基于此,“場域層級”的研究成為對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分析的補充。
與前面討論的組織內部過程模型類似,圖2提供了一個過程模型來詳細分析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如果特定制度場域中的制度邏輯是穩(wěn)定的,那么多重制度邏輯相關聯的張力將會降低。然而,即使沒有集體動員,組織身份模糊性也會涌現,而組織之間實踐的差異性,或者實踐的表現形式不同,也將催化新的制度邏輯產生。簡言之,制度邏輯的變遷往往需要集體身份與實踐恰當的變異。在什么條件下行動者得以抵制新的制度邏輯,以及其如何反向動員。這需要深入思考如何能夠更好地研究制度邏輯與不同組織之間的身份和實踐的動態(tài)關系。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在根本上與制度邏輯相關聯,但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即與制度邏輯松散耦合。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制度場域中,即使遵守同一制度邏輯,制度邏輯之間或許也存在著細微差別。這種差別可能源自文化的質性差異,或者等級地位的差別。這一研究可以幫助理解產生于特定制度場域中的多重制度邏輯,并對行動者進行歸類(例如監(jiān)管者、貿易協會、媒體和評論人等)。與制度邏輯的研究方法相一致,通過深入闡釋“場域層級”之間的嵌套性,可以得出結論:制度邏輯是“連接的機制,能夠將三種社會互動的動力機制聯系在一起,能夠連接社會互動的微觀系統(tǒng)與中觀(與宏觀)層級,連接象征層面與物質層面,以及連接能動性與結構”
。可以說,制度邏輯理論構建將研究者的關注點引向更廣闊的研究領域,有助于系統(tǒng)地理解“場域層級”之間的嵌套性,以及制度邏輯與組織之間實踐與身份的相互關系等。

四、研究評述
本文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闡明制度邏輯這一研究視角的本質,構建綜合性、多層級和跨層級的理論框架,從而指導相關理論與實踐研究。可以說,任何制度理論都必須明確闡釋出∶(1)社會結構和行動的“部分自治性”;(2)制度的象征性和物質性層面;(3)制度的歷史權變性;(4)制度如何在多個分析層級上運作。本文闡述了制度邏輯視角如何建立在新制度主義理論之上,卻又與新制度主義理論具有根本性區(qū)別。換言之,制度邏輯理論建構不是對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延伸,而是提供了一套系統(tǒng)的制度分析方法,開發(fā)了有關制度邏輯如何塑造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的實踐和身份動態(tài)的過程模型。在此基礎之上,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存在恰當的變異是一個關鍵性的內生機制,其可以引發(fā)深刻的制度變遷。而決策、意義構建、集體動員調節(jié)恰當的變異,并提供了最終導致實踐和身份的實質性改變的關鍵動力機制。已有關于組織身份的相關研究主要強調制度同形框架下組織身份與制度環(huán)境的趨同性,而難以有效解釋組織身份獨特性的形成機制。本文從多重制度邏輯理論視角出發(fā),認為外部復雜的制度環(huán)境為組織界定獨特性身份提供基本元素,并且行動者也能夠能動性地根據其面臨的制度邏輯沖突,而激活組織身份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這呼應了多重制度邏輯理論所強調的“場域層級”之間的嵌套性。
總體來看,學術界關于充分闡釋制度變遷的相關研究仍有待深入,尤其是對于不同形式的社會互動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上結合起來仍然不甚理解。此外,盡管本文闡釋了社會互動的三種動力機制(決策、意義構建和集體動員),但是關于這些動力機制彼此之間的聯系仍有待進行深入研究,這可以通過微觀與宏觀層面來進一步解釋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的實踐與身份的動態(tài)變化。因此,本文提供的分析模型意在為探索更為宏觀或微觀的研究領域拋磚引玉。例如,可以利用社會心理學或認知心理學來構建制度邏輯理論,并闡釋出價值認知與制度情境之間的關系如何受制于制度秩序的影響,以及行動者應采取何種策略平衡多重制度邏輯的復雜性,并且解決多重制度邏輯的演變與共生問題。
[1]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
[2] 涂智蘋,宋鐵波.制度理論在經濟組織管理研究中的應用綜述——基于Web of Science(1996—2015)的文獻計量[J].經濟管理,2016(10):184-199.
[3] 杜運周,尤樹洋.制度邏輯與制度多元性研究前沿探析與未來研究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3(12):2-10+30.
[4] Thornton,P.H.,I.Ocasio,and M.Lounsbury.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structure,and proce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5] 涂智蘋,宋鐵波.多重制度邏輯、管理者認知和企業(yè)轉型升級響應行為研究[J].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45-57.
[6] 鄧少軍,芮明杰,趙付春.組織響應制度復雜性:分析框架與研究模型[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8(8):3-16+29.
[7] 李海秋.多重制度邏輯下的組織身份形成機制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21(10):148-152.
[8] 王鵬.理論·價值·制度·實踐:黨的百年奮斗成就之邏輯透視——深入學習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1-8+152.
[9] 于金富,鄭錦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形成的歷史邏輯、制度邏輯與實踐邏輯[J].經濟縱橫,2022(2):13-18+2.
[10] BARLEY S R.Technology as an Occasion for Structuring:Observations on CT Scann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adiology Departmen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6,31(1):78-108.
[11] 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M].張明德,夏遇男,彭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136.
[12] STRANG D,MEYER J W.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Diffusion[J].Theory and Society,1993,22(4):487-511.
[13]SUTTON J R,DOBBIN F,MEYER J W,et al.The legalization of the Workplace[J].American Joural of Sociology,1994,99(4):944-971.
[14]SUCHMAN M C,EDELMAN L B.Legal Rational Myths:The Nev Institutionalisms and the Law and Society Tradition[J].Law and Social Inquiry,1996,21(4):903-941.
[15] KURTMOLLAIEV S,FJUK A,PEDERSEN P E,et al.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ervice Design: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J].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2018,21(1):59-74.
[16] Randall C.Emotional Energy a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Rational Action[J].Rationality and Society,1993,5(2):203-230.
[17]ANSARI S M,FISS P C,ZAJAC E J.Made to Fit:How Practices Vary as They Diffus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1):67-92.
[18]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17(1):1-25.
[19]BARGH J A,BOND R N,LOMBARDI W J,et al.The Additive Nature of Chronic and Temporary Sources of Construct Accessibility[J].Jou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0(5):869-78.
[20] Legitimizing Nascent Collective Identities:Coordinating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J].Organization Science,2011,22(2):449-463.
[21] SUDDABY R,GREENWOOD R.Rhetorical Strategiesof Legitimac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5,50(1):35-67.
[22] WINDER G M.Building Trust and Managing Business over Distance:A Geography of Reaper Manufacturer D.S.Morgan's Correspondence,1867[J].Economic Geography,2015,77(2):9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