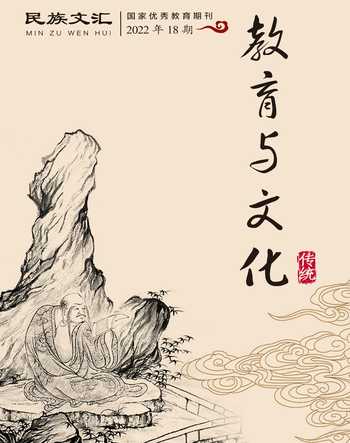淺談微博開放用戶IP屬地功能的影響
徐積佩
摘 要:隨著科技的發(fā)展,移動(dòng)終端的迅速普及。現(xiàn)代數(shù)字社交媒體的互動(dòng)性打破了以往傳統(tǒng)媒體的模式,從單方面的受傳者轉(zhuǎn)變成互動(dòng)者,增加了公民了解信息的窗口,公眾獲取信息更加便捷,參與公共議題的門檻降低。本文以中國(guó)主流社交媒體——微博為例,探討其在疫情期間開放用戶IP屬地功能帶來的影響。
關(guān)鍵詞:社交媒體; IP屬地;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公信力
后真相時(shí)代人們?cè)诿浇榧夹g(shù)發(fā)展的賦權(quán)下得以進(jìn)行更加廣泛多元的表達(dá)與交流[1]。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huì)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表達(dá)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2]。社交媒體為大眾提供了新的討論平臺(tái),改變了傳統(tǒng)的信息傳播模式。同時(shí)也帶來了隱私泄露、謠言傳播等問題,造成惡劣影響。
一、社交媒體
(一)中國(guó)主流社交媒體——微博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指互聯(lián)網(wǎng)上基于用戶關(guān)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與交換平臺(tái)。目前,中國(guó)的主要社交平臺(tái)為微博、微信、博客、論壇等。微博是微博客(microblog)的簡(jiǎn)稱,是基于用戶關(guān)注鏈接關(guān)系的信息分享、傳播和獲取的平臺(tái)。2006年,在美國(guó)網(wǎng)站“Twitter”(推特)推出了微博客服務(wù)之后,2009年新浪微博(以下簡(jiǎn)稱微博)誕生。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中國(guó)社交媒體覆蓋率迅速增長(zhǎng)。經(jīng)過10余年的迅速發(fā)展,微博已成為中國(guó)主流社交平臺(tái)。
(二)社交媒體的特點(diǎn)
近些年,在熱點(diǎn)新聞事件中,社交媒體體現(xiàn)了其強(qiáng)大的實(shí)時(shí)性和互交性。在新聞事件的報(bào)道速度和傳播廣度、深度都領(lǐng)先于傳統(tǒng)媒體,使熱點(diǎn)事件第一時(shí)間被受眾捕捉和討論[3]。微博在中國(guó)社交網(wǎng)絡(luò)中占據(jù)領(lǐng)先地位,成為中國(guó)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之一,以"碎片化"的信息滲透到社會(huì)生活的眾多領(lǐng)域,掀起了中國(guó)社會(huì)信息傳播的"微博熱"[4]。微博以分享與發(fā)現(xiàn)為基本傳播形態(tài),以獨(dú)特的技術(shù)優(yōu)勢(shì)、豐富的社會(huì)實(shí)踐和推動(dòng)公民社會(huì)建立的潛質(zhì),對(duì)公共領(lǐng)域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5]。
在突發(fā)事件發(fā)生時(shí),公眾通過社交媒體得知最新進(jìn)展保障其知情權(quán)。同時(shí),社交媒體為傳統(tǒng)媒體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促進(jìn)了傳統(tǒng)媒體報(bào)道方式的革新。但其用戶和信息規(guī)模龐大,且缺乏“把關(guān)人”,在公共衛(wèi)生突發(fā)事件時(shí)期,少數(shù)不法分子趁機(jī)煽動(dòng)負(fù)面情緒,形成網(wǎng)絡(luò)輿情,對(duì)政府工作的開展和社會(huì)的穩(wěn)定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6]。
二、社交媒體開放用戶IP屬地功能
2022年4月28日,新浪微博宣布將全量開放評(píng)論展示發(fā)評(píng)IP屬地。并在個(gè)人主頁(yè)一級(jí)頁(yè)面展示IP屬地。微博方面表示,該功能旨在更透明地向廣大用戶呈現(xiàn)真實(shí)情況,無(wú)法由用戶主動(dòng)開啟或關(guān)閉。據(jù)悉,微博將根據(jù),最近發(fā)博、發(fā)評(píng)、投票的IP屬地判定所屬地區(qū),顯示規(guī)則為國(guó)內(nèi)顯示到省份/地區(qū),國(guó)外顯示到國(guó)家。在微博開放IP之后,今日頭條、抖音、小紅書等平臺(tái),也已經(jīng)上線或者宣布擬上線此功能。
(一)開放IP屬地以規(guī)范言論自由
社交媒體使公眾獲得了話語(yǔ)權(quán),可以在網(wǎng)絡(luò)媒體上發(fā)布和接受任意信息。社交媒體也在追求利益、點(diǎn)擊率、關(guān)注度、流量。因此美國(guó)學(xué)者施拉姆曾提出“即時(shí)報(bào)償新聞(娛樂、災(zāi)難、體育、漫畫等迎合大眾口味的比較低俗的新聞)在不斷排擠延期報(bào)償新聞(公共事務(wù)、社會(huì)問題、經(jīng)濟(jì)事件、健康教育等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更為重要的新聞)”。在網(wǎng)絡(luò)世界,言論缺乏社會(huì)道德標(biāo)準(zhǔn)束縛,受眾被表象信息誤導(dǎo)對(duì)事件形成片面的認(rèn)知。疫情期間,確診者遭遇網(wǎng)絡(luò)暴力,個(gè)人隱私被泄露。給受害者帶來沉重的精神壓力和巨大的心靈創(chuàng)傷。為此中央網(wǎng)信辦開展“清朗·網(wǎng)絡(luò)暴力專項(xiàng)治理行動(dòng)”,社交媒體開放IP屬地,為凈化網(wǎng)絡(luò)生態(tài)、捍衛(wèi)網(wǎng)絡(luò)良序、文明上網(wǎng)具有積極意義。
(二)開放IP屬地以凈化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
社交媒體的發(fā)展使公眾獲得了話語(yǔ)權(quán),打破了傳受雙方的界限,同時(shí)也造成了網(wǎng)絡(luò)謠言的病毒式傳播。在疫情期間,社交媒體中的信息量增加。各類謠言彌漫。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大量謠言和負(fù)面信息,不利于社會(huì)穩(wěn)定,開放IP屬地有利于打擊仿冒搬運(yùn)、造謠傳謠、冒充熱點(diǎn)事件當(dāng)事人、蹭流量等不良行為,維護(hù)真實(shí)有序的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
(三)開放IP屬地以捍衛(wèi)政府公信力
網(wǎng)絡(luò)社交媒體為大眾提供了新的討論、評(píng)價(jià)政務(wù)的平臺(tái), 政府可以借助社交媒體塑造良好形象、澄清不實(shí)消息、了解民眾動(dòng)向、增加互動(dòng)機(jī)會(huì)。但負(fù)面信息和謠言會(huì)導(dǎo)致政府公信力下降[7]。在新冠疫情期間,微博等社交媒體上出現(xiàn)了大量與疫情相關(guān)的信息,不準(zhǔn)確和虛假的信息會(huì)誤導(dǎo)人們對(duì)形勢(shì)的判斷,引發(fā)了社會(huì)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信息公開透明,是應(yīng)對(duì)“信息疫情”的最佳疫苗[8]。
結(jié)語(yǔ)
社交媒體的出現(xiàn)在豐富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的同時(shí)也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如謠言肆虐、惡意傳播等。在疫情期間,這些問題誤導(dǎo)用戶,造成恐慌、擾亂社會(huì)秩序,不利于社會(huì)和諧穩(wěn)定。社交媒體開放用戶IP屬地的功能在抑制謠言傳播、整頓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捍衛(wèi)政府公信力等方面具有積極效果。
參考文獻(xiàn)
[1]馮莉.“幻影公眾”的認(rèn)知實(shí)踐:后真相時(shí)代生活世界的真相建構(gòu)解讀[J].傳媒觀察,2022(04):87-92.DOI:10.19480/j.cnki.cmgc.2022.04.010.
[2]丁柏銓.論公眾意見表達(dá)及與政府、大眾傳媒的關(guān)系[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2009,30(04):124-128.
[3]王妍.淺談社交媒體對(duì)熱點(diǎn)新聞的輿論影響[J].今傳媒,2017,25(03):47-48.
[4]謝耘耕, 徐穎. 微博的歷史, 現(xiàn)狀與發(fā)展趨勢(shì)[J]. 現(xiàn)代傳播: 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011 (4): 75-80.
[5]張跣.微博與公共領(lǐng)域[J].文藝研究,2010(12):95-103.
[6]桑瑛.新媒體在突發(fā)事件報(bào)道中的作用——以微博為例[J].新聞知識(shí),2014(04):62-63.
[7]趙富麗,段桂敏,陳麗君.新冠肺炎疫情下網(wǎng)絡(luò)謠言特征與對(duì)策研究[J].新聞研究導(dǎo)刊,2021,12(12):122-124.
[8]丁慕涵.社交媒體時(shí)代的疫情傳播:私人領(lǐng)域的公共化[J].中國(guó)廣播,2020(04):62-67.DOI:10.16694/j.cnki.zggb.2020.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