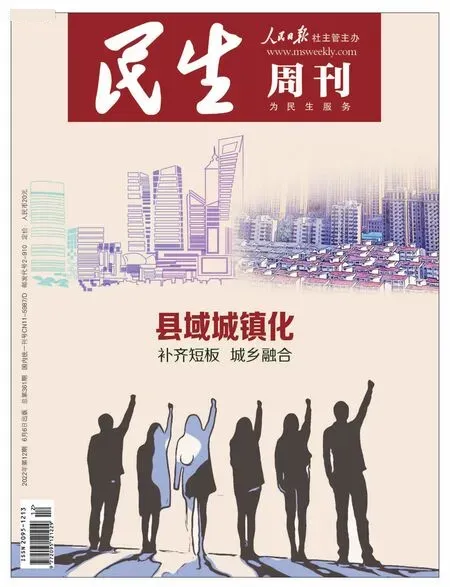城鎮化下半程 縣域空間巨大
□ 《民生周刊》記者 鄭智維
10年前開始關注縣域經濟和縣城發展,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后來將研究領域擴展到城市群、都市圈。談及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馮奎認為,城鎮化發展在空間上逐步走向協調,這是一個不斷優化和調整的過程。
作為我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縣城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有重要意義。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提出,到2025年,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縣城短板弱項進一步補齊補強。
“由于之前投入力度不足,我國大部分縣城現有基礎設施、產業配套、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綜合承載能力與其作為城鎮化重要載體的使命還有差距。”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告訴《民生周刊》記者。
城尾鄉頭

湖北宜都鳥瞰
“鄉村振興離不開城市的反哺。”陳耀認為,現代農業所需的技術、資金、人才都需要來自城市的支持,脫離城市單純談鄉村發展振興是走不通的。
目前來看,人口向大城市尤其是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流動依然是城鎮化的趨勢。我國有19大城市群,從人口和經濟份額來看,這19個城市群及其內外部的40多個都市圈占到全國總量的70%以上。
但目前,我國城鎮化規模格局還不夠合理。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出現“城市病”的同時,一些中小城鎮不斷衰弱。在此背景下,推進更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既是民眾呼聲,也是大勢所趨。
位于“城尾鄉頭”,縣城是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天然載體。“在城鄉發展中,縣城有聯結、平臺、橋梁等多種功能及作用。”馮奎認為,發展縣城,既是城鎮化的任務,也是鄉村振興的要求。
除了有利于引導農業轉移人口就近城鎮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空間布局外,推進縣域城鎮化也是加快推動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
和地級及以上城市城區相比,縣城的市政功能設施目前尚不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較低。此前,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指出,現階段,縣城投資消費與城市的差距很大,人均市政公用設施固定資產投資僅為地級及以上城市城區的1/2左右,人均消費支出僅為地級及以上城市城區的2/3左右。
“提升縣城發展質量,勢必要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配套等方面著力,無疑將會出現一輪基建潮。”陳耀說。
擴大內需考量
事實上,除了對吸納農民進城就業安家、促進城鄉要素跨界配置外,推進縣域城鎮化背后亦有經濟發展的考量。
在陳耀看來,縣城城鎮化補短板、強弱項,有利于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時有利于拉動投資、促進消費、帶動城市發展。此外,我國縣域產業整體呈現出低、散、小的特點,縣城基礎設施建設可推動縣城產業發展升級。
前些年,資源要素較多向中心城市、城區集中。“從市政公用設施固定投資來看,縣城人均僅相當于地級及以上城市城區的1/2,縣城在醫療、養老、垃圾與污水處理、公廁、物流設施等方面均有短板。”馮奎說。
作為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如何推動縣城的發展,也是我國發展的重點。
“在穩增長的要求下,縣城有巨大投資潛力,是有效投資的方向。”馮奎認為,縣城補短板能形成有效投資、拉動需求,是現在各方面都看得準的建設方向,值得社會投資跟進。

河南光山,城鄉面貌煥然一新。
針對人口與產業流入的縣,馮奎建議,要抓住時機實現“產業—人口—空間”的全面轉型,朝著現代化中小城市方向邁進。特別是都市圈范圍內的縣,實際要逐步與城區一體化發展。
在培育發展特色經濟和支柱產業方面,他建議,應強化區域性物流基地建設,形成有影響力的專業市場,提高就業吸納能力,在先進制造、商貿流通、文化旅游等一個或幾個方面體現特色性、專業性。
分類支持引導機制
我國縣域發展千差萬別,不同縣域有著不同發展路徑。
2022年度中國百強縣排行匯總數據顯示,我國GDP突破千億元的縣(縣級市)有43個。其中,排名第一的昆山2021年GDP達4748.06億元。
除了這些經濟強縣,也有一些縣城人口流出。由于資源枯竭、產業衰落,一些縣城出現勞動力外流、房價下跌等現象。“有些縣城,僅能維持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主城區僅有一條主干道,往往還是國道。”陳耀說。
整體來看,我國縣城財力較弱。“靠自身財力條件沒有能力去建設,縣城往往需要市、省、國家層面給予支持。不同分類的縣城,承擔的功能不同,需要上級政府進行分類支持、分類指導。”陳耀說。
早在2020年5月29日印發的《關于加快開展縣城城鎮化補短板強弱項工作的通知》就明確,要立足各地區發展基礎和要素條件,建立分區分類的支持引導機制。
在此基礎上,《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明確要科學把握功能定位。
按照分類引導縣城發展方向,本次政策明確5類縣城的發展路徑,包括加快發展大城市周邊縣城、積極培育專業功能縣城、合理發展農產品主產區縣城、有序發展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城,以及引導人口流失縣城轉型發展。
“千城有千面。”馮奎說,推進縣域城鎮化應立足本縣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功能定位,統籌縣城生產、生活、生態、安全方面的實際需要,從而確定不同類型縣城的發展路徑。
人口流向新趨勢
在上海工作第八年,馮迪決定回老家縣城找份工作。他的這個決定,并非沖動之舉,而是一直在自己的人生規劃之中。
4年前,馮迪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兩年前孩子出生。今年的疫情,加快了他回鄉發展計劃的實施。“回縣城工作,陪孩子一起成長。”
和馮迪有著類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就近就地城鎮化,有利于解決夫妻分居或留守兒童問題。”在調研中,馮奎注意到,農民工流動近年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城鎮化半徑相對縮小,就地就近城鎮化權重在上升。
“中心城市已有長足發展,鄉村振興正全面啟動。在城鄉之間起著關鍵聯結作用的縣城,對加快城鄉融合發展意義重大。雖然進入城鎮化下半程,我國縣域城鎮化仍有空間。”馮奎說。

2010—2020年27個樣本省份縣域常住人口增減情況
目前,縣城及縣級市城區人口占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的約27.5%。截至2021年底,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為9.1億人。其中,1472個縣的縣城常住人口為1.6億人左右,394個縣級市的城區常住人口為0.9億人左右。
有學者預測,到2035、205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有望達到75%—80%。這意味著,我國未來還有1.5億~2億左右的新增城鎮人口。
“大城市周邊縣城,尤其是都市圈內的縣城,人口回流現象會越來越多。除了大城市功能外溢推力外,還有縣城發展拉力,這種推拉決定著人口流向。”陳耀說。
我國人口流動呈現出“跨省區人口流動趨緩、近域化流動趨勢加強”的新趨勢。有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間,全國農村總流出人口中跨省進城人口增加2657萬人,而省內進城人口增長近1.12億人。
這表明,省內城市務工成為近年來人口流動的趨勢。馮奎認為,由于縣城既是一地行政中心又是經濟中心,因此在吸納農業轉移人口方面還有潛力。隨著縣城的進一步發展,未來可能成為多半鄉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