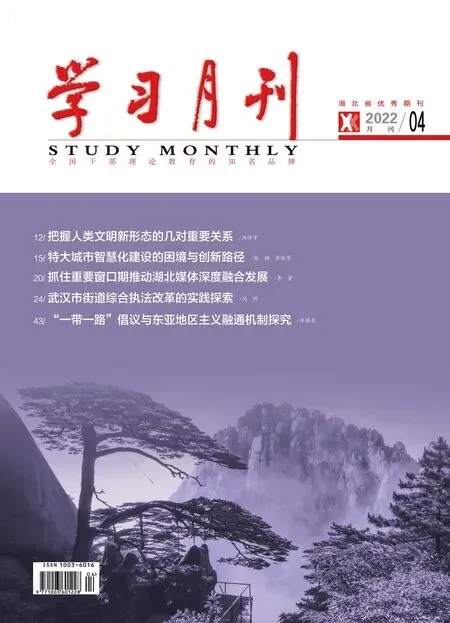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先驅黃藥眠
●殷 鶴 李世輝
黃藥眠(1903—1987),是我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先驅。早在1928年黃藥眠便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并系統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之發展》《費爾巴哈提綱》等馬克思主義經典篇目,為其了解并掌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黃藥眠詩歌、散文創作的不斷豐富以及其對美學、文藝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他逐漸擔負起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任。
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文藝觀的積極踐行者
即便馬克思主義科學地論證了國家消亡的必然性,但并不妨礙其在一定歷史階段對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維護。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是資本主義高速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加快對落后民族和國家侵略擴張的時代,被壓迫的民族只有做到真正獨立并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開始自身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必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來反對外來的敵人”。文學藝術對國家民族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必須成為維護國家主權、推動民族獨立的重要武器。黃藥眠從青年時期就開始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樹立了“要成為一名革命戰士”的人生觀,并拿起文藝的武器投入到民主救國運動中,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文藝觀。
將政治宣傳與文學藝術有機結合。青年時期的黃藥眠目睹了舊中國社會的一片狼藉——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斷加緊,軍閥混戰也越來越頻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企圖在詩歌創作中尋找慰藉的黃藥眠并沒有放棄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憂慮,他熟悉古今中外各種詩體,特別是能將政治宣傳和詩歌藝術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新詩的詩體建設走出了新路。青年時期,他在《黃花崗的秋風暮雨》一文中用細膩的文字描繪黃花崗的景象,用“神人”比喻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烈士,字里行間透露著深深的憂傷,憂傷之中又帶著敬仰和剛毅。全詩沒有激昂的愛國宣誓,也沒有口號式的政治標語,但是卻展現出了青年黃藥眠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文藝思想,激勵人們接過烈士們的接力棒,為重建一個新中國而拼搏奮斗。黃藥眠的這一文藝思想貫穿了他的一生,沒有因為人生的起伏而衰減。晚年時期,他在《祖國山川頌》中歌唱祖國的大好河山,全文清淡而真誠、華美而不矯飾,在形散而神不散中盡顯散文的魅力,極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并激發愛國之情。
把文學藝術作為戰斗的武器。早年的黃藥眠在接觸了泰戈爾、海涅、康德的文藝作品后,一度認為詩人的偉大與否與國家是否強大的關系不大。但是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以及自己對文學藝術研究的深入,黃藥眠的文藝觀向愛國主義轉型,他拿起文藝的武器,參與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之中。在淪陷區,黃藥眠創作了大量的作品鼓舞戰士抗日士氣,語言質樸生動,為民眾所喜愛。他的作品鮮見空泛的政治口號,也沒有激進的鼓動言語,這些源于黃藥眠沉穩的文風,他不會輕易去發表不成熟的見解或不合時宜的觀點。他所著的長詩《桂林底撤退》描繪了一幅狼煙四起、哀鴻遍野的撤退全景圖——火車站里擠滿了人,黃沙河邊傳來了槍炮聲,成千上萬的難民在呼喚聲和哭泣聲中奔跑。細膩的文字、質樸的語言,飽含了對戰爭的厭棄與對侵略者的憎恨,激勵讀者團結一致“收拾舊河山”。此時的黃藥眠已經“放下個人的牧笛,吹響群眾給予我的號角”,用自己的滿腔熱血和文藝作品去抗擊侵略者。黃藥眠文藝思想的形成并不是源于書房中的冥想,“戰斗武器”的獲得也完全在于他的親身經歷,這一點在他所著的報告文學《粵北會戰記》中可見一斑——1939年他曾造訪粵北,深入敵區,采訪戰士,留下了十余萬字的文學作品。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就是最好的武器,不僅可以滿足災難深重的人民群眾的精神追求,還可以激發人民群眾的斗爭精神,將文藝作品的功能最大化發揮。
二、以生活實踐為基礎的文藝觀的積極倡導者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藝就是“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文藝源于實踐,更源于我們的日常生活。黃藥眠充分研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提出了自己的文藝理論——“生活實踐論”,認為生活由“實踐+情感”組成,二者共同作用才能創作出好的文藝作品。
堅持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黃藥眠主張文藝工作者應該立足現實、立足生活,創作出符合歷史潮流的作品。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到社會中去,特別是到人民群眾中去,用心去感受人民群眾的生活。這一理論有力地抨擊了當時學界教條式地引進蘇聯文藝理論的現象,維護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黃藥眠十分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一文藝理論也深刻地表現在了他的文藝創作過程中。抗日戰爭時期,黃藥眠多次奔赴抗戰前線,以詩人、記者、戰士等多重身份參與到文學藝術創作中,留下了諸多寶貴的文藝作品,喚起了無數讀者心中的良知和愛國熱情,號稱中國詩歌史上最長的詩的《桂林底撤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他的散文集《尋找生活的海洋》收錄的作品更是緊緊聯系生活,從生活的細小處觀察,尋找人生的真諦。
堅持情感投入是文藝創作的關鍵。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如何建設我國的文學藝術理論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一種聲音是照抄蘇聯理論,還有一種聲音則是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在文藝創作中的主客觀關系上做文章。黃藥眠則認為文藝工作者在堅持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的同時,還要有感情地介入生活,以此達成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統一。黃藥眠認為屈原之所以能寫下傳世之作,是因為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將個人的情感融入到了人民群眾的生活之中,并轉化成了文藝創作的力量。而一些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沒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也是因為在創作過程中沒有與人民群眾相關聯的真情實感的帶入。
三、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文藝觀的積極弘揚者
馬克思主義理論歸根到底是人民的理論,是為了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創立的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滿足人民群眾對先進文藝作品的需求,馬克思主義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人民群眾、記錄人民生活,馬克思主義文藝作品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黃藥眠是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文藝觀的堅決擁護者和積極弘揚者,他反對文藝作品與人民之間產生隔閡,或者成為人民群眾高不可攀的存在。他的“生活實踐論”也正是以人民為核心,以讓人民更好地生活為目的。
“生活實踐論”從人民的角度對文藝大眾化運動存在的問題進行批判。黃藥眠認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興起的文化大眾化運動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當時的文藝工作者雖然走到了工農群眾中,但是并沒有真正與他們打成一片,只是單純地以尋找創作素材為目的,沒有真正地體驗大眾的情感。這種帶著情感隔膜接觸人民群眾的做法顯然是與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文藝觀相違背的,以致于相比文藝大眾化運動的規模而言,優秀文藝作品的數量明顯不足。此外,黃藥眠雖然認可文藝作品帶有政治情感,但堅決反對文藝政治化,他認為文藝應該是為民眾服務的,而不是去主宰民眾的,那些將文藝當作提高民眾欣賞水平的拯救手段的觀點無異于將文藝政治化,這樣就失去了文藝的本來意義。所以,黃藥眠主張文藝源于生活,但更源于人民,只有對人民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才能真正做到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才能挖掘最好的創作素材,才能完成優秀的文藝作品。而那些將文藝政治化的行為,并非是從人民群眾的需求出發,自然不會生成優秀的文藝作品。
“生活實踐論”從審美的角度確定了文藝作品應接受人民群眾的檢驗。1957年,黃藥眠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美學講壇上針對學界“美就是美,是客觀存在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美并非存在于事物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根據自身生活實踐對美的評價中,即人的審美活動中。文學藝術作品之所以能給人以美的感受,是因為它滿足了人們物質或精神生活的需要,符合了人們的審美標準。所以,文藝作品應該接受人民群眾的檢驗,以是否滿足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作為文藝作品優秀與否的評價標準,這一點也批駁了當時社會上“反對降低藝術標準以迎合普通民眾的審美趣味”的觀點。在文藝創作實踐中,黃藥眠也是積極為勞動群眾寫作,反映大眾聲音,并接受人民群眾的檢驗。如他的散文《工蜂頌》以工蜂為喻,贊美了祖國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他們通過辛勤勞作收獲美好生活。該散文一度入選小學生語文教材,深受人民群眾好評。
黃藥眠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留下了諸多寶貴的文學藝術作品,更是一位文藝理論家,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黃藥眠任教北京師范大學,嚴格執行黨的文藝、教育方針政策,不僅升華了自身文藝理論,更是培養、教育了無數文藝新人。在建黨百年的今天,我們追憶黃藥眠,不僅是要學習他的文藝理論,學習他以愛國主義為核心、以生活實踐為基礎、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文藝觀,以更好地繁榮和發展我國文藝事業,更是要通過對文藝史的學習,加深人們對“四史”的了解,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來之不易,從而更加堅定“四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