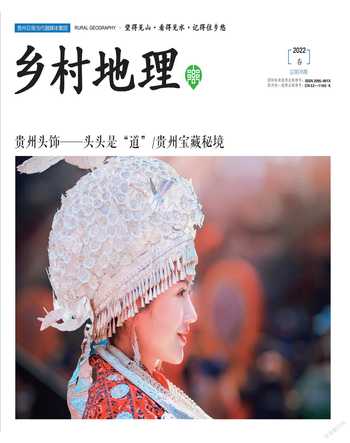悠悠歲月寄深情
姚江


前些日子,我搭程老鄉的轎車,從天柱回了一趟老家,到達時已近黃昏。
晚飯時,與幾位老人圍爐煮酒,敘說陳年往事,聊起家常,對家鄉的情感一絲絲涌上心頭。想起很多天柱人對我老家票洞的印象還很陌生,有的甚至連票洞的名字都未聽說過。天柱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不用提。于是我提筆寫幾個文字,希望它能被更多人了解。
票洞四面群山環抱,山巒疊翠,群峰澎湃,雄姿英發,它虎踞橫臥在山谷中,形如燕子窩,是天柱縣高釀鎮木杉村的一個自然寨。全寨有二十多戶人家百余人口,現有吳、龍、鄒、姚、李、劉、龔等七個姓氏,全部為侗族,鄉民交流皆用侗話。據說,龍姓在票洞已繁衍了十七代,至少已有三百五六十年的歷史。最先遷入票洞居住的是吳姓和陶姓,是票洞的開拓者,這兩個姓氏比龍姓還要早遷居兩三代人。姓氏發展最多的時候達到九姓,比木杉大寨還多,故有“七姓木杉九姓票”的說法。由此可以推算,票洞的歷史淵源可追溯到四百二十年前,為明朝萬歷年間。
因沒有史料記載,全寨所有的姓氏族譜記錄的東西都沒有超過一百年,我無法了解它四百多年來的全部演變過程,任憑它風云變幻的往事封存在歷史的塵埃中……若干年前的所有過往煙云已無法一一追憶,只能從票洞人口口相傳中探究一二。前人到此定居后,開荒拓土,造林耕田,歷盡艱難。我們只能用想象的方法去觸摸那段歷史,它好像是跨越明清兩代的時光飄過來似的。被“割斷”的歷史部分,成為我心中的遺憾和隱隱灼痛。
票洞民居坐南朝北而建。整個寨子還分成十分動聽的小地名,如“登洞”“角龍啊”“沖榴”“偶門”等。居民住房主要以兩層木質結構樣式的吊腳樓為建造風格。前些年,當地政府工作人員曾到票洞宣傳異地移民搬遷政策,但因人們鄉戀情結濃厚,舍不得離開生養長大的地方,無搬遷愿望。如今,生活水平提升,村民們新建的都是磚混結構瓦房,十分氣派。現在的寨子風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木房與磚房相間點綴,互相映襯,別具風格,寧靜自然。
票洞風光旖旎,景色迷人。它前面有一條小溪以溫馴的品格繞寨流淌而過。連綿起伏的山巒向寨子兩邊延伸,有的形如獅子嚎叫,有的貌似蛟龍飲水,為大自然舒展了一幅美麗天然畫卷。
為填補前人無村寨歷史記錄的文字空白,謹以一首《票洞懷古》小詩作記:
遠去江流宛若龍,
常飄玉帶把持中。
客家停馬關千里,
夜半挑燈閱五重。
票洞人思想開闊,崇尚以文載道,為人謙遜,詩書達理。票洞人熱情大方,凡是到票洞做客,都尊為貴賓,你來就會體驗到“相逢不飲空歸去,洞中桃花也笑人”的邀約,飄香的米酒,壇中的腌魚,家中的茶葉,都會端上桌前,讓客人品嘗,體驗不醉不歸。票洞人民勤勞,富有教育培養子女讀書成才的高貴品質。哪怕再苦再窮也要供子女讀書上大學。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里戶戶都有大學生,甚至有考入北大的孩子。從票洞走出來的有大學教授、政府官員、建筑工匠等等,他們在國家最需要的地方發揮聰明才智。雖然崗位不同,職業不同,作為票洞人,他們的骨子里無不流露出一股“孤傲”的氣質,展現了侗族人的剛毅和執著堅定。
在我的記憶中,父輩都是種植黃豆、生姜、玉米、藍靛等農作物作為主要經濟來源,或養田魚賣魚苗,燒木炭、養肥豬變賣換成我們的學費。高中以后,每逢周末,我要從六十里開外的天柱縣城走路回家拿生活費,有時因父母無法湊好生活費而又步行重返學校,只有多扛幾斤大米換成菜票又維持一個星期……再看看今日已然脫離艱苦歲月的美麗票洞不免有些唏噓。
時間過得真快,幾百年如彈指揮間。票洞經過明清及民國時期的懵懂青春,如今,已歷練成為一個令人神往的地方。村寨公路沿著木杉通往高釀,直達天柱,連通世界。婀娜多姿的票洞,以洋洋灑灑的氣度走過了四百多個春夏秋冬,無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愿它一切美好如初。(責任編輯/孫晉楠)
村寨信息:
區位:黔東南州天柱縣高釀鎮木杉村票洞寨
交通:貴陽出發,經貴遵高速往凱里方向進入蘭海高速,經余安高速沿榕高速到達天柱縣高釀鎮。或乘坐高鐵到達凱里站,轉乘大巴前往天柱縣,縣城可搭乘公交至高釀鎮。
鄉村特色:有較為著名的“一線天”“老虎落難洞”“白龍洞”“老龍潭”等多處自然景觀,特產有遠口發豆腐、天柱臍橙、天柱土鴨、天柱大血藤果等。CD079D0D-BA75-4BE1-A69E-368CA3B19A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