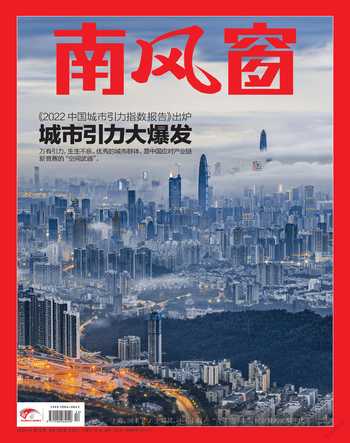《婦女權益保障法》大修
朱秋雨

“移走法條里的一粒沙,也許就移走她身上的一座山。”
此刻,是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2年通過以來,第三次修訂的時機。5月前后,面對該草案在向全社會公開征集意見的活動,許多人士開始奔走相告。
博主“卡卡荷生”在微博寫道:“不用擔心自己無話可說,請相信,只要開始,所有的建議都根植在你息息相關的生活。”這條微博獲得近10萬人次的轉發,14萬次點贊。
對該草案的熱情涌動,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2021年12月,《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第一次面向社會征求意見時,共獲8萬余人參與,共提交42萬余條意見。
再到這次,為時一個月的第二稿征集意見活動于5月19日截止,中國人大網顯示,又有8萬人提出了30萬條意見。
擁有19年從業經驗的反家暴律師李瑩告訴南風窗,該法是最近的“除民法典以外最受關注、參與度最高的”一部法律。在這期間,她與所屬機構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內部人員、專家學者聯合,就二次審議稿提出34條建議。
這些行動,與性別平等和女性意識覺醒的大背景相關。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蔣月對記者總結稱,本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一大進步在于首次確認性別歧視的定義,“明確規定排斥、限制婦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項權益,就是歧視婦女”。
“換言之,婦女依法享有某些特殊權益具有正當性,不違反平等原則。”她解釋。
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李洪祥告訴南風窗,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大修,既是回應2021年實施的民法典對婚姻自由、夫妻財產等新規的認定,也響應“三孩”政策等社會變化下對婦女權益提出的新要求。
李洪祥曾參與中國法學會組織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專家咨詢會,他認為,此次大修充滿亮點。
他說,性別平等在現實中遠未實現,“到了現階段,追求的不只是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我們的目的,是實現實質性的平等”。
2021年12月20日,《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一審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當月24日,第一次面向公眾征集意見。
作為專注于弱勢群體社會服務的人員,李瑩立刻行動了起來。她首先在處理婦女問題的一線社工、律師等群組里搜集意見,又參加了婦聯組織的會議,還組織了專題研討會,與眾多北京的法律學者交流,“一個月的時間都泡在提出意見上”。
結合多方觀點,李瑩做出了一版屬于“源眾”機構的58條建議。
在這個版本里,她們提出了如提高人大代表中的婦女代表以及職工代表大會中女職工代表的比例等42條修改內容,也希望新增諸如“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等應開展性別意識和保護婦女法律法規的教育和培訓”等16條建議。
她告訴南風窗,上述建議有4條在二審草案中得到反映。
李瑩認為,盡管仍有不足,但研究婦女問題的專家形成了共識:從一審草案來看,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是一次“大修”—“從機制到具體措施,到婦女的權利上,都有非常大的完善”。
例如,一審草案首次提出男女平等性別評估機制,明確性騷擾、就業性別歧視等具體的定義。
據新華社報道,一審草案相比現行法律,修改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
李洪祥告訴南風窗,一審草案一大特點是與民法典協調一致。因此,草案將原來“人身權利”的章名修改為與民法典同樣的表述:“人格權益”,將婦女的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分別進行保護。
蔣月總結稱,二審草案的一大修訂也與人格權有關—將原先第六章的人格權益提前至第三章,使其在具體權利類型中僅次于“政治權利”。這一安排體現了“人前物后”的法律邏輯。
被劃定在人格權益章節的“禁止性騷擾”是其中一大亮點。李洪祥對南風窗回憶,從1990年代開始,我國法學界多次就“性騷擾”的定義開展討論,但始終未達成共識,爭議在“某些情況下,很難將女性的主觀感受劃歸為性騷擾(認定要件)”。
而此次的二審草案不僅用列舉的方式明確性騷擾的主要表現形式,還規定了采取性騷擾預防和制止措施的法律責任,同時明確規定了學校和用人單位是預防和制止性騷擾的責任主體。
令上述專家感到眼前一亮的條例,出現在二審草案。其中新增一條,為預防未成年女性被侵害,要求學校建立入職查詢制度:查詢人員是否具有性侵害、性騷擾等違法犯罪記錄。
草案公布以后,與長期面臨的爭議相似,如何推進法律的執行,成為了接下來關注的焦點。
知名法學教授李明舜在《婦女權益保障研究》專著里曾表明:“我國婦女法缺乏可操作性。”他認為,修改和完善的方向,應是突出其保障性—強調國家干預和保護;實現司法化,使其具有可訴性等。
李洪祥也在此次面對全國人大法工委征集一審草案意見時,著重建議“法律不僅具有宣言書的作用,還應該具有可操作性”。
他在一審草案公布后不久提出,“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除了宣告婦女擁有哪些權利,還要明確權利受到侵犯后應當如何救濟”。
李洪祥對南風窗解釋,救濟措施是“從權利到責任的過渡地帶”,需要各單位和組織踏實地做事落實,解決現實問題,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一審)草案規定的婦女權利并非都有明確的救濟途徑—這需要加以明確,否則婦女可能不能真正享有這些權利”。
上述建議在今年4月公布的二審草案中得到反映。不夠明晰的“法律救濟與法律責任”章節,被拆分為“救濟措施”和“法律責任”兩章,強化了救濟措施的監督、落地及責任追究。
與此同時,執法主體的法律責任在二審草案進一步明晰。其中一個社會背景是在2022年的全國兩會,無論政府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均對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作出回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閉幕后的記者會上表示,對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嚴厲打擊,嚴懲不貸。
4月18日,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叢斌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匯報稱,基于部分地方揭露出的拐賣婦女等惡性案件,暴露出基層治理存在一定短板,擬增加強制報告與排查制度。
二審草案寫下了這一規定:“婚姻登記機關、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婦女疑似被拐賣、綁架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及時調查處理。”
同時,二審草案明確,婦聯應當發揮其基層組織作用,會同公安等部門加強對拐賣、綁架等侵害婦女權益行為的排查。
“這就實現了法律的剛性和柔性并舉。”李洪祥總結上述變化。
另一種提高法律操作性的方式,多位法律學者告訴南風窗,即條文內容精細化,這亦是本次修法的一大進展。蔣月認為,此次修法改變了以往“宜粗不宜細”風格,有助于執法特別是司法適用。
例如,過去的婦女法只是一則“禁止就業歧視”條款,如今明確列舉了職場性別歧視的主要情形,規定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中,不得限定男性或者規定男性優先。
二審草案還對企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個人基本信息外,不得進一步詢問或者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以及意愿。”
“立法技術進步明顯。”蔣月總結說。

婦女作為“半邊天”的角色,隨著三十年來《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不斷修訂,從立法層面得到了確認和加強。但從現實各方面來看,性別平等遠未實現,女性依然易成為權益受損群體。
深耕婦女法多年的法學專家蔣月和李洪祥都對此強調稱,在鼓勵生育“三孩”的關口,理應正視女性因為生理結構、在承擔和維系家庭以及孕育生命時的作用和價值。
蔣月告訴南風窗,二審草案第五章“勞動和社會保障”在第46條至第54條規定“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國家建立健全職工生育休假制度等與生育有關的政策”。但總體看,這些內容絕大多數來自《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現行法規,而針對新情況作出的新應對不足。
所謂的新變化,蔣月認為,在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的今天,女性職業發展的窗口期與最佳生育年齡基本重合。這意味著,女性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平衡的難度加劇,“迫切需要增設制度予以緩和”。
她因此建議,參照國務院《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相關內容,新增一條:“鼓勵、支持用人單位建設家庭友好型工作環境,為女性生育回歸崗位或再就業提供培訓等支持”。
相關舉措包括,建立女職工哺乳室、孕婦休息室等母嬰服務設施,提供福利性托育托管服務等。
李瑩也贊同上述建議。她至今印象深刻,2017年到耶魯大學訪學時,曾見過驚奇的一幕:許多母親來上課時,直接將孩子放到了一個專門照顧1歲以下嬰兒的機構。而該機構就設置在耶魯法學院內部。
“我當時特別尷尬,一下意識到我國嬰幼兒的托育機構數量不夠。所以希望鼓勵大型企業或社會力量建立托育機構,并降低對幼兒年齡的限制。”她說。
二審草案公布后,李瑩所屬機構也就生育政策單獨提起7條意見。她告訴南風窗,保障女性生育權的制度將過多成本轉向企業,加劇女性就業時的隱形歧視。
因此,她建議新增“明確對以女職工為主的用人單位在稅收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明確規定減輕企業繳納生育保險的壓力”等,從源頭減輕女性就業面臨的不平等。
與眾多民間機構的意見相似,綜合發達國家的經驗,李瑩呼吁婦女法明確延長男性育兒假的要求,“并明確不能不休或轉讓給配偶”。
李洪祥認為,上述來自民間的聲音具有一定的時代因素和依據,目的是“將男女拉到同一個起跑線上”。
他也在提交給全國人大法工委的二審建議稿中,建議“在考核、評價、崗位聘用等環節,對孕哺期女性適當放寬期限要求,延長評聘考核期限”。
在《婦女權益保障法》大修的節點,有一股積極建策的力量來自民間,他們的聲音同樣不可忽視。
微博、小紅書、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臺,“團結就是力量”“為我們的后代盡一份力”等語言廣為流傳,試圖呼吁更多人重視此次修法。
性別研究學者、媒體人李思磐曾在受訪時分析,近幾年社交媒體上的女性比較活躍,彼此形成一種相互激勵的狀態。在社交平臺上,討論自身權益的議題都很多,“說明大家有興趣、有動機去參與”。
與刻板印象不同,李瑩接觸的積極參與婦女法意見征集的女性,其實是背景迥異的。
“有在職場中被歧視的孕婦,或者因為產假被解雇、被家暴,或者是曾遭受性騷擾的女性等等。”她認為,是否積極參與意見征集活動,與學歷、經濟水平等無關,“與人生經歷有關”。
一直迫切地向李瑩所在機構反饋建議的,是一群“紫絲帶媽媽”—孩子被父親暴力搶走、藏匿,導致她們無法與孩子相見。很多時候,即便監護權屬于女性,孩子仍不在身邊。
李瑩告訴南風窗,這群母親希望的,是法律可以規定搶奪孩子一方不允許有撫養權;藏匿造成嚴重后果的,應追究責任。
李瑩將該建議寫成了法條意見,放入公眾號,鼓勵更多人共同倡導。
但她發現,每次主張新增與女性利益相關的立法或修法時,都有聲音表示不理解:“已經有相關的制度了,何必對微小的權益一提再提?還要專立一部法律?”
更多奇怪的聲音,不一而足。
作為研究《婦女權益保障法》多年的男性,李洪祥認為,性別平等從來不止形式的平等。基于過去長期男女不平等的境況,以及女性在現實中更易被侵害的生活,“大家如今自然希望減少男性的權益,增加女性的權益”。
但李洪祥表示,立法終歸是平衡多方的過程,修訂法律很多時候要避免爭議,“一是過多爭議本身沒有意義,二是不能讓好的初心因此被誤解和破壞”。
從這個角度看,李瑩說,從立法上實現性別平等無法一蹴而就,但她總體而言感到樂觀,“至少我們在形成聲勢,讓我們女性的聲音每次都能參與到立法中”。
李洪祥則將法制的進步比喻成數字。
“如果有1了,后面加幾個零都管用,要是連1都沒有,0再多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