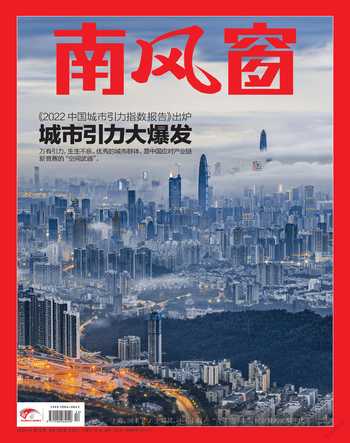青島,能否趕上“下半場”
杜杕

每每提及“最憋屈省會”,大眾總會不由想到兩座城:一個是身在江蘇、輻射安徽的南京,另一個則是常年省會首位度“吊車尾”的濟南。
濟南被一些人認為欠缺省會之風范,調侃起來也毫不客氣。曾經,濟南甚至被認為有點像縣城。
被稱為山東“雙子星”的另一座城,卻別有一番景象—“綠樹青山,不寒不暑,碧海藍天,可舟可車,中國第一”,這是梁實秋筆下的青島。綠樹掩映的街道,融合中西方文化風格的紅樓洋房高低錯落、連綿起伏,而且為了體現城市景觀的設計感,每一棟近代建筑的外形都無一重復。
青島,嘗近代開放風氣之先,異域風情不僅刻印在城市風貌上,還和這座城的制造業圖譜交織互動。
從基礎設施到生產制造,青島屬于國內最早踏入工業化軌道的那批城市。
19世紀末,這座濱海城市被定位為軍事基地和交通要塞,山海之間修建起青島港和膠濟鐵路。為了服務城市發展,歐洲的啤酒、汽車、自行車也在這時傳入。
青島德國啤酒廠、麥庫爾電燈廠、礦泉水廠拉開了青島發展輕工業的帷幕,海軍修船所、鐵路公司的四方修理廠則為青島之后的機械、動車制造打下基礎。
時局變遷后,紡織業成為青島的主要產業,順帶生產火柴、面粉、榨油、制鹽、制絲等日化品類。到1936年,以日資為主的青島紡織業有紗錠56.8萬枚,占全國的10%,紡織工業的資本總額更令人咋舌,單單一城就占全國行業總資本的1/4。
憑借從紡紗、印染到機械制作等環節的完整產業鏈,青島穩坐國內三大輕紡工業城之一。解放前夕,上海、青島、天津三市的棉紡織設備就占到全國七成左右,“上青天”的美譽由此而來。
建國后,青島原有的工業基礎得到傳承。一方面,輕紡業依舊保持全國領先地位;另一方面,軌道和陸路交通也頗有長進,青島四方機廠造出了第一輛國產蒸汽機車,之后又在這里誕生多個“中國第一”:第一批鐵路客車、第一列雙層客車。
作為自行車工業的發跡地之一,1954年青島的自行車產量便突破萬輛大關,和沈陽、天津、上海并列為國內四大自行車行業之都。
家電業的興起,也多少暗含了一點歷史的伏筆。1984年青島電冰箱總廠組建,其冰箱生產技術正來源于德國利勃海爾公司。第二年,青島的第一代彩電、雙缸洗衣機,分別引進自日本的松下和夏普的生產線。
如果說近代的青島制造有著西方和日系的影響,那么改革開放后,韓資無疑是青島經濟版圖里濃墨重彩的那一筆。
1989年,韓方在城陽投資45萬美元成立青島托普頓電器有限公司,這是山東第一家、國內第二家韓國獨資企業,托普頓也成為韓資企業涌入青島的開端。
當然,這樣的跨國資本流動并非偶然。一是地緣相近,青島到首爾的直飛航班不過兩小時功夫,二是產業梯度轉移的必然選擇,漢江奇跡推動韓國一躍成為發達國家,土地、勞動力等生產成本大增,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內難以為繼,不得不尋找新熱土。鄰近的青島正好還有制造業基礎,雙方可謂一拍即合。
在這之后的近20年,青島都是韓資在華的第一大流入地。2008年,韓資企業在青島就有4000多家,跟著廠子、項目一起過來的韓國人接近10萬。
即使到2019年,在青島注冊的韓資項目累計仍然達到13010個,實際投資額197.4億美元。
韓國企業在青島有多密集?青島當地流傳著一種說法,只要會中文就不會迷路,只要會韓語就不愁工作。
乘著外向型經濟的“春風”和“五朵金花”的崛起,1990年代,青島實現了對大連的趕超,在五大計劃單列市里位列第二。進入和世界全面接軌的21世紀,青島繼續高歌猛進,2005—2010年,GDP穩居全國前十,2008年還一度超過無錫躋身全國第九。因為沿海區位、對外經濟和深圳的相似,青島有了“北方深圳”之稱。
只是,在下一個十年,這座北方大港的榮耀并未延續。
2010年后,青島在全國的排名幾度滑落,相繼被佛山、成都、武漢等南方城市趕超。2018年,地方的經濟數據改由國家統計局統一核算,青島的GDP遭遇“擠水分”,由原來的12001.52億元下調至10949.38億元,2019年的經濟體量也不及1.2萬億,11741.31億元的GDP排在寧波、無錫之后,青島的全國排名“著陸”到第15名。
而且,青島作為“北方第三城”的地位也并非不可撼動。強省會、臨空產業的加持下,鄭州勢頭正猛。
掉隊了,為什么?
有人喜歡“見微知著”。2004年的CCTV年度經濟人物頒獎典禮上,主持人邀請34歲的馬化騰向商業巨頭、海爾掌門人張瑞敏推銷QQ,卻遭對方無情拒絕:“現在還沒有說服我,非常感謝你剛才非常動人的說服詞,但至少我現在還沒有這個興趣要加。”
這樣一個科技圈流傳的故事,常常被用作青島產業轉型遲緩的一個側面印證,只顧守成家電、紡織、石化等傳統行業,錯過了互聯網的“上半場”。
殊不知,青島既錯過了互聯網的“上半場”,也錯過了利用外資的“下半場”。
2003年開始,青島就開始出現韓資企業的非正常撤離,而且這一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據山東省外經貿廳統計,2003年韓資企業從青島非正常撤離的有21家,2004年有25家,2005年有30家,2006年43家,2007年翻一番達到87家,到2008年非正常撤離的韓資企業累計達到206家。
不少韓資企業家,直接撇下租來的廠房設備,不支付員工工資和久拖的債款,不辦理適當的破產手續,一夜之間就飛回韓國,讓一些青島人焦頭爛額。
但這樣的大規模撤資,也有跡可循。2008年韓資大規模撤離時,青島市統計局就發文承認,市內引進的外商投資企業多為韓企和日企,規模小、創利低、繳稅少、不規范。不妨去看更具體的行業:在青韓資主要集中在制鞋、化纖、電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矩陣,明顯傳統而粗放。
隨著青島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消退、生產成本上升,草根型的韓資企業生存空間大大壓縮。青島韓國社會和企業聯盟經理Sung Jeung-han曾向媒體表示,青島6000家韓資企業中的20%~30%都在虧損,“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和進口價格上漲是主要原因”。廠房、設備都是租來的,那么一走了之就比破產清算成本更低。
而在同期,同樣以外向型經濟見長的蘇州,已在謀求轉型。
首先看外資的產業結構,如果用銷售收入衡量外商投資的行業結構,2007年蘇州外資營收前三的行業分別為電子信息和通訊設備(46.6%)、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7.0%)、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5.1%),電子信息產業作為蘇州的主導產業,外資的集中度尤其高。而縱觀青島營收前十的外資企業,將近半數都屬于石化、冶煉行業。
其次,要改變“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傳統加工貿易模式,出路還在于吸引外資落地研發、銷售等附加值更高的環節。根據山東省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青島跨國公司總部機構有49家,而蘇州在2011年,這一數字就已達到147家,外資研發企業也有416家。更多總部機構的落地,往往意味著外資對地方的經濟貢獻、技術溢出都更為明顯。
從簡單幾個數據的對比,可見這座曾在一次次開放中贏得發展紅利的城市,多少也因為轉型遲緩、邁的步子不夠大,而錯過了利用外資的“下半場”。
近年來,青島不乏新一輪開放的戰略機遇。2018年6月,上合組織青島峰會上,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范區橫空出世。得到政策加持的青島,在國際物流、現代貿易、雙向投資、商旅文化和海洋“4+1”個領域,可以有更多資源傾斜和先行先試的探索。
錯過了互聯網的“上半場”,“下半場”終于不缺席。根植制造業基礎,青島立下打造“工業互聯網之都”的雄心。日前,國家工信部公示2022跨行業跨領域工業互聯網平臺清單,海爾推出的卡奧斯COSMOPlat已經連續四年位列榜單首位。
還有,制造業的家底也依然扎實。2021年初出爐的先進制造業集群“國家隊”名單里,全國25個集群入圍,山東2個集群都花落青島,一個是海爾、海信、澳柯瑪等家喻戶曉企業成就的智能家電集群,另一個是全國動車組整車60%“青島造”的軌道交通裝備集群。
2021年青島的經濟數據公布后,制造業比重一欄頗受關注—工業增加值3884.07億元,占GDP比重為27.48%,較2020年提升1.1個百分點,這是自2006年來,青島工業增加值的首次上升。
作為北方明珠,青島對資源的吸引力依然強勁。比如,在《2022中國城市引力指數報告》中,青島的城市引力名列全國15位,是北方地區除了首都北京和兩個強省會(西安和鄭州分別為11和14)之外,唯一入選前15名的城市。該報告由南風窗傳媒智庫和鹽財經出品,以城市對資本和人才的吸引力為評判指標,側重于對城市發展動能和潛力的測算。
青島重振制造的決心不小,但要回歸第一梯隊,那塊“短板”還是高端制造。經常同青島上演“三國殺”的沿海工業大市—寧波、無錫,2020年規上工業營收利潤率分別為8.8%、6.9%,青島則只有5.5%。規上工業利潤率不高,側面反映制造業的層次偏低。
即使是明星產業,青島的智能家電業仍然困于缺少關鍵上游配套。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總裁周云杰曾以合肥對比分析,在用地、用工成本以及招工難度上,青島的條件都優于合肥。但更明顯的差距則體現在本地配套率上:與合肥70%相比,領先數十年的青島僅有40%。
合肥力推“芯屏器合”產業,青島卻有“缺芯少屏”的煩惱。即使2021年青島引來京東方積極“補課”,但這一項目主要生產顯示端口器件,而非京東方最具科技含量的面板。
從外部引進更強大的“鯰魚”來激活整個產業,是一個可行的思路,比如特斯拉落戶臨港,但觀念開放、實干氛圍才能形成“強磁場”。對此,青島是否也會將其作為可選項?
這幾年,青島也有好學之心,“接上海”,“學深圳,趕深圳”,還有大批干部南下考察蘇州、成都,“拜師學藝”思想觀念、產業布局、招商引資、政務服務。
閱盡千帆后,唯愿這座濱海城市能找到自己的“青島模式”,重回中國城市的最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