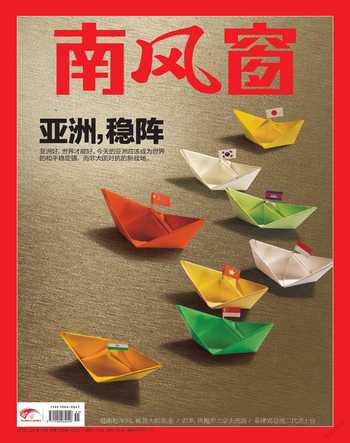東南亞的抉擇
湯興

當地時間5月12日至13日,趕在拜登上任后首次亞洲行之前,美國-東盟特別峰會在白宮召開。
這是東盟國家領導人首次以團體身份齊聚在華盛頓,也是他們時隔6年再次參加由美國總統主持的峰會。東盟十國中,除了剛剛結束大選的菲律賓派外長洛欽作為代表、緬甸因為去年發生軍事政變而未獲邀請外,其余八國的領導人皆出席了峰會。
拜登在峰會上表示,雙方關系進入新的時代。
從白宮公布的信息來看,此次峰會主要達成了三項成果:美國和東盟的關系將于今年11月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美國將向東盟提供價值1.5億美元的援助;美國任命哈內斯·亞伯拉罕(Yohannes Abraham) 為新任美國駐東盟大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李明江告訴南風窗,此次峰會,雙方本就沒有太高期望,“美國通過這次峰會體現了對東南亞地區的重視,表明它會持續與東盟國家加深全方位的合作。而東盟的期待也一直是希望美國繼續參與東南亞事務,在這個地區凸顯重要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周方冶則認為,作為中美都非常重視的外交對象,東盟在峰會上保持了其一貫的中立性和自主性,表態留有回旋空間。
被拉攏的對象
在峰會召開的前一天,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表示,拜登政府已經深刻意識到,其他緊迫的全球挑戰都不能分散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注意力。他稱,盡管烏克蘭危機的確占據了拜登政府很多精力,但華盛頓依然意識到其最大地緣戰略挑戰來自印太地區。
“過去幾屆政府曾下過將重點放在東亞或印太地區的決心,但卻被其他緊迫的挑戰轉移了注意力,這種情況不能再發生了。”坎貝爾說道。他還透露,以往負責東盟事務的是一小組美國官員,現在整個美國政府都會參與。
周方冶向南風窗記者分析說,東南亞是印太戰略的核心區域,同時也是中國的重要周邊。圍堵中國,東南亞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和東盟的互信缺失較大。拜登將東南亞重新納入重點方向后,需逐步重建與東盟的關系。”
據中國商務部數據,東盟在2020年起躍升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已經穩坐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13年。2021年雙邊貨物貿易額達到8782億美元。東盟10個成員國都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相關文件,中國與東盟都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
在民眾認知層面,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中國已不在一個量級。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 2022年度《東南亞態勢報告》顯示,76.7%的受訪者將中國視為東南亞最具經濟影響力的國家,而認為是美國的只有10%。另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中國是東南亞地區最具政治和戰略影響力的國家。
不過,根據ISEAS的報告,在拜登上臺后,東南亞民眾對美國的信任度有明顯提升。而且,相較于特朗普,拜登政府在東南亞投入了更多精力。
自去年下半年起,副總統哈里斯、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和國防部長奧斯汀等多名美國高級官員訪問東南亞。拜登政府還派遣官員出席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美國-東盟外長會、東盟地區論壇等多個以東盟為中心的系列地區會議。
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下的一些小多邊機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威脅到東盟的中心地位,東盟各國領導人也已經很明顯地感知到這種威脅。
去年10月下旬,拜登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舉行線上峰會,宣布了1.02億美元的新合作倡議計劃,并首次提出“印太經濟框架” (IPEF)構想。今年2月,白宮公布《印太戰略報告》,“加強與東盟關系,在東南亞擴大雙邊合作”,是該文件列出的10項印太核心計劃之一。
但不少學者認為,拜登對東南亞的關注遠談不上有多重視。《外交政策》指出,拜登在任期第一年沒有與任何一位東南亞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談。相比之下,拜登在白宮會見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領導人。此次美國-東盟峰會也是一推再推,由1月拖到3月,直到5月才得以舉辦。
最新版《東南亞態勢報告》也顯示,肯定美國在東南亞的參與度有所增加的受訪者比例(45.8%)較去年(70.6%)大幅減少,認可美國是可靠戰略伙伴的比例從54.7%下跌至42.6%。
李明江向南風窗分析道,東盟對美國的不信任與對中國的完全不同。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主要來自南海問題,而對美國的不信任實際上是擔心美國不重視該地區,沒有足夠多的承諾和政策上的意愿,來更多地參與該地區事務,幫助東南亞維持穩定和保持發展。東南亞國家把美國視為地區安全穩定的維護者,這一認知是根深蒂固的。
在周方冶看來,這次峰會的召開,美國在11月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承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東盟對美國強烈的擔憂和不信任。美國通過峰會表明,即使處于俄烏戰爭中,東南亞依舊是美國的戰略重心。這一步對整個局勢是關鍵的,后續美國會有各種相關工作跟進,東南亞國家也會評估美國是否在開空頭支票。
拜登在峰會上宣布的1.5億美元的援助,被諸多美媒詬病金額“微不足道”,峰會缺乏實質性成果。該筆撥款將用于協助東盟國家發展清潔能源、推動教育,以及加強海事安全及衛生防疫工作。而僅在去年11月,中國就承諾在未來三年向東盟提供15億美元的發展援助,用于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路透社稱美國的經濟籌碼對東盟不夠有吸引力,未能彌補美國與東南亞在經濟領域合作的短板。
對此,李明江認為,在與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方面,美國確有劣勢,但不必過于強調撥款金額的大小。他表示,美國國內政治決定了政府不可能輕易給其他國家提供大額援助,或提出自貿協定、市場準入這類宏大的經貿政策。東南亞國家了解這一客觀事實,對美國也沒有過高的期待。但東南亞國家重視美國市場是很顯然的。另外,李明江補充道,美國目前仍是東南亞第一大投資來源國,這對東南亞經濟也至關重要。93EE35CE-D1BE-4090-A9D4-1C955D4E12EE
“中心”的矛盾
拜登在5月13日下午的峰會上說,“東盟的中心地位處于本屆政府尋求我們都希望看到的未來戰略的核心位置”,并強調他這樣說是真誠的。峰會后的聯合聲明也寫道,美國支持東盟的“中心地位”和團結。
這點也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中有所表述:“美國歡迎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東盟,在東南亞發揮領導作用。我們贊同東盟的中心地位,支持東盟努力為該地區最緊迫的挑戰提供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塑造并維持在區域結構中的“中心性”,在地區機制中發揮主導作用,一直是東盟發展對外關系的基本原則,被寫入指導文件《東盟印太展望》。
但就戰略目標而言,美國“印太戰略”所服務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東盟在《東盟印太戰略展望》中追求的“中心地位”并不一致。“印太戰略”中對抗中國的色彩,也與東盟強調的包容、開放和平等截然不同。東盟已經表明,他們不愿在相關合作上將中國或者俄羅斯排除在外,這與美國的利益訴求存在分歧。
在分析人士看來,美國主導的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以及正在成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小多邊機制,正在稀釋東盟的“中心”地位。
李明江認為,下半年到年底,東南亞國家預計會與美國就加入IPEF進行具體商談。他表示,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下的一些小多邊機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威脅到東盟的中心地位,東盟各國領導人也已經很明顯地感知到這種威脅。
近些年,美國在把雙邊同盟逐步推向多邊化。李明江表示,QUAD、AUKUS是美國為主導的地區安全領域架構的一部分,它會對東盟在地區安全領域的引領作用造成制約,無疑會沖擊到了東盟的中心地位。“但這些機制尚未出現取代東盟中心地位的態勢,因為無論是AUKUS還是QUAD,目前范圍都還比較小,而且局限于非傳統安全,以威懾為主。”
不過,李明江補充道,這些聯盟有擴大的趨勢,尚不清楚能夠擴大到什么程度,比如韓國、越南是否會加入QUAD。
對于周邊區域出現強軍事聯盟,東盟是極為敏感和抵觸的。若東盟國家在后續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小多邊聯盟,這甚至可能會導致東盟瓦解。
周方冶表示,對于周邊區域出現強軍事聯盟,東盟是極為敏感和抵觸的。若東盟國家在后續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小多邊聯盟,這甚至可能會導致東盟瓦解。
擔心冷戰,不想選邊
在美國-東盟峰會之前,坎貝爾稱臺灣問題和俄烏戰爭將會是討論的問題之一。但在會后的聯合愿景聲明中,卻完全沒有提及臺海問題,也沒有出現“中國”字眼,只提及了維護南中國海和平、穩定和繁榮。針對俄烏戰爭,也沒有提到俄羅斯,僅表達了對烏克蘭主權、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尊重。
從東盟的表態來看,其保持了一貫的中立性和自主性。
現在中美競爭對東盟來說還是屬于可控范疇,中美關系有競爭也有合作。因此,目前的中美戰略競爭態勢下,東盟的“大國平衡”外交還有一定的操作空間:一方面避免公開選邊站,繼續堅持開放、平等和包容原則;另一方面通過維持內部團結,保有自主權和中心地位。

不過有學者指出,如果中美關系進一步往對抗方向發展的話,部分東盟國家就會面臨選邊的壓力。而且,東盟在處理地區事務上面的引領作用,它的中心地位,不可避免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東盟國家不希望看到中美出現新冷戰或是走向全面對抗,它們希望中美關系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既不要太緊密成為“兩國集團”(G2),也不要走向完全對抗,讓小國被迫選邊。
從東盟的表態來看,其保持了一貫的中立性和自主性。
周方冶分析道,對于東南亞各國來說,現在或許有“寒冬將至,多穿棉衣”的心態。“它們對可能出現的冷戰感到恐懼,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是第一位的,甚至要考慮如何在新冷戰格局下生存。況且目前,它們無法預測,中美若徹底走向對抗,誰會是最后的贏家。”
在李明江看來,目前東盟國家還沒有到成為中美地緣政治工具的程度,尤其是東盟國家有著加強東盟團結的共同意愿,希望以東盟多邊機制,用四兩撥千斤的方式來應付中美博弈。東南亞各國利用東盟的集體性力量,現在基本上可以維持住中立地位。93EE35CE-D1BE-4090-A9D4-1C955D4E12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