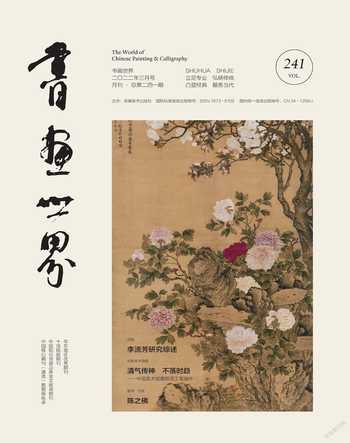清氣傳神 不落時趨
李星



工筆畫作為一種繪畫樣式,反映了中國繪畫的獨特審美品位。中國美術館藏古代繪畫作品約600件,其中有相當多的作品是由鄧拓先生捐贈,而除了宋元時期的作品10余件之外,其余皆為明清時期繪畫。其中,工筆畫作品數量不多,但不乏名家力作。在此,筆者試通過對館藏古代工筆畫尤其是明清工筆作品的概觀,探究其時代審美特征。
宋以前,工筆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可謂一直是主流,傳統工筆畫起源于魏晉,興盛于唐代。五代時期,以徐熙、黃筌為代表的工筆畫家形成了“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兩種不同的風格,對后世工筆畫影響深遠。此后,宋朝延續了唐文化的繁榮,在宋徽宗的倡導下,畫家們非常重視寫生和對客觀物象的觀察,此時期的工筆花鳥畫發展達到鼎盛狀態。進入元代,官方畫院較前代呈現衰微,在“復古思潮”的影響下,以趙孟為代表的元初畫家倡導繪畫要有“古意”,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元代及之后文人畫家們的藝術追求。自明、清以來,水墨寫意的潮流使得工筆畫這類創作方式日趨邊緣化,但在宮廷畫院和文人士大夫中仍保留著工筆畫的一席之地:一部分畫家因循守舊,拘泥于傳統的程式和技法;同時另一部分畫家致力于突破固有的局限。后者主要代表畫家包括邊景昭、林良、呂紀、仇英、惲壽平、陳洪綬、沈銓、郎世寧等人,這些畫家的積極探索極大地豐富了工筆畫的表現語言。
其中,明代院體花鳥畫在繼承五代、兩宋工筆重彩傳統的基礎上,又演化出獨特的形態,出現了水墨寫意、設色沒骨等不同風格與技法,進入了繼宋代之后院體花鳥畫的又一繁盛期。明代院體花鳥畫的傳承與發展,既豐富了花鳥畫體系,同時對后世的花鳥畫創作以及整個繪畫史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呂紀作為明代院體畫代表人物,其花鳥初學邊景昭,并受林良水墨畫法影響,后遍學唐宋諸家名跡,終自成一體,將工筆重彩與水墨寫意相結合,以此豐富、發展了工筆重彩花鳥畫的技法。呂紀的《牡丹白鷴圖》(圖1),整幅畫面呈現出一種秾麗、富貴的氣息,畫面中心的幾束粉白牡丹間,一只白鷴立于湖石之上,其視線又延伸至石下的雉鳥。白鷴的尾羽在牡丹襯托下顯得華美勁健,其上方幾根桃枝斜出,四只鳥雀棲于枝頭,相互鳴叫,使整幅畫面具有百鳥爭春的景致,有別于宋代工筆畫的纖巧細致之風。
仇英初師從周臣學宋人院體畫,后與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吳門畫家結交,其畫開始追求文人筆墨意趣。他在收藏家項元汴家中數十年,“覽宋元名畫,千有余矣”(仇英《秋原獵騎圖》項元汴之孫項聲表題跋),其臨摹功力日益精湛。在繼承唐宋傳統的基礎上,仇英吸收民間藝術與文人畫之長,形成了一種雅俗共賞的風格。他的《采芝圖》(圖2)巧妙地將工筆人物與青綠山水結合為一體,畫面中部煙云繚繞,一位高士佇立于山石之上,衣袂隨風飄動,神情安詳地注視著遠方。盤曲的松樹下,一位童子正采摘靈芝,在遠處云煙中,墨竹搖曳,兩抹淡淡的青山更顯悠遠。畫中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生動,筆法精細且流利,樹石勾勒綿密秀潤,青綠設色清麗古雅。此幅作品生動地表現了高士恬淡、清靜的心境,富有溫雅脫俗的格調,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趣味。董其昌曾評價仇英道:“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伯骕,精工之極而又有士氣,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極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董并稱仇英是“趙伯駒后身”,可見其對仇英的工筆人物和青綠山水之推崇。
至唐寅、仇英之后,明代人物畫因表現羸弱的病態感而備受詬病,五官沿襲程式,體態柔弱纖細。而在時習漸衰的形勢下,明末出現了一批以陳洪綬為代表、畫風迥異的人物畫家。陳洪綬博覽宋元古畫,重視對傳統正脈的研究和繼承,他師其精神、自辟乾坤,博采眾家之長為己用,將文人水墨畫的意趣提煉并應用在工筆人物畫中,并創造出一種戲劇化、“怪誕”的筆墨語言。中國美術館藏陳洪綬(款)《人物圖》(圖3),款識曰“洪綬寫壽”。畫面左下方,一位老者坐于石幾之上,抬著右手正在說些什么,右側一老婦手持茶盞坐于蕉葉之上,與老者相對而坐。畫面中心一位高士正倚古石怪木而坐,蕉葉鋪地,身旁置一古琴,其一手執扇,一手托腮,眉目低垂,若有所思。老者身旁的石桌上供著蟠桃和靈芝,象征著長壽,另有一盤靈芝正置于爐上烘煨,旁邊還有一位侍者手持執壺。整幅畫面典雅簡潔,著色淡雅,人物衣紋細致,用線更顯柔潤老練,在平淡中蘊含著變化,顯得古樸自然。此幅作品有別于陳氏中年方硬的用筆和極強的形式感,它顯示出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作品中多采用迂回圓潤的用線方式,并更加注重表達人物的精神,可謂開辟了工筆人物畫之新風。
明代之前,工筆作品被泛稱為“院體”繪畫;明末之后,“工筆畫”一詞才開始逐漸使用,將工筆畫和寫意畫在名稱上加以區別。清代寫意繪畫盛行,工筆繪畫技法發展無不受其影響。惲壽平在這一背景之下,繼承北宋徐崇嗣的畫法,將文人寫意畫技法融入沒骨花鳥畫。他“一洗時習,別開生面”,廣涉宋元諸家,汲取古人意氣,并注重寫生,以極似求不似,把“仿古”與“寫生”有機結合。惲壽平不僅使失傳數百年的沒骨技法得以復興,還開創了清代繪畫史上影響深遠、傳播廣泛的“常州畫派”,這一派之新風更推動了此時期工筆畫的發展。作品《紫云珠帳》(圖4)正是惲壽平的代表作之一,畫面整體構圖呈“S”形,藤蔓相互纏繞,葡萄葉和果實穿插其間。他直接以顏色或墨筆渲染成形,用筆著色清新淡雅,色調層次分明,在葉筋處僅用線條勾勒。畫面既有工筆畫的逼真形態,更具寫意畫的生動神韻,整體筆濕墨潤,清氣傳神,可謂別具一格。
沈銓作為清中期宮廷花鳥畫家的代表,其技法遠宗黃筌寫生法,近取邊景昭、呂紀等人。他工寫花卉、翎毛、走獸,畫風謹嚴工細,賦色妍麗,常以極精細的勾勒渲染取勝。《松鹿圖》(見扉頁)為沈銓繪畫中多見的題材,畫面一棵蒼松垂于峭壁之上,蒼松之下湍急的江水拍打著礁石和崖壁,遠山縈繞在云霧之中。懸崖之上有四只梅花鹿,成雙成對,坐臥者相互依偎,站立者或俯首或仰頭觀日。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祥瑞之獸,沈銓畫鹿作品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在構圖方面的巧妙,使畫面整體虛實更迭、動靜結合、陰陽相生。梅花鹿神情各異,勾勒精細,絨毛絲絲可見,表現了畫家精湛的寫生功夫。松石與波濤的用筆兼工帶寫,墨色濃淡相宜,皴法靈動多變,體現了其高超的水墨表現能力。在“黃家富貴”與“徐熙野逸”之間,沈銓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并在工筆花鳥走獸與寫意山水樹石之間構建出自己的獨特面貌。雍正年間(1723—1735),沈銓應日本之邀,東渡傳授畫藝,歷時三年,其細密精致、色彩艷麗的畫風深受日本人推崇,成為“南日本畫壇影響深遠,被日本譽為“舶來畫家第一人”。
康熙年間(1662—1722),郎世寧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被招入內廷供奉,成為宮廷畫家,其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參與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工作。郎世寧擅長畫人物、花卉、走獸,注重明暗、透視,設色富麗,精工細致,融會中西繪畫技法,自成一家。此幅《九鶴圖》(見扉頁)為絹本設色,蒼松盤根錯節,聳立于巨石之旁,九只仙鶴或棲于樹干,或展翅齊飛,或立于山石振羽,或在溪邊飲水,整幅畫面給人以祥和安寧之感。畫中樹石多用中國傳統筆墨技法描繪,并注重皴染和明暗的過渡。其中飛禽造型逼真,畫法采用勾勒、填色、暈染等方式,使其形體光影變化細膩,富有立體感。在中國筆墨意趣基礎之上,畫面相對削弱了西畫中強烈的光影對比和焦點透視效果,以此符合東方特有的審美意趣。此作呈現出清后期工筆畫吸收西洋繪畫寫實技法并融通后的典型面貌,充分體現了郎世寧在中西繪畫技法上的探索精神,其開拓的“中西合璧”繪畫新風,對當時的宮廷繪畫與審美影響甚大。
縱觀明清工筆畫的發展,無不受當時文人畫風格的影響,在表現技法上將工筆設色和水墨寫意互參,在題材的選擇和表現方式上更為注重主體意識的表達,在畫法上探索中西畫法之融合,這些特征都推動著此時期工筆畫的發展。明清之后,由于文人畫的興盛和水墨寫意繪畫技法的成熟,工筆畫逐漸趨于邊緣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筆畫名家寥寥,數量之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回溯明清之際,工筆畫雖然相較于宋、元鼎盛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在題材、構圖、技法等方面的嘗試仍有諸多可取之處,或可為后世提供些許啟迪與借鑒。
約稿、責編:金前文5C517A3E-3FFC-4BE7-ABB9-81FA0EECCD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