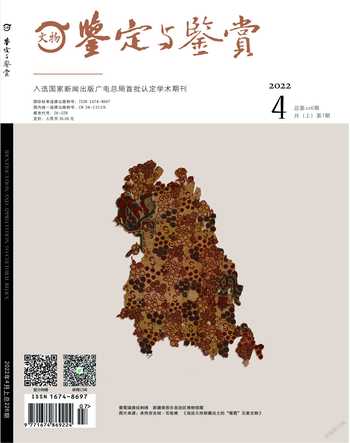金代家族墓出土文字所見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
辛巖
摘 要:家族墓地由于其營建和使用時間更長,更能體現出某些因素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的變遷,因此往往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特定時期的家族發展史、家族內部關系,以及更加宏觀層面的文化發展變遷和社會等級結構。新中國成立以來,金代家族墓中出土文字的考古發現數量頗豐,為系統整理各家族發展脈絡并以此進一步探討金代社會形態提供了良好基礎。
關鍵詞:金代;家族墓;出土文字;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7.023
0 引言
金朝是我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政權,完顏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稱帝、建立金國:“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封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①金朝的疆域東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北達外興安嶺,西部沿今內蒙古包頭、山西大同、陜西延安、甘肅臨洮等一線與西夏王朝接壤,南沿秦嶺、淮河一線與南宋王朝劃界。②金朝在其存續期間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并在已有的考古發現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對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的研究是考古學的重要議題之一,家族墓地與單一的墓葬相比,由于其營建和使用時間更長,更能體現出某些因素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的變遷,因此家族墓地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特定時期的家族發展史、家族內部關系,以及更加宏觀層面的文化發展變遷和社會等級結構。新中國成立以來,金代墓葬及家族墓的考古發現數量頗豐,同時,目前發現的各金代家族墓中已發現多方墓志或買地券,這為系統整理各家族發展脈絡、并以此進一步探討金代社會形態提供了良好基礎。筆者將以金代家族墓葬中出土的墓志、買地券等出土文字為基礎,觀察所屬家族的發展脈絡,以期對金代的社會形態及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做進一步探討。
1 金代家族墓出土文字資料概述
目前金代家族墓中的出土文字有以下幾例:
北京市烏古論窩論家族墓地中,烏古論窩論墓③中出土《大金故紫金光祿大夫烏古論公墓志銘》,烏古論元忠夫婦合葬墓中出土《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判彰德尹駙馬都尉任國簡定公墓志銘并序》及《大金故魯國大長公主墓志銘》。
北京市海淀區南辛莊張氏家族墓地④M1出土《大金故宜(武)(將)(軍)(騎)都尉(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銘》。
北京魯谷金代呂氏家族墓地⑤M35呂嗣延墓出土《大金故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呂公墓志銘并序》,M56內出土《故朝請大夫政事舍人充史館修撰知薊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府君墓志銘并序》,發掘區內發現呂士安墓志。
河南焦作馮氏家族墓地⑥M3馮汝籍墓內發現一塊銅質“合同契券”,為馮汝籍墓的買地券。
山西汾陽東龍觀金代家族墓地⑦中,北區M48內出土地心磚一塊,南區M3內出土買地券一塊、地心磚一塊,南區M5內出土買地券二塊、地心磚一塊。
大同市南郊金代家族墓地⑧M2內出土墓志一方,為《進義校尉前西京大同府定霸軍左一副兵馬使陳公墓志銘》。
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家族墓地⑨中的董明墓、董堅墓兩座墓葬的門額上均懸掛有買地券一塊。
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家族墓⑩墓室后室南壁門上方有墨書磚質地券一方,前室南壁墓門上方砌磚質地碣一方,此外在墓室內其他部位有多處銘刻。
山西稷山縣馬村金代家族墓地kM7段楫墓北壁鑲嵌一塊磚刻小碑,銘曰“段揖預修墓記”,為此墓的買地券。
山西聞喜縣小羅莊金代家族墓地lM2出土買地券一方。
河北省新城縣時立愛、時豐家族墓地m中,時立愛墓葬中出土時立愛墓志一方,為《大金故勤力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謚忠厚鉅鹿郡□食邑壹萬戶食實封壹千戶時公墓志銘》,時豐墓中出土時豐墓志一方,為《大金故禮賓使時公墓志銘》。
通過初步整理,可以發現目前出土文字的墓葬涉及金代女真族貴族、漢臣及漢族普通百姓,形式為墓志或買地券。這些墓志及買地券中大多記載了墓主人的生平、墓主所屬家族世系以及建墓、下葬的過程,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2 家族發展脈絡及姻親婚配選擇所見金代社會結構及社會分層
通過整理金代家族墓中的出土文字,了解不同家族的發展脈絡、家族參與國家政治情況和姻親狀況,加之了解平民墓葬中出土的買地券的內容,我們可以對金代社會“女真族貴族—漢族入仕官員—漢族平民百姓”的社會結構產生比較清晰的認識。
2.1 女真族貴族
關于屬于金代女真貴族的烏古論氏—烏古論窩論屬烏古論部,該部落是女真族產生之初便已存在于族內的一支重要力量,及至女真族入主中原前后這一時段,烏古論部落已經不斷發展壯大,并參與了女真族對漢地的征伐戰爭。窩論墓志記載:“正隆之初,起十三貴族猛安以控制山東,公家遂居萊州。”n對宋戰爭中的軍功也奠定了窩論以及整個烏古論氏在女真族統治階層中的政治地位,烏古論窩論在死后“加贈金紫光祿大夫”。窩論有子四人,長曰掃和,次曰撒改,次曰阿魯谷,次曰元忠;有女三人。窩論的七位子女中以元忠一支發展最為興盛。根據元忠墓志記載,元忠娶皇長女豫國公主為妻,在金朝與宋、達靼的外交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死后封“開府儀同三司勛上柱國,食邑戶三千,食實封戶三百”o,其后代有五子二女。窩論有孫子十一人,孫女八人。窩論的子輩及孫輩入仕者均在朝中的軍隊系統中任職,其家族勢力頗為興盛。
關于烏古論家族的姻親婚配狀況,由出土墓志可知,除烏古論元忠娶豫國公主為妻外,烏古論窩論的三個女兒,“長適故太子太師榮王爽上之從弟也,次適故原王長子奉國上將軍阿乳,次適故耨碗溫都太師侄回回孫”;烏古論掃和及烏古論撒改之女(共五人)皆“適貴族”;烏古論元忠的兩個女兒“長女適榮王之子符寶祇候,長壽,特封金源郡夫人;次適皇再從侄懷遠大將軍奉御咬住”p。烏古論氏的女性后代在進行婚配選擇時也全部選擇女真族貴族—且男方大多也屬于軍隊系統。由此可見,烏古論窩論家族成員的婚姻十分看重家族的門第及政治等級,也由此可知金代的女真族貴族在進行姻親婚配時的“女真族族內通婚”,以及加強軍、政聯姻的傾向。
2.2 漢族入仕官員
關于金代的入仕漢臣,通過分析墓志內容可見呂氏家族、石氏家族、陳氏家族及張氏家族的家族發展脈絡及姻親狀況。
縱觀北京魯谷金代呂氏家族墓地,以呂嗣延為基準進行觀察:其太祖呂密,“贈太子洗馬”,其妻馬氏“封韓國太夫人”q。其祖呂德方,為“遼統和中舉進士甲科,官至檢校司空順州刺史”,其妻南氏“封魯國郡太夫人”r。其父呂士安,“重熙中舉進士,官至左散騎常侍奉陵軍節度使”,先后娶妻三人,“先娶隴右李氏,度支判官可象之女,次娶南陽韓氏,故宣徽南院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紹文之女……未及,封蔭并早謝于世,今夫人天水趙氏,金州團練使嗣之女”s。及至呂嗣延一輩,呂氏家族隨著呂嗣延考取科舉而入仕金朝,呂嗣延為其父與第三任妻子天水趙氏所生,“公舉□昌中進士,歷安德州中京內省判官,豐應二州觀察判官,中京留守,推官灤河、遵化二縣令。皇朝天會初授西京鹽鐵判官。四年改殿中侍御史。從王王師南伐太原,以勞遷太常少卿”,其妻南陽韓氏“崇文公之六代女孫也”t。呂嗣延生子二人、生女一人,“長曰巖,次曰介石,女適門祇候韓?。巖……官至信武將軍燕都倉使。介石……進士乙科,官至中憲大夫,安州刺史,皆卒于官”u。呂嗣延的孫輩有孫子七人,“忠節保義,校尉衛州酒使……忠衛忠顯,校尉監中都醋使司……忠美修武校尉,酒房都監,亦皆卒于官……忠敏舉天德進士,高弟令為南京路都轉運副使……忠翰舉貞元進士第一,為莫州刺史……忠彥武略將軍靈石尉……忠一進義校尉……”;孫女四人,“一適承信校尉韓據,三為浮圖氏,其次以疾示滅”v。呂嗣延的曾孫輩,曾孫有八人,其中“適、邈并進義校尉”,曾孫女六人,其中“一適應奉翰林文字趙承元,一適鄉貢進士王陟,余尚幼”w。由此可見,呂氏家族由遼至金世代均由考取科舉的方式進入仕途的家族發展歷程,在呂嗣延一輩實現了從“遼官”到“金臣”的轉變,以及在進行姻親婚配時一直以同為入仕的漢族官宦家族為選取標準。整個家族在墓志記載可見的發展歷程中,維持了家族長期的人丁興旺以及歷代子嗣均享有較高的社會政治地位。
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金代漢臣時立愛家族中。以時立愛為基準對其家族進行觀察:時立愛的祖父為時延義,“贈鎮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妻趙氏,“追封岐國夫人”x。時立愛之父時承諫,“贈鎮東軍節度使兼侍中”,娶妻三人,“娶趙氏、張氏、王氏”y。時立愛為時承諫第六子,曾在遼代通過科舉入仕,后來在遼、金兩朝為官。時立愛“遼大康九年登進士弟,授秘書省校書郎,泰州軍事判官”,最終至“兼漢軍都統,累官至太子少師”;及至金代,則從“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諸行宮都部署”,一直至“(天會十五年)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進封鄭國公,致仕。天眷三年,官制行易開府儀同三司。皇統元年以受尊號,恩封鉅鹿郡王”。時立愛娶妻二人,李氏、王氏“皆追封岐國夫人”z。時立愛生子三人,長子“未名而卒”;次子時漸,官至“太子左翊衛校衛”;繼子時豐,因“汴誠破,皆有功,為士卒先”而“累遷禮賓使”,時豐娶妻張氏,為“靜江軍節度使少微之孫女”。時立愛生女三人,其中“長適進士柴思議”“次為比丘尼,法名思瓊,賜紫方袍,號聰慧大師”“次適中大夫,前橫海軍節度副使左淵”。時立愛有“孫男三人,重國承事郎登,皇統二年進士第,均國昭信校尉,門祇候,彥國習進士業”;孫女六人,其中“長侍奉議大夫,析津府安次縣令,襲夷鑒;次適承奉郎,前大同府長清縣承王克溫;次適進士趙然,后全歸”。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時氏家族在發展過程中同樣經歷了由“遼官”向“金臣”的轉變過程,不斷通過科舉入仕以求家族的發展,在婚配時以同屬漢族入仕官宦為選取標準,從而在客觀上達到不斷鞏固家族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目的。
北京市海淀區南辛莊張氏家族墓地和大同市南郊金代陳氏家族墓地與前述三個家族相比,墓地體量及記載所見的家族規模極小。張氏家族以墓主張震作為基準進行觀察:其祖父張維保曾任遼代樞密使。其父張□讓曾任鄧州觀察使、知景州軍州事。張震本人早期就職于無極縣,后來官至(宣)武將軍,且“以曾祖樞密蔭人充內,供奉班祇候,授左班殿,直始監招燕州酒次,監冀州□□□□酒次,監無極縣酒次,任真定府續錦使,次除雄州軍器庫使□,任差榷(佑)安軍,次監□□□□”。張震娶妻韓氏,“娶韓氏為清河縣君,乃本朝□尉相公,(緝)資(鼓)之(女)”。大同市南郊陳氏家族墓地,以M2墓主陳公為基準進行觀察:其父陳玉曾從軍;陳公本人則“自亡遼己前,亦補定霸籍中。造至本朝,招集捕捉,累有勞效,自在仕三十有余……太守嘉其行能,考其功績,□超外左一副兵馬使,兼保奏朝廷教,加進義校尉”。陳公之子陳德輝“以習筆吏為業”,陳公之女嫁于同郡進士許生夫。兩個家族的家族發展過程與婚配情況進一步鞏固了上文中關于金代漢族人家族發展軌跡及婚配標準選取的論述。
2.3 漢族平民百姓
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材料可以發現,諸多金代漢族平民的家族墓地中出土了買地券,基本見于現山西地區的家族墓中,材質大多為石質或陶制,放置于墓室內地面上、或懸掛于墓室內壁之上。根據出土買地券墓葬的特征可以推測,使用買地券的基本為當時的平民百姓,買地券的格式和內容較為一致。以東龍觀金代家族墓地南區M5王萬墓出土的買地券為例,其內容為:“維明昌六年五月十二日汾州西城崇德鄉居住王立,伏為本身病患,今來預修細砌墓一座,故龜筮協從,相地襲吉,宜于本州西河縣慶云鄉東景云村西北一里,己未祖園前安厝宅兆,謹用錢九百九十九貫文,兼五彩信幣,買地一段,新封園一座,南北長一十三步五分二厘,東西闊一十二步五分,東至甲乙,西至庚辛,南至丙丁,北至壬癸,內方戊己,分掌擘四域,丘墓神祇,封步界畔,道路諸神,齋整阡陌,千秋百歲永無殃。答今以脯修酒飲百味香新奉為信契。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瑩安厝,已后永保修吉,知見人乙卯,保人壬午,直符丙申,故氣邪精不得干擾,先有居者永避他處。若違此約,此地掌吏使者自當其禍,王立悉皆,安吉急急如五方使者女青律令”。
買地券存在的意義是向地下的神祇宣告亡人在陽間的生命已經結束、正式成為冥界的一分子,并通過“買地”取得在陰間的居留權和居住地,且此種權力受到諸如女青律令之類冥界法律的保護。通過觀察金代家族墓中已出土買地券的內容可以發現,其篇幅大多較短,并不記載墓主生平及墓主所屬家族世系,而主要記載墓地的占卜選址、買地的耗費與過程、墓地塋域范圍、立契過程以及違約的懲罰性條款,反映了墓主基于傳統的鬼神信仰及風水堪輿思想基礎上的封建迷信思想。同時,雖然買地券內多無關于家族世系的記載,但金代平民家族墓地仍會通過墓葬的有序排列表達一種長幼有別的尊卑、等級觀念,以及對于家族世系的尊重。金代漢族平民家族墓中基本無常見于女真族貴族及漢族官員墓中常見的墓志,由此可見對買地券或墓志選擇的區分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當時的社會分層。
3 結語
從上述金代女真族貴族及漢族官員的家族發展脈絡和姻親選擇以及平民墓葬中買地券中記載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窺見金代在政治結構方面的社會階層劃分。
首先,女真族貴族的統治階層以及各層級的漢族官員在后輩的婚配選擇過程中會以與自己所屬同一族群、政治地位同一層級的作為基本標準,從而不斷強強聯合,加強自己家族在某一領域的政治影響力。雖然依據文獻我們可以發現金朝建國后居于統治地位的女真族仍會啟用漢臣,使其參與國家的管理,但僅就出土文字資料而言,還未發現女真族與漢族通婚的案例,女真族貴族的婚配選擇基本選擇女真族貴族,而漢族官吏的婚配選擇則基本為漢族官吏。
事實上,金代的女真族統治階層在治國理念層面對于社會中的各種思潮以及漢族文化在很多方面呈現出了較為開放的態勢。例如,女真族貴族烏古論元忠次女后出家,改信佛教—“祇候女二人……次為尼,賜號通悟大師”。又如,女真族也在漢族人的影響下逐漸不斷完善本族的宗廟和祭祀制度:“金虜本無宗廟,祭祀亦不修。自平遼之后,所用執政大臣多漢族人,往往說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何可不念?虜方開悟……至褒立,還亮父德宗于外室,復奉安父懿宗宗廟于太廟,其昭穆各有序。”但在國家治理、各家族保障自身發展等更多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層面,金代社會仍存在較為明確的、以民族作為劃分標準的階級分層。
其次,就金代的漢族人內部而言,也體現出入仕官員與普通平民百姓的階層差別,在一些葬俗的“選擇”上體現出了不同的傾向。例如,在對于買地券和墓志的使用選擇上:金代漢臣的家族墓地中未發現買地券,而平民家族墓地中也未發現墓志。至于此類葬俗是否在當時已經形成定制,筆者認為這有待于對傳世文獻及地下出土文獻的進一步發掘后才能形成定論。而通過科舉入仕,則成了金代漢人乃至前朝臣子維持現有政治地位以及實現階層躍升的重要途徑。
注釋
①脫脫,等.金史:卷二:本紀第二:太祖[M].北京:中華書局,1975:26.
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Ⅱ[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990.
③袁進京,王武鈺,趙福生.北京金墓發掘簡報[M]//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一輯.北京: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1983.
④秦大樹.北京市海淀區南辛莊金墓清理簡報[J].文物,1988(7):56-66.
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魯谷金代呂氏家族墓葬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⑥河南省博物館,焦作市博物館.河南焦作金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9(8):1-17,97-99;河南省博物館,焦作市博物館.焦作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J].中原文物,1980(4):1-6,67-70.
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陽市文物旅游局,汾陽市博物館.汾陽東龍觀宋金壁畫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⑧王銀田.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畫墓[J].考古學報,1992(4):511-527,541-548.
⑨楊及耘.侯馬101號金墓[J].文物季刊,1997(3):18-22;暢文齋.侯馬金代董氏墓介紹[J].文物,1959(6):50-5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侯馬65H4M102金墓[J].文物季刊,1997(4):17-27.
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侯馬102號金墓[J].文物季刊,1997(4):17-27.
k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3(1):45-63,99-10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山西稷山馬村4號金墓[J].文物季刊,1997(4):41-46,48,51.
l楊富斗.山西省聞喜縣金代磚雕、壁畫墓[J].文物,1986(12):36-46,105-106.
m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J].考古,1962(12):646-650,8.
n袁進京,王武鈺,趙福生.北京金墓發掘簡報[M]//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一輯.北京: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1983:68.
o袁進京,王武鈺,趙福生.北京金墓發掘簡報[M]//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一輯.北京: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1983:71.
p袁進京,王武鈺,趙福生.北京金墓發掘簡報[M]//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一輯.北京: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1983:69.
qrtuvw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魯谷金代呂氏家族墓葬發掘報告:附錄三:金代呂嗣延墓志考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169.
s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魯谷金代呂氏家族墓葬發掘報告:附錄二:遼代呂士安墓志考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154-155.
xy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J].考古,1962(12):647.
z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J].考古,1962(12):647-648.
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J].考古,1962(12):649.
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J].考古,1962(12):64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陽市文物旅游局,汾陽市博物館.汾陽東龍觀宋金壁畫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89.
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20.
袁進京,王武鈺,趙福生.北京金墓發掘簡報[M]//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一輯.北京:北京歷史與考古叢書編輯組,1983:72.
張棣.金虜圖經:宗廟:大金國志校正:附錄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6: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