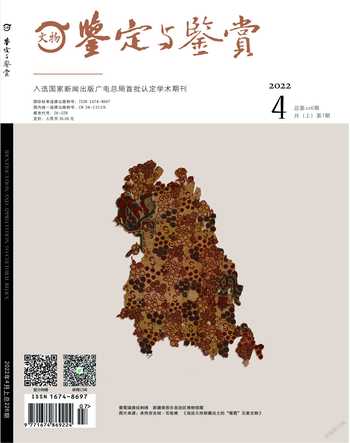補史乘之闕
楊燕
摘 要: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多以圖像及實物為主。服飾依附于人,描繪人物的繪畫作品自古有之且不乏珍品,對歷代人物畫也可見傳記、鑒藏及品評著述,從中亦可窺見所處時代的服飾風貌。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支,文獻及一些重要的史料在服飾史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夠關注和重視。與繪畫密切相關的畫學文獻中,在論人物畫部分有對服飾形制、色彩、紋樣以及衣冠之制的相關內容涉及,可以作為服飾史研究的補漏考證之用。
關鍵詞:畫學文獻;古代人物畫;服飾史;史料考證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7.026
對中國服飾史的研究,與之密切相關的研究史料有文獻、圖像和實物。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支,文獻應得到進一步重視。近年對服飾史的研究側重“以圖證史”,圖像提供的研究信息和圖像學研究方法確實很受用,但有時畫家所繪的人物形象受個人創造性及流傳過程中的變更等原因,可能會使人誤讀人物畫傳達的圖像信息。因此,以“以衣冠而辨畫”亦可能存在陷阱。涉及中國古代服飾史研究的資料性文獻非常龐雜,正史、政書、類書、辭書、文學、專業論著及檔案中都含有相關記載。①其中,與人物畫有密切相關性的畫學文獻著作為研究服飾史提供了圖像以外的證據,譬如畫家傳記、書畫鑒藏等著述,為解讀人物畫所包含的服飾信息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理論支撐,同時也可補漏服飾史的相關研究。論及畫學文獻與服飾史研究的開篇之作是包銘新先生的《畫學著作與中國染織服飾史研究》。②本文將在時賢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對歷代畫學著作中論及人物畫部分加以梳理,分別從人物畫與服飾史關系和畫學文獻中的服飾形質、色彩、紋樣以及畫學著作中的衣冠之制幾個方面加以論述。
1 人物畫與服飾史之關系
沈從文先生在論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方法時,從歷史形象的角度出發,將實物作為“出土的圖像資料”③,統一歸類于圖像類型,與文獻相結合進行探索研究。由于紡織實物是一種有機物,其脆弱的屬性使其在考古遺跡中難以大量如實保存下來,而繪畫、壁畫、雕塑、攝影等可以說是研究服飾史另一類重要的圖像資料和信息。其中,傳世人物繪畫作品在研究服飾史中扮演了圖像資料的角色,此外繪畫作品還可見題跋,這些也可作為文獻資料加以研究。人物畫對于研究服飾史而言是文獻、圖像并存于同一實物載體,卷軸人物畫為服飾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如卷有引首拖尾,軸有詩堂、綾邊為題跋提供了空間,使畫家可以書畫互彰、詩畫結合,也體現了卷軸畫有別于壁畫、年畫的“卷軸氣”④,如果有畫家所畫前一時代服飾形象尚待詳考時,從題跋中也可窺見一些證據,以此來甄別某一時代服飾風貌的真實程度。⑤
唐五代之前的存世服飾實物較之明清和近代要少許多,因此傳世繪畫就成為研究服飾史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盡管早期卷軸人物畫大多為后世摹本,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忠實原作而反映當時服飾風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人物畫在三大畫科中產生的時間最早,也是與服飾史研究關系最密切的。人物畫以描寫人物為主,是直接反映現實的畫科,具有明確的時代特征,畫家以現實生活為藍本,描繪生活中的人物,這不僅反映了當時的審美情趣、繪畫水準,也忠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服飾。這些人物的著裝不僅是為研究歷代服飾史、服飾文化帶來了便利,還為一些在斷代上有爭議的繪畫作品解開謎團提供了證據。⑥在“垂衣而治”的古代中國,服飾作為人物身份的重要表征,帶有美化傾向的寫實性特征,人物畫中的服飾不僅再現了畫中人物所處時代的衣冠制度,也融入了畫家的繪畫技巧和審美觀,使服飾比它本身更完美。
人物畫中重要的畫科“仕女畫”以女性形象及婦女為主題。《唐朝名畫錄》將以女性形象見長的周昉列為“神品中”,排名僅在“畫圣”吳道子之后,稱周昉“畫仕女為古今冠絕”⑦。而約兩百年后宋代的郭若虛在他的《圖畫見聞志》“論婦人形象”中,把仕女畫描述成當時已經衰落退化的一個畫科,認為“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于眾目,不達畫之理趣也”⑧。再到米芾在《畫史》中北宋文人對女性題材繪畫的極端否定:“鑒閱佛像、故事圖,有以勸誡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是煙云霧景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仕女翎毛,貴游戲閱,不入清玩。”⑨當然這些著作多出于文人和文人畫家之手,他們習慣以自然山水為重心。元代的湯垕在《畫鑒》中也認為“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⑩。他們根本不會想到后世明清宮廷卻極為盛行美人圖而成為通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對其古今優劣如何評價,人物畫中服飾的表現往往反映了畫家所處時代的印記。此外,還有以表現人與馬的活動為主的人馬畫,人馬畫還可能涉及游樂、出征、狩獵等題材,對研究少數民族以及軍戎服飾也是重要的意義;歷史畫多為宮廷畫家“秉筆直繪”,對于服飾史的研究價值很高,有助于對不同服飾的穿著場合及因穿著者身份而產生的級別限制等問題進行探究;釋道畫主要留存于寺觀、石窟壁畫中,其中宗教繪像中的供養人像是服飾史研究的重要一類,對考證化妝、發式、服飾形制、染織品紋樣等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另有明清小說、戲曲的刻本插圖中的人物形象,也可用作研究服飾之用。
一方面,歷代人物畫是美術史、繪畫史的重要圖像研究資料;另一方面,歷代人物畫也是服飾史的重要的圖像研究證據。其中,歷代畫學文獻也有涉及人物畫的內容信息,雖以離散狀態藏于其中,但一些與服飾屬性及服飾制度的記載可作為完善和修正中國古代服飾史的佐證。
2 畫學文獻中的服飾形質、色彩、紋樣
人物畫中的服飾信息包含有形質、色彩和紋樣。對歷代畫學文獻進行整理,雖然相關內容記載有限,但對服飾史研究所提供的文獻補缺作用亦不可小覷。以下,試舉畫學文獻中有關服飾形制、色彩、紋樣幾個方面的例子來說明其補遺的重要性。
宋代米芾的中國畫品評著作《畫史·唐畫》中有關于唐人冠制的記載十分精彩: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為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箆,所以裹帽則必用箆子約髪,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發角加后,以入幞頭巾子中,箆約發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后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發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于門,背取下掠子箆發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為大不謹也。又其后,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后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為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為重禮,無則為無禮。不知今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為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制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發,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為漣水,古徐州境每民去巾,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著,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逢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也。
米芾所說的唐初舉人和李白所穿的大袖之衣,實際上在唐代似乎只有少數慕古讀書人或隱士高人穿著,一般人已很少穿了,在人物畫中也不多見。不過,可以從米芾提到的“逢掖”大袖衣的描述中確定為上衣下裳,是沿襲春秋以來魯國讀書人所穿(圖1)。k
清代李斗的《揚州畫舫錄》在記述南方女子服裝時,雖然記錄的只是揚州一時一地的制作,其實也反映了全國中上層婦女效法為時髦的衣著色彩:“揚郡著衣裳為新樣,十數年前(乾隆初)緞用八團,后變為大洋蓮、拱璧蘭。顏色在前尚三蘭、朱墨、庫灰、泥金黃,近尚膏粱紅、櫻桃紅,謂之‘福色’。”關于衣著樣式也有記述:“裙式以緞裁剪作條,每條繡花,兩畔鑲以金線,碎逗成裙,謂之鳳尾。近則以整緞折以細裥道,謂之百褶。其二十四折者為玉裙,恒服也。”l從其描述中可知這種樣式的褶裙當時風俗一斑。這類描繪夫婦生活的繪畫作品可以在《燕寢怡情冊》中看到(圖2)。
除服飾形質、色彩外,還有與染織紋樣相關的內容,畫學著作中也有記載,如研究唐代絲綢的團窠紋樣時,就不能不提到“陵陽公樣”。史料記載武德八年(625)敕制官袍上之的“陵陽公樣”m記載于畫學文獻的《歷代名畫記》卷十,關于竇師綸的記載:“竇師綸……封陵陽公。性巧絕,草創之際,乘輿皆闕,敕兼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官至太府卿,銀、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n從畫學文獻記載可以得知唐初竇師綸在成都作行臺官時的創意設計是唐代絲綢的特種宮錦,川蜀織錦工人作的瑞錦宮綾,有對雉、斗羊、翔凰、游麟之狀,章彩綺麗,宜應用于屏風、舞茵、帷帳間。
3 畫學著作中的及衣冠之制
中國古代衣冠之制主要是用于規范人們服飾形制及著裝行為的律令o和禮俗,有時還表現了統治者對服飾違制或奢靡現象的整飭。研究服飾史尤其是服飾制度需倚重文獻,傳統文獻資料有《輿服志》和《儀衛志》以及奏章詔令等正史、政書類典籍等。這類文獻對于服飾制度的記載屬于官方文章,行文簡單而籠統,從人物繪畫的具體語境來看欠缺生動寫實的記錄。畫學著作中的有關服飾之制的記錄可作為文獻的補充。
古人畫人物,特別是畫其前代人物,講求“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業”,故歷代人物類畫論常于開篇詳述衣冠之制。如《過云廬畫論》云:“畫人物,須先考歷朝冠服、儀仗、器具制度之不同,見書籍之先后。”p《山靜居畫論》云:“畫人物必先皆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制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q《圖畫見聞志·卷一·論衣冠異制》:“自古衣冠之制,薦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在鑒別繪畫時,服飾制度是重要的考證信息,如《廣川畫跋·上王繪圖鈘錄》載:“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于載籍,殆唐貞觀所受貢于四海者也。”又有《書李端愨收唐畫乞巧圖》作:“此圖傳世為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舊制,以是知之。”r
唐代張彥遠對衣服、車輿的年代特征和南北異同及其在畫作中的考證進行了詳細敘述:
若論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如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于晉代;幃帽興于國朝。舉凡此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于漢魏,冪籬起自齊隋,幞頭始于周朝(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帽皂向后幞發,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為四角也),巾子創于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于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于今人。芒履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辯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
——《歷代名畫記·卷二·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其中對閻立本畫明妃騎馬用帷帽,以為不合古制。王昭君為漢代人物,而幃帽興起于唐朝s,是唐早期非常盛行的婦女出行之服,帷帽是冪籬的改良,約在南北朝時期由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傳入中原t。另傳世幾種《明妃出塞圖》多宋、明人筆,未見著唐式帷帽。惟宋人繪《胡笳十八拍圖》蔡文姬著帷帽(圖3),和唐人作《明皇幸蜀圖》中所見還相近(圖4)。《胡笳十八拍圖》畫服裝不甚統一,這一部分可能是從舊傳《明妃圖》加以增飾發展而成,而原稿一部分或如所說出于唐人之手。u此為繪畫作品中時空錯亂之病例。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以專門篇幅論衣冠異制,其中對發展至隋唐時期,在當時不分階層均可戴用的男子首服幞頭的樣式及演化有十分詳細的記述:
自古衣冠之制,薦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袞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冪籬。后周以三尺皂絹向后袱發,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腳。隋朝唯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于后魏。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于幞頭之內,前系二腳,后垂二腳,貴賤服之,而烏紗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幞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v
—《圖畫見聞志》
此記述可與正史w及其他文獻x的記載對照以此來相互補漏。而幞頭至宋代已明顯進入官服體系,并對元明清時期的官員首服產生重要影響。
4 結語
對中國古代服飾史而言,考古及傳世的文物以及史料在研究中均具有歷史價值和圖像信息價值。其中,與文獻相結合進行探索研究可最大限度地使研究有理有據,而非主觀臆想。尤其人物畫中描繪的衣著服飾,往往信息雜駁,僅依靠正史記載的衣冠制度有時難免偏頗,在研究時需要結合與此密切相關的畫學文獻進行印證。不過值得謹慎的是,畫學文獻中論述相關服飾史信息是作者明確觀點還是編纂而得的文獻資料須得以厘清。要而言之,將歷代畫學著作與其他史料文獻綜合利用,可補中國服飾史研究之缺。
注釋
①包銘新.中國染織服飾史文獻導讀[M].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06:5-48.
②包銘新.畫學著作與中國染織服飾史研究[J].新美術,2008(3):20-28.
③王亞蓉.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④卷軸畫之雅又被稱為“卷軸氣”,清代畫家方薰稱:“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致論,(而)在乎雅俗。”可以理解為卷軸畫的作者少工匠,故方薰又稱“士人畫多卷軸氣”。參見方薰.山靜居畫論[M].鄭拙廬,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⑤例如,《王蜀宮妓圖》為唐寅早年工筆人物畫代表之作,畫家自題詩:“蓮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綠與爭緋。”后跋曰:“蜀后主每天宮中裹小巾,命宮妓衣道衣,冠蓮花冠,日尋花柳以侍酣宴……”《王蜀宮妓圖》一題為明末收藏家汪珂玉所定,恐有誤。文獻記載:“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俱衣道衣,簪蓮花冠,施脂夾粉,名曰醉妝。”題畫詩反映出蜀后主命宮妓頭戴蓮花冠、身穿道衣這一史實,可作為五代服飾風貌研究的輔證資料。參見沈雄.古今詞話[M].孫克強,劉軍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⑥例如,對《韓熙載夜宴圖》一畫的研究,沈從文、余輝等學者均從衣冠服飾的角度進行了考證:沈先生從男子著綠衣、叉手示敬等角度論證該畫可能完成于宋初北方畫家之手;余輝先生以婦女發飾、男子衣冠為切入點,通過與其他代表性圖像及對應朝代的文獻相比對,推測畫中女子發飾為宋代常用的方額、垂螺髻,韓熙載所戴高巾為東坡巾,并由此得出該畫作者應是南宋畫院高手的結論。參見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余輝.《韓熙載夜宴圖》卷年代考—兼探早期人物畫的鑒定方法[J].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4):37-56.
⑦朱景玄.唐朝名畫錄[M]//陳高華.隋唐五代畫家史料.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5:236.
⑧郭若虛.圖畫見聞志[M].鄧白,注.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6:59.
⑨米芾.畫史[M]//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988.
⑩湯垕.畫鑒[M]//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第二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897.湯垕于此書中大段引述米芾的話以為立論根據,如在討論收藏的時候說:“道釋為上,蓋古人用工于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謂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之論也。”
k衣名“逢掖”(或“馮翼”)由《禮記·儒行》篇而來。“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稱:“逢,大也,大掖即大袂禪衣。”
l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M].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
m唐朝官服的袍服形制歷經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多次變更,對服飾面料圖紋組織的規定提到過兩次,對唐官常服袍服的“文”做了全面規范。第一次在武德四年(621),其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已上,大科(細)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細)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雙,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參見劉煦,等.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5.
n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第十卷:唐朝下[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o服飾律令按照其規制模式可劃分為授權性律令與禁止性律令。授權性律令主要通過詔令形式規定人們在何種場合可以穿著怎樣的服飾,較常見的如帝王冕服制度、不同品階官員冠服搭配方式及后妃命婦服飾形制等。禁止性律令是指對服飾材質、色彩、尺寸及穿著場合等作出的禁限,亦可將其統稱為“服飾禁例”。
p“畫人物,須先考歷朝冠服、儀仗、器具、制度之不同,見書籍之后先。勿以不經見而裁之,未有者參之,若漢之故事,唐之陳設,不貽笑于有識耶?”參見范璣.過云廬畫論[M]//王伯敏,任道斌.畫學集成.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2.
q方薰.山靜居畫論[M].鄭拙廬,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r董逌.廣川畫跋[M]//于安瀾.畫品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s《舊唐書·輿服制》載:“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t《隋書·吐谷渾傳》:“其王公貴人多帶冪籬。”參見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舊唐書·輿服志》:“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冪籬。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參見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u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304.
v郭若虛.圖畫見聞志[M].鄧白,注.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6.
w《唐會要》載武德四年敕令稱:“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是也。自后紗帽漸廢,貴賤用之。故事,全復皂而向后幙發,俗謂之幞頭。周武建德中,裁為四腳。”參見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90.
x《夢溪筆談》卷一:“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腳。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腳。本朝幞頭有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腳貴賤通服之。”參見沈括.夢溪筆談[M].張富祥,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