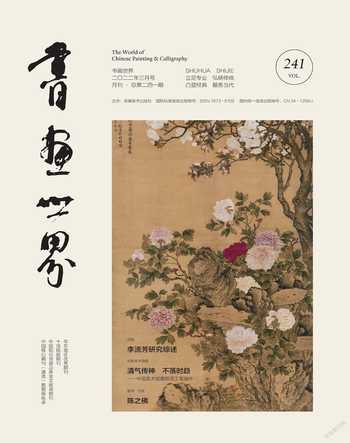何焯書學兩面觀的具體表現
曹凡


內容提要:清代校讎家、書法家何焯(1661—1722)傳世著作較多,其《義門題跋》《義門先生集》中均存有他對書法的見解與詮釋。何焯書學思想雖主要傾向于“書宗魏晉、崇古尚韻”,但隨著清初“碑學”的發展,其后期也出現了碑學傾向。本文試圖通過對何焯的書學論著進行梳理,探討其書法品評方面的言論,把握何焯的書法品評態度及其審美標準,從而對他書學思想兩面觀的具體表現有所了解。
關鍵詞:何焯;書學;兩面觀
在中國書法史長河中,涌現出眾多杰出的書法名家,他們博采眾長,積極從傳統中汲取營養,創作了許多流傳至今的經典作品,被后世學書者當作典范。他們在書法品評等理論方面,同樣為后世提供了諸多借鑒。但對同一書家及作品,因持評者立足點不同,往往會有不同的觀點。中國書法史上對清代校讎家、書法家何焯(1661—1722)的品評就是如此,帖學者評其尚晉之古韻,碑學者評其具“廉鍔風神”。
何焯,字潤千,早年因喪母而改字為屺瞻,晚號茶仙,別署無勇、義門、香案小史,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何焯生活軌跡大多遺留在康熙年間,是康熙年間有名氣的書家之一,與笪重光、姜宸英、汪士并稱“康熙四大家”。何焯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并入能品。
一、書宗魏晉、崇古尚韻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由于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偏好,朝野上下無不欽慕于王書。太宗即位后,獨尊羲之書法,確立王書大統地位,即“書宗魏晉”。這一思想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重要的影響,魏晉書法也因此而為后世所推崇。
何焯受到董氏復古書學思想與其師邱三近的影響,在書學上追求“晉韻”。在學書時,他喜臨晉唐法帖,對魏晉風度心生向往。其在作品《李白五言詩》中寫道:“自恨俗筆,無晉人韻。”此詩句體現出他在書法學習實踐中對魏晉書風的傾慕,且這一書學思想貫穿其一生。
何焯在《義門題跋》中對歷代書家的評騭,始終秉持書宗魏晉之思想。何焯跋《舊本顏魯公多寶塔碑》曰:“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神,便足以為二王繼。”[1]222何焯之所以于唐代眾多書家中推崇顏真卿,即是因為顏氏筆法合于右軍父子,實為對晉韻的追崇。
與何焯有相同觀點的書家不在少數,如黃庭堅在《山谷題跋》中稱:“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2]董其昌跋《爭坐位帖》:“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于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為宋一代書學淵源。”[3]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何焯《昆陵唐氏宋拓十三行跋》曰:
余竊謂晉、梁相去差近,《洛神》亦自有右軍所書,殆未可知。今所存《十三行》則姿態翩躚,興會豪舉,故與大王不類,未容便議褚、柳鑒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露無余,多帶顏法,遂開蘇、黃風氣。[1]224
可看出何焯對宋代書家的品評則頗具微詞,原因在于其認為宋人書“與大王不類”。
另《張旭肚痛帖跋》亦曰:
《肚痛帖》筆勢固豪頗,亦失之流宕,去晉人便自邈然,疑蘇才翁兄弟所為,未必真伯高也。然書學不到黃長睿,驟有異同,鮮不貽誚于蚍蜉撼大樹矣。姑獻疑焉,待明者決定可乎![1]224
觀張旭《肚痛帖》墨跡,何焯懷疑其為偽作,理由就是從用筆判斷,此帖與晉人相去甚遠。由此可看出,有無晉人筆意已成為何焯品評書家作品優劣的首要標準,何焯崇尚魏晉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何焯欲維護書法正統,是否取法古人、有無古韻也是其對書家作品評判的另一標準。何焯《漢夏承碑跋》曰:“觀其用筆淳古,使人追想東京文物之美,實與三代同風。”[1]218其向往漢隸之淳古,上溯至夏、商、周三代之變,乃其崇古風氣之另一端。
在何焯的早期品評中,常常以承有古韻、直追晉唐品評元明一些書家,跋《董思翁摹爭坐位帖》中曰:
思翁行押尤得力《爭坐位帖》,故用筆圓勁,視元人幾欲超乘而上。此跋其加意所書,精采溢發,直與魯公相質于千載之上,不惟來學可資為津逮也。[1]226
何焯贊譽董其昌用筆圓潤,遠超元人,直追魯公,高古可賞。再如何焯對祝允明的品評,同樣贊譽有加,《祝京兆書跋》曰:
自明初景泰間,書體皆沿元人遺風,而用筆乃勁拔,筋骨足備。成弘以后,推排吳興,稍欲上追魏晉六朝,自立一家之則,其筋骨則非前任比矣。然樸雅安重甚得古貌,如此數紙豈亦近時佻薄所能窺仰耶?[1]226
何焯認為祝允明沿襲元人風貌,用筆勁拔,筋骨足備,亦可追溯魏晉,又“樸雅安重甚得古貌”,所以非常推崇。《祝京兆書述跋》曰“用筆渾厚圓足,中廉鍔森然,非枝山先生絕無此書”,更是對祝允明用筆稱贊不絕。
除此之外,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一《鮮于伯機書杜詩》曰:“元人書,吳興、漁洋而外無可存者。”[4]其認為元人書,除趙孟與鮮于樞之外,再無他人。但何焯在校文中辯稱:“虞伯生(虞集)樸雅。袁清容(袁桷)學米,時近晉韻。張伯雨(張雨)出入李括州(李邕)、張從申間,古法甚高。揭曼碩(揭奚斯)草書亦近晉,小楷復工。非二公所能掩也。”[5]何焯認為,元代書家之中,虞集樸雅;袁桷學米,猶有晉韻;張雨學習李邕、張從申二家,而得古意;揭奚斯草書也有晉人風采。所以這些書家也是何焯所欣賞的,不能被趙孟、鮮于樞掩蓋。因此何焯對元明書家品評,不以時人所論而改轍,始終以是否繼學古人、有無“晉韻”為評判標準。
二、崇“北碑”之美
清初學者在治學上采取“博古通今”的務實之法。由于這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氛圍、訪碑熱潮大盛于“正經考史”的歷史環境中,何焯等在內的大批書家看到了明人所未見的碑版刻石。正是眼界的拓展、北朝碑刻影響,使得何焯的書學思想發生了一定轉變。
何焯晚年推崇北朝碑版書法,在他的《義門題跋》《義門先生集》中收錄了其不少題跋,其中涉及對書家、作品、碑版的品評,從中可以窺覷何焯“崇碑”書學思想之另一面。
《北魏營州刺史崔敬邕墓志跋》明顯反映出何焯對北碑的接納態度:
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開闊。唐人終莫能及,未可概以北體少之也。六朝長處,在落落自得,不為法度拘局。歐、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繩尺,而古韻微矣。宋人欲矯之,然所師承著皆不越唐,恣睢自便,亦豈復能近古乎?[1]219
他認識并肯定了北朝碑刻一些審美上的意味,雖看似“丑拙”但不為法度所困,落落自得,古韻足,具有“意象開闊”之美。
同時,何焯認為北朝書體具有“廉鍔風神”之美。“廉鍔”是他所提倡的北朝碑版書法的審美標準,所指為碑版拓片字跡清晰,筆力渾厚,且整練方折。他對書法的品評,也喜歡使用“廉鍔”一詞,《雜論》曰:
安溪先生視學時,保定王先家廢苑東,每夜發光,啟土數尺,即《武功寺田公德政碑》也。廉鍔豐神與宋本無異。先生即命植保府學。[1]246
何焯認為此《武功寺田公德政碑》拓本是宋拓珍品,并用“廉鍔豐神”贊譽之。反之,如果拓片字跡不清晰,筆畫不具備方折、利落的北朝古法,不能如董其昌所言“字畫如刀截”并體現“廉鍔”之美的,則以“風神”不足論之。跋《舊本圣教序》曰:
此碑未斷之本已不多得,特拓手非良工,且偶不得佳墨,遂稍減風神,不能如董宗伯所云“字畫如刀截”者爾。[1]220
除此之外,何焯在品評墨跡書法時,也運用此品評標準。其早年曾評祝允明曰:“京兆書血脈往往不貫,又故為奇詭,流宕無法,書之魔也。”[6]其認為祝允明筆畫氣息難以連貫,失筆散亂,缺乏法度。但其晚年受北朝碑刻的影響,隨即改變以往的觀點,極為肯定祝允明書法,但還是用“廉鍔”一詞作評:
用筆渾厚圓足,中廉鍔森然,非枝山先生決無此書,功腕力,惜所值紙澀而毫又弱,如策駑駘上峻坂,意所欲至,蹇蹶弗前,稍減色耳。[1]225
其認為祝枝山用筆“渾厚圓足”,稱贊其“廉鍔森然”,其書寫講求腕力,筆畫力足,即使紙張粗澀、筆毫軟弱,仍能見骨力,而這些正是源于其用筆之勁拔。
綜上所述,何焯于康熙時期,較早對北朝碑刻書法價值產生認同,且認識到了“北碑”之美,于“北碑”之中發現了不同于傳統帖學的審美特征,而這些審美特征正是當時董氏書風下所不具備的,開清代“北碑”審美新風尚,表現出其書學思想中的碑學傾向。
三、小結
筆者所論述的何焯關于評論書法的一些觀點,只是何焯書學理論中諸多觀點的一小部分。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金石碑刻的大量出土,金石學興起,眾多的書家、學者將目光轉向碑刻書法的研究上,不再局限于傳統帖學。何焯被尊為康熙“帖學四家”之一,有著“書宗魏晉、崇古尚韻”的書學思想。他在《義門先生集》中提出的有關書學、碑學思想的觀點,既反映出他書學上對“尚古”傳統審美的執守,也反映出他書學思想的開放性和進步性。這對于清代碑學發展和書法審美的多元化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何焯.義門先生集[G]//《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2.
[2]王中焰.黃庭堅書論[M].杜玉印,注評.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167.
[3]董其昌.畫禪室隨筆[M].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62-63.
[4]孫承澤.庚子銷夏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3.
[5]孫承澤.庚子銷夏記[M].白云波,古玉清,點校.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226.
[6]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M].王彬,嚴英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141.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