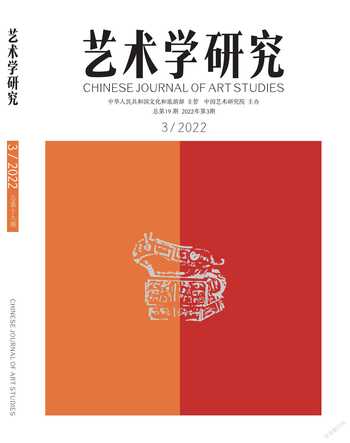《十月》的誕生與藝術批評的理論蛻變
受訪人:羅莎琳·E.克勞斯(Rosalind E. Krauss)
訪談人:魯明軍?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2018年3至9月,在美國亞洲文化協會(ACC)的資助下,魯明軍前往紐約,圍繞美國著名當代藝術評論雜志《十月》(OCTOBER)進行了一系列訪談,從一個側面考察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藝術批評與理論的歷史進程,借以反思當代藝術批評、理論以及藝術媒體生態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其間,先后采訪了羅莎琳·E.克勞斯、本杰明·H.D.布赫洛(Benjamin H.D. Buchloh)、伊夫—阿蘭·博瓦(Yve-Alain Bois)、大衛·喬斯利特(David Joselit)、萊耶·迪克曼(Leah Dickerman)等13位雜志編委成員和作者。本文是對羅莎琳·E.克勞斯的采訪,時間在2018年8月29日。
羅莎琳·E.克勞斯(1941—)是美國著名藝術理論家、批評家,《十月》雜志的創刊人之一,被譽為“繼格林伯格之后對美國藝術批評界影響最大的人物”。她畢業于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先后任教于衛斯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亨特學院,現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作有《現代雕塑的變遷》《前衛的原創性及其他現代主義的神話》《視覺無意識》等。
魯明軍(以下簡稱“魯”):您好!克勞斯教授,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我的采訪。首先,我很好奇,半個多世紀以來,您一直筆耕不輟,您還記得這么多年為多少個藝術家寫過評論?
羅莎琳 · E.克勞斯(以下簡稱“克勞斯”):這個我無法回答你,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些我寫過的藝術家。我最初在《藝術論壇》(Artforum)擔任評論員,他們每個月都會給我分配任務,每期都有五六個展覽,我必須要寫。我記得最早的一個是唐納德 · 賈德(Donald Judd),后來寫過索爾 · 勒維特(Sol Lewitt)、理查德 · 塞拉(Richard Serra)、梅爾 · 波赫納(Mel Bochner)、多蘿西婭 · 洛克伯尼(Dorothea Rockburne)等,我還認識了羅伯特 · 史密森(Robert Smithson),他是如此地令人激動。
魯:這次訪談的主題是《十月》。想必您不止一次回答過這個問題,但我還是想問,40多年前,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和安妮特·邁克爾森(Annette Michelson)創辦了這份偉大的刊物?特別是這個名字,它是指俄國的“十月革命”嗎?
克勞斯:創辦《十月》的關鍵是《藝術論壇》。1962年,《藝術論壇》創刊于舊金山,后來雜志社搬到洛杉磯。1967年,在克萊門特 · 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建議下搬到紐約。這期間,主編一直是菲利普 · 萊德(Philip Leider)。菲利普是個天才,很聰明,也非常友好,所以身邊匯聚了一批有才華的作者和藝術家,直到1971年他離開紐約。接替他的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約翰 · 科普蘭斯(John Coplans),自1972年起擔任主編。他的性格和萊德相反,脾氣暴躁,動輒發火,令很多作者不適,我們也不喜歡他。
20世紀70年代初,編輯部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藝術論壇》改版了,它變得更“厚重”了。因為發行很快,廣告的版面不斷增加,這意味著編輯內容的空間,也就是寫作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導致我們不能寫任何稍長一點的文章,長篇理論或任何類型的精神分析文本都被拒絕。對此,我開始感到不快。二是科普蘭斯沉迷于如何將雜志的空間推銷給畫廊,他不希望發表太多非畫廊展覽和作品的文章,比如關于錄像藝術、電影或表演的文章都沒有發表的空間,因為它們不屬于商業畫廊和藝術界的交易對象。對這些材料感興趣的人除了我還有邁克爾森,于是我倆自然地被編輯部疏遠了,內心也感到與《藝術論壇》越來越遠。在這個過程中,科普蘭斯任命馬克斯 · 科茲洛夫(Max Kozloff)為執行編輯。他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敵視,認為這是一種形式主義。所以在某個時刻,我們決定離開,創造自己的雜志。我還記得有一次,《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發表了一篇科普蘭斯的采訪,在被問到我們為什么離開《藝術論壇》時,他說:“好吧,我們清除了形式主義者。”
《十月》這個刊名來自蘇聯導演謝爾蓋 · M.愛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為紀念“十月革命”10周年拍攝的一部電影,電影的名字叫《十月》(OCTOBER 1917,1928)。受當時蘇聯政治形勢所迫,在這部電影中,愛森斯坦不得不清洗了托洛茨基。同樣,對我們而言,《十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如此,它是對形式主義的一次清洗,并將此作為雜志的一個標志。所以我們決心在所有這些禁忌的主題下展開工作,比如雜志大量刊發有關電影、表演和錄像藝術的討論文章。另外還需一提的是,科普蘭斯一直對法國理論有點過敏。而我此前一直想在《藝術論壇》發表福柯著名的文章《這不是一只煙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但科普蘭斯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受此刺激,《十月》的第1期(創刊號)不僅刊發了我關于錄像藝術的文章《錄像:自戀癥美學》(Vedio: The Aesthetic of Narcissim),還刊發了理查德 · 霍華德(Richard Howard)翻譯的《這不是一只煙斗》—理查德是一位優秀的譯者。因此可以說,我們的創刊號就是一部宣言,它所刊發的多是曾被《藝術論壇》拒絕和退稿的文章。那時的我們都非常反感《藝術論壇》,所以決定在發刊詞中直接提出,我們將沒有廣告,沒有顏色,所有那些看上去已經“變態”的《藝術論壇》的風格,比如全彩印刷、對廣告的需求以及對編輯空間的限制等,在這里都是我們所反對和抵制的。
一開始,我們還能夠保證雜志的運營資金。有這么幾個途徑,一種是我們在蘇荷(SoHo)有一個叫春街書店(Spring Street Books)的藝術書店,是一個非常好的書店,當時由賈普 · 萊特曼(Jaap Rietman)經營。萊特曼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方韋滕伯恩公司(Wittenborn & Co.)—一家位于麥迪遜大道上的圖書出版公司,創始人喬治 · 韋滕伯恩(George Wittenborn)是一位資深的出版商,出版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藝術書籍。正好萊特曼也對韋滕伯恩的理念和傳統感興趣,所以,當我們說起我們的計劃和想法,問萊特曼是否愿意購買我們的雜志時,他很爽快地答應了。第一版印了25本,結果他以每本100美元的價格全部購買了,我們得到2500美元的售書款,然后把這筆錢支付給印刷商,償還了第一筆欠款。除此以外,當時還有一個叫國家藝術基金會的政府項目,每年資助我們25000美元,連續資助了好幾年,到里根時代就被終止了。當時,我們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壓力,可又沒有任何辦法和途徑。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同事,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彼得 · 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是一位建筑師,有一個非營利機構,他稱其為“建筑與城市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1]。他有一個小辦公室,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組成了一個前衛建筑師的群體。不過,他之所以經營這個機構是因為他結識了很多非常富有的人,后者為機構的運營提供了資金保障。他把我們介紹給那些富人中的一個,資助了我們兩年后,也終止了。我記得有一次和好朋友謝里 · 萊文(Sherrie Levine)喝咖啡,我說:“萊文,《十月》已經結束了,我們沒有錢了。”她說:“別傻了!我們會給你照片,你出版一個作品集,把它們賣掉,錢不就來了嗎?”這是個很好的想法,于是我們很快聯系藝術家,編輯了第1輯,第1輯有辛迪 · 舍曼(Cindy Sherman)、謝里 · 萊文等人的作品。我們緊接著推出了第2輯,里面有格哈德 · 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羅伯特 · 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等人的作品。0A5DE064-43AD-4004-A96C-021377C542E1
這就是我們“自我造血”的方式。與此同時,我們還做了一個決定,計劃出版一系列藝術家小書,就是“《十月》檔案”(“OCTOBER Files”),內容是收集、編輯所有關于特定藝術家的最佳寫作。我們做的第一本是關于理查德 · 塞拉的,后來做了安迪 · 沃霍爾(Andy Warhol)的,還有羅伊 · 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伊娃 · 黑塞(Eva Hesse)等藝術家的。這些小書其實非常有價值,也很重要。令我非常沮喪的是,沃霍爾的那本已經絕版。其實最初,這些都是為了賣給學生,所以它們都是小書,定價也偏低。和《十月》一樣,它們同樣沒有任何顏色,開本很小,也不厚。但這些小書貢獻很大,一直支持我們將《十月》繼續辦下去。我與出版商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達成了一項協議,相當于做了一個交易,一本書一美元,就是說他們賣一本書,我們得一美元。因為我已經習慣和出版商的會計打交道,他們有無盡的理由不想付給你版稅,但在這件事上,我告訴他們沒有商量的余地。沒想到,我們從這一系列小書上獲得了不小的利潤。
魯:您如何看《十月》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左翼運動的關系?是否可以說,《十月》本身就是一本左翼刊物?過去40年來,它主要的貢獻是什么?其間又經歷了哪些變化?
克勞斯:嗯,從一開始,在創刊號發表福柯的《這不是一只煙斗》的時候,我們就決心做一本在分析方法上更加豐富、更加多樣的新刊物,并決心要繼續翻譯、刊發和出版像結構主義這樣的法國理論,如克洛德 · 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神話學”作為理論依據或分析工具,那個時候就已經出現在《十月》上。說到這里,我想起過去因為報道佩斯畫廊(Pace Gallery)的展覽,認識了畫廊老板阿諾德 · 格萊姆徹(Arnold Glimcher)—他們在波士頓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有一次他來找我,說他要在畫廊舉辦一個大型的網格繪畫(Grid Painting)展覽,問我是否有興趣撰寫展覽圖錄的文章。因為熟悉,我就答應了,但當時覺得似乎沒有什么比寫一篇關于網格繪畫的文章更無聊了,它有什么可說的呢?!
但后來我想起了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學著作,他在里面談到了網格,給了我很多啟發。他說神話學家一直在從神話中尋找網格,但從未找到它,也不可能找到。因為神話只關乎重復,一遍又一遍,沒有一個神話不是重復的。以俄狄浦斯神話為例,俄狄浦斯的神話有一百萬個版本,包括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也是。而我們要問的是,該如何識別這些版本是否屬于同一個神話?如何才能認識到弗洛伊德版本的戀母情結與原始的俄狄浦斯神話是一樣的?它們是一樣的嗎?列維—斯特勞斯說我們要做的必須是為了創造,但不必創造一個神話的結構,以免你再次看到它時,難以辨識它是否由相同的結構所組成。他說的神話的這種重復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即它們其實是由兩個無法調和的元素組成的。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它們往往是相互對立的,而它們能夠被調和的唯一方式是通過神話的敘事。但他接著又說,敘事并沒有使其得到真正調和,只是暫停了它們,或使其處于暫停的狀態。這就是一個社會能夠容忍這種理論上的撕裂和對立的原因。比如關于俄狄浦斯,他解釋說,他要做的是為了理解神話的結構,因此必須把神話的敘事分成這些片段。而那些不斷重復的片段,其實就是神話的主題。
我們都知道俄狄浦斯的神話,他謀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然后又遇上可怕的瘟疫。所以列維—斯特勞斯說,這些是神話的神話,對于宗教團體來說,它們代表了某種宗教信仰,而這些都是可怕的沖突。因此在這里,神話作為一種方式并不是為了調和這種沖突,而是將其暫停。他說,連俄狄浦斯的名字都與兩個對立的宗教信仰有關。其中一件事與俄狄浦斯的典故有關,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腫脹的腳,所以它關乎地面。列維—斯特勞斯認為,這個神話的結構其實反對兩種關于生育的信仰,即關于人類物種的繁殖。一種是關于兩個人在一起生育的信仰,另一種是他所說的無性生殖的信仰,比如,就像鵝卵石從一塊石頭上脫落一樣,意思是說孩子不是兩個人、而是一個人生出來的。這對你來說有意義嗎?列維—斯特勞斯解釋了二者是如何進行、如何運作的,一旦你得知這是一場戰爭,一場關于兩個人生殖的信仰和關于一個人生殖的信仰之間的戰爭,就會理解在弗洛伊德“戀母情結”理論內部,是孩子不相信他的母親和父親生了他,所以當他相信他只來自他的母親時,就會與父親戰斗。這就是列維—斯特勞斯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而弗洛伊德的“戀母情結”理論實際上是這種原始斗爭的再現。列維—斯特勞斯提示我們,這種重復是有點神經質的,就是說,既然對立不能被解決,那就只能被重復。
由此我想到的是,一旦藝術家開始用網格工作,他們能做的就是重復,他們永遠無法擺脫它。如蒙德里安,他畫了40年的網格。還有像阿格尼絲 · 馬丁(Agnes Martin),用那些六英尺(約1.83米)見方的網格,一遍又一遍,畫了很多年。另外,像賈斯帕 · 約翰斯(Jasper Johns)的繪畫,也與網格有關,他的繪畫是神經質般的網格結構。所以,我不得不嘗試找到它的對立面,就像戀母情結的對立面一樣,解釋為什么他會有這種神經質的、對復制或重復的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十月》不僅推動了法國理論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流通,而且還直接參與了結構主義這一知識的變革,將它帶到了關于當代藝術的討論中。在我看來,這是《十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另外,我認為這對學生也非常重要。如果他們對某個藝術家感興趣,它可以啟發他們四處尋找與之發展相關的類似物,而不再遵循傳統藝術史的那種方式,即考察藝術家是如何與他們的先輩發生關聯的。在我看來,那種大師風格的儀式化傳遞,也就是那種代際分析是非常病態的。對學生來說,四處尋找其他模式,促使其得到解放,則更為重要。
魯:這的確是《十月》對藝術批評寫作的巨大貢獻,在當時也是全新的東西。但事實上,從這些年雜志關心的問題和刊發的文章看,似乎更側重藝術史的深度研究,很少涉及或直接報道、評論當下的藝術現場。您認為這樣一個藝術刊物是如何界定與當下現場的關系的?作為當代藝術的一個純學術媒體,對于整個當代藝術生態,它的意義在哪里?0A5DE064-43AD-4004-A96C-021377C542E1
克勞斯:嗯,我想不出具體的例子,太多了……其實,我們一直在努力刊發一些我們認為對當代藝術家比較重要的文章。我記得20世紀90年代,我們圍繞“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做過一次問卷調查,邀請學者、藝術家思考這個問題并填寫問卷,然后反饋給我們,我們整理討論后發表在《十月》(第77期,1996)上。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處理當代藝術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幾年前,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曾舉辦了一個大型的攝影展,其間他們組織了一個小型會議,有一位發言人談到了數字攝影的作用,認為這在攝影史上是一個創舉。我當時覺得這個題為《從“追蹤—圖像”到“虛構—圖像”:80年代至今攝影理論的展開》(Trace-Image to Fiction-Image: The unfolding of Theories of Photography from the 80s to the Present)的演講十分新穎,也很聰明,后來我聯系他并翻譯了這篇文章,發表在《十月》(第158期,2016)上。我記得他在發言中舉了一個阿特拉斯小組(Atlas Group)的例子。你知道,數字攝影導致了某種檔案工作,而阿特拉斯小組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一直不知道阿特拉斯小組,還是在一個研討會上,聽我的一個學生介紹了它的情況,這才了解。所以,聽到發言人提到阿特拉斯小組,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這是什么。
魯:您還記得這篇文章的作者嗎?
克勞斯:菲利普? · 杜布瓦(Philippe Dubois),是新索邦大學巴黎第三分校電影和視聽系教授。盡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說,就當代藝術而言,我還是不太了解。幾年前我突然中風了,導致我無法頻繁走動,所以沒辦法經常去畫廊看展覽。對此,我也感到非常內疚。
魯:在這種情況下,您覺得網絡會是一種有效的替代方式嗎?
克勞斯:我不認為在網上能真正了解藝術,這似乎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因為你沒有在場感,就沒有辦法對作品作出真實的判斷。我現在雖然很少到現場看展覽,但我們編委會有。《十月》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編委會,比如編委會的成員之一大衛 · 喬斯利特(David Joselit)就非常活躍,對當代藝術現場非常了解,所以這是個很大的幫助。除了他,編委會還有萊耶 · 迪克曼(Leah Dickerman),她是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一個策展人。其實也不止他們兩位,還有個別編委會成員也非常關注當代藝術。
魯: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與格林伯格及其他評論家的交往?
克勞斯:當時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邁克爾 · 弗雷德(Michael Fried)是我的同學,是他把我介紹給了格林伯格。那時我還住在波士頓,當我每次為《藝術論壇》寫評論而到紐約看展覽時,都會去拜訪他。我會去他的公寓看他,通常都會聊上半小時或45分鐘,所以對他比較了解。實際上,正是因為他,我才能夠做關于大衛 · 史密斯(David Smith)作品的博士畢業論文,因為他是史密斯遺產的執行人。但后來,在某一點上我開始變得不喜歡他,我發現他很專制,就像他的批評觀點,大多都非常狹隘。實際上,他在表達這些觀點的時候非常教條,沒有任何空間可以與他產生分歧,可以批評他。還有一件事,有人告訴我,我不相信—但我想應該是真的,就是格林伯格一直在接受藝術經銷商和畫廊的資助,所以他不遺余力地宣傳后者代理或合作的藝術家,把這些藝術家置于他認為的前衛位置上。當我得知這一點的時候,我很失望,因為我一直以為他是絕對獨立的。
除了格林伯格外,我在紐約還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列奧 · 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我曾經每年都會與他共進兩次晚餐。列奧是個嗜煙如命者,除了特殊情況,他從不去餐館,因為在餐館無法吸煙。我和他一起吃飯的時候,他會點中國菜或印度菜,但我不喜歡吃。我們也會玩拼字游戲,他是一個拼字游戲的狂熱者,所以我總是輸。但我真的很喜歡列奧,我從他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關于藝術評論,關于如何與藝術家交往,他曾經說:“如果你在賽馬上下注,就不要和馬說話。”他這是提醒我,批評家不應該與藝術家過多交談,因為他相信,如果作品是好的,它自己就會說話。藝術是連貫的,我們能夠理解作品,不需要去問藝術家本人。
魯: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前衛的原創性及其他現代主義的神話》(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the Other Modernist Myths,1985)一書是對格林伯格的回應嗎?
克勞斯:我當時是被邀請參加一個關于前衛藝術的會議。當然,那個時候沒有人可以在談論前衛藝術時繞過格林伯格。但是在我討論關于神話和神話的重復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思考先鋒派了。先鋒派都有點自豪地認為自己來自“無”,認為自己跳出了所有歷史背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比如未來主義談論的新,就是夜里的車要翻了就推倒它(源自尼采所言“車要翻了就推倒它”—訪談者注),然后翁貝托 · 波丘尼(Umberto Boccion)從他所說的轉彎處或溝渠中升起,進入新的未來主義領域,意思是說,每一個先鋒派都要拋棄他的過去,重新塑造自己。而在我看來,這其實與神話結構有關。在某種程度上,從過去跳出來,落在新的地方,這些藝術家基本上已經確定了他們認為的新的東西,然后在重復中發展自己。這就是我認為的前衛藝術的神話。我舉的一個例子是羅丹和他反復鑄造作品的方式(參見本人《現代雕塑的變遷》第一章“敘事性時間:《地獄之門》的課題”),它就是再現,重復再現是這種神話的核心思想。所以我想說的是,前衛的原創性其實與神話的想法有關。
魯:您怎么看蒂埃里·德·迪夫(Thierry de Duve)在《字里行間的格林伯格:兼與格林伯格的辯論》(Clement Greenberg Between the Lines: Including a Debate with Clement Greenberg,2010)一書中對格林伯格的修正?以及邁克爾·弗雷德在《藝術與物性》(Art and Objecthood)一文中對格林伯格的辯護?0A5DE064-43AD-4004-A96C-021377C542E1
克勞斯:格林伯格對于邁克爾 · 弗雷德來說是一個圣人。在我看來,邁克爾所相信的一切都來自格林伯格的歷史觀,比如事情的必然性及其年表、先鋒藝術的必然發展等。邁克爾無法想象在沒有格林伯格理論結構的情況下如何思考藝術。蒂埃里 · 德 · 迪夫的圣人不是格林伯格,而是馬歇爾 · 杜尚(Marcel Duchamp)。他反復思考的是格林伯格否定杜尚之現代主義歷史的方式。對蒂埃里來說,這不可能是真的。因此,他想重塑一部現代主義的歷史,這里面杜尚就是祖先,是開端。我認為蒂埃里的工作是開創性的,非常好。
其實,在這之前我還翻譯了蒂埃里的一本書。他在《十月》先后發表了三篇文章,都是我翻譯的。后來我把這三篇文章匯集成一本書,叫《馬克思血汗工廠里的縫合:博伊斯、沃霍爾、克萊茵、杜尚》(Sewn in the Sweatshops of Marx: Beuys, Warhol, Klein, Duchamp,2012),交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幾乎同時,我寫了一本關于德 · 庫寧的書《永不停歇的德 · 庫寧:尋找那個女人》(Willem de Kooning Nonstop: Cherchez la femme,2015),一開始寄給了一直跟我合作的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該出版社出版了幾乎我所有的著作,但出版社編輯回復說他們對關于德 · 庫寧的書不感興趣。我有點沮喪,不知道該怎么辦,于是想到了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因為此前他們出版了我翻譯的蒂埃里的書,我試著把關于德 · 庫寧的書稿也寄給了他們,沒想到他們同意出版這本書,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安慰。
魯:據我所知,1987、1997年《十月》曾編過兩本合集,可以說是對兩個10年的總結,不同時期,涉及不同的話題,包括“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體制批判”(Critique of Institutions)、“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修辭學”(Rhetoric)、“身體”(The Body)和“藝術/藝術史”(Art /Art History)、“后殖民話語”(Postcolonial Discourse)、“身體政治/精神分析”(Body Politics / Psychoanalysis)、“景觀/體制批判”(Spectacle / Institutional Critique)。這些話語、論題與當代藝術現場是一種什么關系?是相互緊貼,還是有一定距離?
克勞斯:我舉個例子吧。比如米格翁 · 尼克森(Mignon Nixon),精神分析對她的寫作思維至關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還是取決于她的研究對象,并不是理論先行這么簡單。她在路易斯 · 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身上花了很多時間,下了很大功夫,所以還是取決于主題,取決于作者要研究的藝術家,在這個基礎上,再考慮依賴哪種理論框架。
談到這個,我想起去年《十月》決定使用我們自己的理論技能,寫一些反特朗普的小品文。我們發表的那篇是哈爾 · 福斯特寫的《皮埃爾 · 特朗普》(Père Trump,第159期,2017)。福斯特在文中提到,這其實跟弗洛伊德講的“原始的父親”(The primal father)這個故事有關。在《圖騰與禁忌》(Totem & Taboo,1913)中,弗洛伊德從達爾文的“原始部落”—一個由全能的父權者統治的偉大的兄弟團體—中推導出這個人物。這個可怕的“父親”享受著部落中所有的女性(這是女性在這個古怪的故事中唯一的角色),并把兄弟們排除在性之外,以至于他們起來殺死了這個暴君。然而這一行為使他們陷入了深深的內疚之中,因此他們再次將死去的“父親”提升為神,或者至少是一個圖騰,圍繞這個圖騰建立了禁忌(最重要的是禁止謀殺和亂倫的禁忌)。對弗洛伊德來說,由此社會就開始了。哈爾用這句話來描述忠貞,就是特朗普追隨者的那種卑微的忠貞。我也寫了一篇不太討喜的文章,所以到現在都沒有發表,題目叫《愛我的發件人》(Love me Sender)。它基本上是一篇關于特朗普的推文,我認為它可以被解釋為弗洛伊德的反移情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關于病人和病人之間的愛,是病人和治療師之間的移情。但是治療師對病人有一種反情欲的反應。弗洛伊德在“多拉”案例的研究中寫了很多這方面的內容。他給威廉 · 弗利斯(Wilhelm Fliess)寫信,與很多人通信,那時他正在寫作《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一書,他感到缺少一種藥物。而這實際上是他描述自己對“朵拉”的一種反移情的方式。所以,這便是為什么說《愛我的發件人》是關于特朗普的推文的原因,但編委會不喜歡它,所以沒有發表。
魯:您的寫作和藝術史研究方法的轉向有交叉嗎?比如新藝術史的轉向,比如視覺文化的興起,其中包括T. J.克拉克(T. J. Clark)、斯維特拉娜·阿爾珀斯(Svetlana Alpers)、于貝爾·達米施(Hubert Damisch)、路易斯·馬林(Louis Marin)的研究,等等,您會關注他們的研究嗎?
克勞斯:我關于德 · 庫寧的那本書就是受T. J.克拉克的啟發寫的,它是圍繞德 · 庫寧的一張畫《在哈瓦那的郊區》(Suburb in Havana,1958)展開的,那幅畫很精彩。我非常敬佩克拉克,我認為《瞥見死神:藝術寫作的一次試驗》(The Sight of Death:An Experiment in Art Writing,2008)是他最好的書之一,我記得他在書中針對普桑的一幅畫持續數日地觀察,做非常詳細的分析和記錄,里面有很多關于黑暗的描述。我也非常喜歡斯維特拉娜 · 阿爾珀斯的作品,但并不像和克拉克那樣我能感覺到和她有什么聯系。達米施對我非常重要,不幸的是他去世了。他的研究是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這不僅啟發了我對結構主義的興趣,也幫助我理解結構主義。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非常了解他的。你還問到了誰?0A5DE064-43AD-4004-A96C-021377C542E1
魯:路易斯·馬林?
克勞斯:哦,我是路易斯 · 馬林作品的崇拜者。正好最近我正在讀路易斯 · 馬林的一篇關于羅蘭 · 巴特的文章,它涉及巴特的一本書《羅蘭 · 巴特自述》(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2010),很有意思。他發現巴特在關于自己的那本書里,是把自己作為一個角色來創作的,他既把自己當作對象,也當作自己。這就是馬林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他很敏銳。
另一個我非常感興趣的藝術史家是邁克爾 · 巴克桑德爾(Michael Baxandall),特別是他那本《15世紀意大利的繪畫與經驗》(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1972)。在這本書里,他攻擊了學界關于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習見。一直以來,我們通常都認為文藝復興繪畫的主體是古典人文主義者,即那些繼承希臘羅馬傳統、受過古典訓練并具有人文主體意識的群體,但巴克桑德爾透過大量的文獻發現,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主體不是古典人文主義者,而是商人(merchant)和紳士(gentleman)。這主要體現在“贊助人”這一維系藝術創作的社會慣例和習俗上,它包含了商業、宗教以及知覺。作為“雇主”(client),贊助人在整個過程中起著支配性的作用。巴克桑德爾發現這里的商人有一種“桶式凝視”(barrel-gazing)和“體積計量”(gauging,即運用幾何學和圓周率來測算桶的體積)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一個商人如果要賣給某個客戶一堆釘子,通常這些材料都會被裝在一個桶里,這樣的話,商人就必須對里面的釘子進行排序和估量,即時計算出桶里有多少釘子,以便給出一個價格。由此,他說這些能以非常復雜和非常迅速的方式進行思考的商人就是“看桶的人”。巴克桑德爾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將此引申到關于文藝復興繪畫的討論中。
通常,文藝復興繪畫中多邊形的體積遵循的還是透視法。但當你看到保羅 · 烏切洛(Paolo Uccello)的作品時,你會禁不住去想一個藝術家是如何制作出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精致的幾何物體的。按照巴克桑德爾的說法,烏切洛的這種復雜形體的塑造方式正源自與透視概念絕對相反的“桶式凝視”。它與透視無關,而與這些復雜的體積有關,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這是文藝復興時期所有人的特征。他是一個教堂的信徒,他知道如何閱讀彩色玻璃窗上講述的非常復雜的故事。他是個舞者,他知道如何通過舞蹈與其他人建立某種聯系—巴克桑德爾在書中專門探討了文藝復興時期舞蹈對繪畫的影響……因此,你可以說巴克桑德爾是發明了能夠理解文藝復興繪畫的方法的人。這很奇妙,且絕對精彩!
魯:非常受啟發!下面這個問題是關于編輯部內部運作的。我們知道《十月》網羅了一批優秀的藝術史學者和批評家,可以談談他們嗎?比如安妮特·邁克爾森、哈爾·福斯特、伊夫—阿蘭·博瓦(Yve-Alain Bois)、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帕梅拉·M.李(Pamela M. Lee)等,他們有的是您的合作伙伴,有的是您的學生,每個人都不一樣,彼此之間會有分歧嗎?比如您和邁克爾森之間。作為編輯,在關于一篇論文是否刊用的問題上,編委之間會有爭論嗎?
克勞斯:我們的意見通常都很一致。當作者給我們投來文章時,就會被分配到相關研究領域的幾位編委手中,請他們同時審核,然后進行編輯、評議和決定,最后會對錄用的文章提出建議,然后再將其寄回給作者進行修改。《十月》遵循的是一種集體編輯的過程,編委成員彼此之間沒有分歧。和很多刊物編委會不同的是,我們更像是一個思考項目的小組,所以我們的編輯也不像很多學術刊物那么教條和死板,就像本杰明 · 布赫洛針對特朗普的現象,提出作為一個藝術刊物,希望做點什么來回應這個可怕的現象,于是就有了哈爾 · 福斯特的《皮埃爾 · 特朗普》,還有我的《愛我的發件人》。這種臨時的舉措和行動與一般的學術刊物還是很不一樣的。
魯:說到這里,我想起之前和伊夫—阿蘭聊天的時候,他提及他創辦的雜志《光斑》(Macula),我想知道《光斑》和《十月》之間有什么關系嗎?
克勞斯:嗯,《光斑》當時對格林伯格非常感興趣,他們翻譯發表了格林伯格幾篇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書籍。當然,這個跟在法國的幾位對格林伯格感興趣的批評家有關。所以,當我遇到伊夫—阿蘭和他的助手讓 · 克萊爾(Jean Clair)時,他們和我談了很多關于格林伯格的問題,因為我是他們遇到的真正認識格林伯格的人。后來,我為他們寫了一些東西,關系也變得密切起來,“光斑”(這里指出版社)還出版了我許多著作的法語版。這中間,伊夫—阿蘭來到紐約,加入了《十月》的團隊。
魯:“《十月》叢書”(OCTOBER Books)在整個《十月》的編輯、出版和運營框架中,是什么角色?
克勞斯:“《十月》叢書”基本上都是學位論文。對此,我其實并不贊成,那些書稿大多是通過我們的學生寄給我們的,主要是學生的學位論文。我認為出版學位論文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所以每次我都投反對票,但我總是被投票淘汰了。
不過有一篇我很喜歡,是研究意大利貧窮藝術的,作者是賈列赫 · 曼蘇爾(Jaleh Mansoor),是我的研究生,論文題目叫《馬歇爾計劃現代主義:意大利戰后抽象藝術和自治的開端》(Marshall Plan Modernism: Italian Postwar Abstract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Autonomia,2016)。我一直對論文的標題過敏,按常規這樣的論文可能叫某個時期的某某某,或者別的,就是那種非常學術的標題。但我對她說:“你必須要想一個賣座的標題,以便于申請獎學金之類的,不能只是說‘上世紀60年代末的意大利繪畫。”后來,我們想到了馬歇爾計劃的現代主義,因為意大利貧窮藝術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歇爾計劃”的影響。你知道“馬歇爾計劃”嗎?
魯:我知道“馬歇爾計劃”,是二戰結束后,美國對西歐各國予以經濟援助和協助重建的一個計劃,對歐洲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切入關于意大利貧窮藝術的研究,的確是一個獨特的視角,回頭我找來一定認真拜讀。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中國的。您之前去過中國嗎?對中國的當代藝術家有了解嗎?
克勞斯:這是個尷尬的問題。我不認識任何中國藝術家。我曾經在馬薩諸塞州的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上學,有一段時間在衛斯理學院大衛斯博物館(Davis Museum,Wellesley College)任職。如果要說跟中國藝術有關,我想起有一個衛斯理學院的中國校友,一個叫宋美齡的女人,她是我關于中國藝術唯一的經驗。幾年前,大衛斯博物館想做一個她的畫展,找到我,但我對中國和中國藝術完全不了解,于是我去求教哈佛大學的一個中國教授,在他的幫助下,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展覽。她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但即便如此,我對她的了解依舊很有限。她是蔣介石的女兒嗎?
魯:不是女兒,是蔣介石的夫人。我的問題問完了。耽誤您這么久,非常抱歉!再次感謝您!
克勞斯:哦,那我搞錯了。不客氣,很高興和你聊這些事情。這是我第一次接受中國學者的訪談,這讓我倍感意外。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一般項目“美國《十月》雜志的藝術理論范式與文化政治實踐研究(1976—2008)”(項目批準號:2020BWY025)階段性成果。
[1] 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建筑工作室和智囊團,位于美國紐約曼哈頓,成立于1967年,1984年關閉。
責任編輯:崔金麗0A5DE064-43AD-4004-A96C-021377C542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