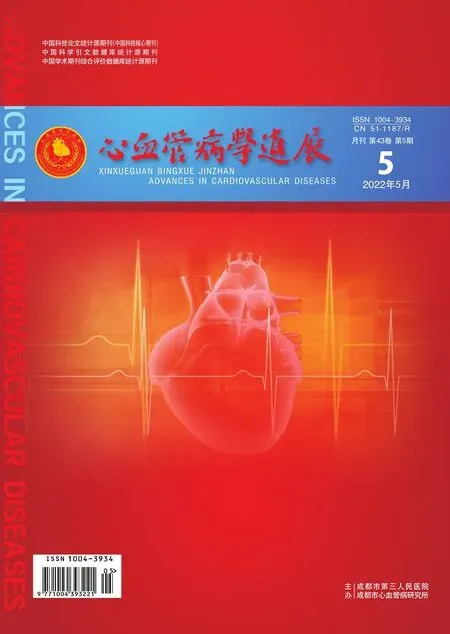左心耳封堵術后裝置相關血栓
柏懿璇 崔凱軍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內科,四川 成都 610041)
心房顫動(房顫)為最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中國年齡≥45歲的居民房顫患病率約為2%。且房顫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在75歲以上人群中,患病率為5%[1],隨著社會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房顫的患病率將進一步升高。缺血性腦卒中是房顫最嚴重的并發癥之一,積極預防腦卒中成為了房顫患者重要的治療目標。臨床多以口服抗凝藥物(oral anticoagulation,OAC)用于房顫相關腦卒中的預防,但由于相關的高出血風險,抗凝藥物的臨床應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左心耳封堵術經過近20年的發展,已成為預防房顫相關腦卒中的一種重要治療方式。5年長期隨訪研究[2]證實了左心耳封堵術預防腦卒中的療效不劣于OAC,且大出血的發生率更低。隨著術者經驗的增加和技術的改進,左心耳封堵術得到持續發展。然而,左心耳封堵術仍面臨諸多挑戰,其中,裝置相關血栓(device-related thrombus,DRT)作為術后隨訪觀察的重要內容,已成為術者和患者所擔憂的并發癥之一。現就現有文獻分析討論左心耳封堵術DRT的發生率、發生時間、預后、危險因素和治療,并做出總結展望。
1 DRT的發生率
左心耳封堵器作為一種異物植入體內,會存在血栓形成的固有風險。據此,該領域的兩項隨機對照試驗PROTECT-AF[3]和PREVAIL[4]均采用術后45 d口服華法林,隨后6個月氯吡格雷與阿司匹林雙聯抗血小板的治療方案,但Dukkipati等[5]通過薈萃分析發現此方案下DRT發生率為3.74%。而在ASAP研究[6]中,由于具有華法林禁忌而在術后僅采用抗血小板治療(antiplatelet therapy,APT)的150例患者中,有6例(4.00%)發生DRT。在真實世界EWOLUTION研究[7]中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卒中和出血風險,隨訪1年發現DRT發生率為3.70%,2年發生率為4.10%[8]。然而Fauchier等[9]在一項法國8個中心回顧性研究中,報道DRT的發生率為7.20%。PINNACLE FLX研究[10]顯示,在應用新一代Watchman FLX封堵器的400例患者中,有7例(1.75%)發生DRT,而在應用了Amulet裝置的多中心研究[11]中,DRT發生率為1.60%。分析可能原因為兩種新一代裝置將其表面螺釘內嵌,進而降低了此處DRT發生的可能性。應用國產LAmbre裝置的一項薈萃分析[12]顯示,其DRT發生率低于Watchman和Amulet等裝置,為0.70%。期待進行中的研究能進一步補充LAmbre裝置的循證證據。這些DRT發生率的差異可能與研究樣本量、患者基線水平、裝置類型、隨訪檢測的時間和方法、DRT診斷標準以及術后用藥策略等不同有關。
2 DRT的發生時間
DRT在診斷時間上差異較大,大多數患者DRT出現在術后1年內,可能由于在此階段裝置表面尚未完全內皮化,進而易導致DRT的發生。然而,隨著時間的延長和隨訪次數的增加,檢測出DRT的患者數量也在增加。Simard等[13]統計分析在237例DRT患者中,分別有24.90%的患者在術后45 d內,38.80%在術后45~180 d,16.00%在術后180~365 d,以及20.30%在術后365 d后診斷為DRT。有病例報告報道了1例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后7年,經CT檢查提示一個巨大血栓附著于裝置表面[14],即使裝置表面的內皮化可使DRT的發生率隨時間的延長而減少,但仍需警惕可能存在的遲發性DRT。提示術者需對卒中高危患者增加隨訪頻次和延長隨訪時間。目前臨床上仍以經食管超聲心動圖檢查(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為診斷和隨訪DRT的標準檢測方法。由于TEE的診斷受操作者經驗的影響,且為有創操作,部分患者不能耐受。近年來心臟計算機斷層掃描造影逐漸成為一種替代的隨訪檢查方式。
3 DRT的預后
左心耳封堵術后發生DRT的患者是否會導致血栓栓塞事件風險的增加暫無明確定論。有研究[15-16]發現,在DRT與非DRT患者之間,發生血栓栓塞事件的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但也有研究發現,與非DRT患者相比,DRT患者缺血性事件發生率可高出3倍[5]、4倍[9]甚至5倍[17]。另一個研究[18]隨訪兩年發現DRT患者具有較高的卒中率(13.8%)和死亡率(20.0%),且經治療后血栓未完全消退者具有更高的心血管事件風險。故評估危險因素、識別高危患者并予以積極的管理,對降低DRT和血栓栓塞事件的發生率就顯得尤為重要。
4 DRT的危險因素
目前已有多項研究探討了DRT可能的危險因素,大致分類為:(1)患者基線相關因素,如卒中病史、永久性房顫、CHA2DS2-VASc評分和血管疾病等;(2)封堵器裝置相關因素,如封堵器類型、材料和大小等;(3)術中及術后相關因素,如術中封堵器植入位置、裝置周圍殘余漏和術后抗栓用藥策略等。
4.1 患者基線相關因素
Saw等[16]認為吸煙和女性為DRT的獨立預測因素,Fauchier等[9]則表示高齡和卒中病史為危險因素。Dukkipati等[5]對四項Watchman封堵器FDA前瞻性試驗進行了分析,認為患者短暫性腦缺血發作或卒中病史、永久性房顫、血管疾病、左心耳直徑增大和左室射血分數低為DRT的危險預測因素。
4.2 封堵器裝置相關因素
有學者[19]認為Watchman裝置一體結構與Amulet裝置分體結構相比較,其封堵位置位于左心耳頸部而近端未能完全覆蓋,導致該區域形成凹槽,血液在此凹槽中流速減低,進而導致Watchman裝置DRT的發生率更高。而Amulet IDE隨機對照試驗[20]顯示,Amulet組和Watchman組DRT的發生率相似。故對于不同類型裝置的DRT發生率是否有差異,還需更多的對比研究來進一步分析討論。
4.3 術中及術后相關因素
Pracon等[21]發現,與未發生DRT的患者相比,DRT組患者中存在更多封堵器植入較深和植入尺寸更大的情況。另有研究者[22]指出,封堵器植入覆蓋肺嵴與術后低DRT的發生率相關。血流動力學的改變是否也會導致內皮化不全,從而增加DRT的風險?有研究[23]認為周圍漏血流逸出后,使裝置表面發生異常的內皮化愈合反應,甚至發生裝置移位錯位,進而導致DRT的發生。Bai等[24]經多變量分析顯示,裝置周圍漏導致DRT的發生率增加,可能是由于殘余漏的存在使得封堵器周邊血流易形成渦流淤滯。提示釋放封堵器后,應全面仔細地評估其封堵效果。由于左心耳形態個體化差異較明顯,常用封堵器的類型以及型號并不能滿足所有形態左心耳的最佳封堵問題。目前有一款適形性的左心耳封堵器能創造出高度貼合的植入物,個性化匹配各種左心耳結構。其臨床前研究顯示,7個封堵器均成功植入犬模型并完全密封,組織學顯示術后60 d新生內皮已覆蓋在裝置表面[25]。隨后該款封堵器首次臨床應用顯示在術后45 d,18例患者中有1例出現了DRT[26]。
在封堵器表面完全內皮化之前,如何選擇抗栓方案(表1)來有效預防DRT引起了廣泛討論。
數據表明,在減少術后血栓形成的風險上,短期OAC比APT更有效。有研究[27]采用傾向性匹配方法分析術后采用APT和短期OAC治療的差異,發現DRT在APT組中更多見(3.10% vs 1.40%,P=0.014 8)。而一項納入了83項研究[28]的薈萃分析顯示,術后采用短期OAC或APT的患者,DRT的發生率并無統計學差異。隨著新型口服抗凝藥物(novel oral anticoagulation,NOAC)的發展,其也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臨床。研究者[29]在隨訪13個月后,與標準APT相比,長期半劑量的NOAC顯著降低了DRT的風險(3.40% vs 0.00%,P=0.009)。由于臨床中較多患者不耐受OAC,術者會選擇在短期內給予患者雙聯抗血小板治療(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DAPT)。在EWOLUTION真實世界研究[30]中,60.2%的患者術后接受了DAPT,1年隨訪分析采用DAPT的患者中,有22例(4.00%)出現DRT,且有1例患者發生卒中。另一項術后采用短期DAPT的研究[31]中,隨訪6周發現298例患者中有5例(1.70%)出現DRT。但對于有極高出血風險的患者,單藥抗血小板治療(single antiplatelet therapy,SAPT)也有應用。對于術后采用SAPT,隨訪發現DRT的發生率與PROTECT-AF研究中相當(3.30% vs 4.20%)[32]。一項納入110例患者的研究[33]中,術后有87.8%的患者接受SAPT,有12.2%患者接受DAPT,DRT發生率為1.90%。而法國8個中心的回顧性研究[9]顯示,術后有35.8%的患者接受了SAPT,7.7%的患者未接受抗栓治療,DRT的年發生率為7.20%,明顯高于大多數研究。基于此結果,有學者提出了對APT的擔憂,故針對于具有抗凝治療禁忌和高出血風險患者,臨床上還需更多和更大型的研究來評估這一治療方案的可行性。正在進行的ANDES隨機對照試驗(左心耳封堵術后短期OAC與APT預防裝置血栓的比較,NCT03568890)可能有助于確定術后最佳的抗栓治療,以降低DRT的發生。

表1 左心耳封堵術后的抗栓策略
DRT的預測因素大多局限在小樣本量或單中心研究中,一項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13]發表了左心耳封堵術后DRT的預測因素,該研究納入了37個中心237例DRT患者,每例患者匹配了2例術后無DRT的患者。隨訪過程中發現DRT組發生裝置移位、封堵器殘余分流以及缺血性腦卒中的比例更高,但兩組患者術后抗栓藥物的應用無統計學差異。多因素分析顯示DRT的預測因素包括:高凝狀態性疾病、心包積液、腎功能不全、裝置植入距離肺靜脈邊緣>10 mm和非陣發性房顫,并據此建立了DRT風險評分系統:高凝狀態性疾病和心包積液均計為4分,腎功能不全、裝置植入距離肺靜脈邊緣>10 mm和非陣發性房顫均計為1分,總分1分者為DRT低危,≥2分者為高危。可據此評分系統對左心耳封堵術后患者行DRT危險分層,便于對高危患者進行更積極的預防和管理。
5 DRT的治療
診斷DRT后,多數患者通過恢復短期抗凝治療或更換抗血小板藥可消除DRT,但也存在由于DRT巨大而需外科處理的病例。常用的治療方法包括:平均2周的低分子肝素治療及8~12周的華法林治療且維持國際標準化比值于2~3。對于已接受華法林治療的患者應加大劑量,使國際標準化比值維持在2.5~3.5。若患者的出血風險較低,還可考慮添加小劑量阿司匹林。據薈萃分析[34]顯示低分子肝素治療的DRT溶解率為100%,華法林治療的DRT溶解率為89.5%。DRT溶解后復發的報道較少,在真實世界研究[24]中,有3例DRT患者停止抗凝治療后DRT復發,因此3例患者將終身接受華法林抗凝治療。另有病例報告[35-36]報道了NOAC(阿哌沙班和達比加群)治療DRT的可行性。但也有病例報告[37]報道了患者術后應用達比加群發生DRT,后改用利伐沙班或華法林后血栓得以溶解。故需更多研究來分析不同NOAC的具體獲益情況。若抗凝治療仍無效或DRT巨大,則應考慮外科處理。當患者診斷為DRT后,需密切隨訪來觀察血栓溶解情況。消除DRT后,仍需繼續隨訪,以監測血栓是否再形成。
6 小結
DRT的預防和管理應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從臨床醫生可操作的層面加以控制管理:(1)根據危險因素識別高危患者并警惕DRT的發生。(2)手術操作應更加規范,確定植入裝置的大小以及植入的位置,避免發生裝置周圍殘余漏。(3)術后最佳抗栓治療目前并無統一標準,還需后續研究進一步確定方案。現可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規律的個體化用藥。(4)術后對患者進行規律的隨訪,及時檢出DRT并予以積極治療。(5)統一判斷DRT的經食管心臟彩超或影像學診斷標準。另一方面,左心耳封堵器的設計和材料的優化可降低DRT的發生風險:(1)減少裝置中暴露的金屬面積,如新一代Watchman FLX和Amulet封堵器,兩種封堵器目前的數據均表明減少了DRT的發生,但仍需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證實。(2)左心耳封堵器被覆膜大多分為聚酯膜、聚四氟乙烯薄膜和聚氨酯膜等。現在新型材料在左心耳封堵器中開始了初期探索研究,有望使得封堵器被覆膜具有更快速促進內皮化和生物降解等優點,進而減少DRT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