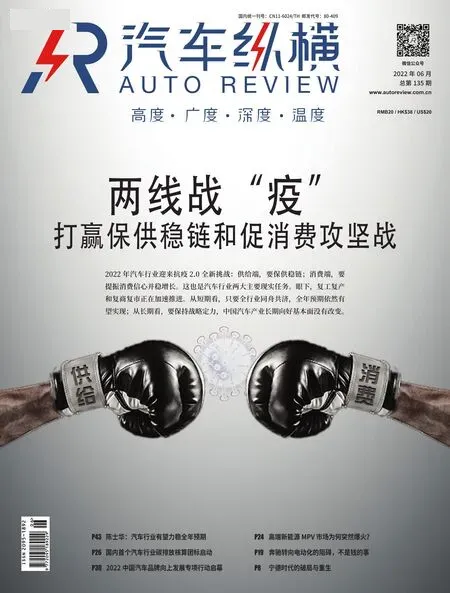奔馳轉向電動化的阻礙,不是錢的事
文 /《財經》記者 郭懷毅
編輯 / 王靜儀
不再是豪車第一不重要,這家巨頭對“油改電”路線的摒棄彰顯了電動化決心,但在2022年的中國市場,國產化率不高勢必會掣肘奔馳的供應鏈。
新能源汽車的時代風起云涌,曾經的汽車發明者奔馳也在努力追趕。
1866年,德國人卡爾·弗里德里希·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造出世上第一輛汽車,豪華品牌奔馳由此成名。
兩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的發展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電動化”。梅賽德斯-奔馳集團股份公司(FRA:MBG,下稱“奔馳”)董事會主席康林松(Ola K?llenius)再次向外界傳遞了電動化轉型的決心。
從2021年的市場表現來看,重金打造的全新純電品牌EQ系列雖然同比增長154%,可全年4.8萬輛的銷量不但落后于特斯拉等新勢力,也不敵寶馬和奧迪這樣的老對手。
好在財報數據不錯,給了奔馳一定的轉型資金條件。
為了在電動汽車市場實現反擊,奔馳一方面將投資400億歐元以實現所有品牌的電動化。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純電汽車的快速迭代,奔馳開始放棄燃油車時代的傳統戰略,從“油改電”變全面純電。
中國是奔馳最大的單一市場以及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能否在中國的新能源市場取得突破,將關系到奔馳的轉型成敗。
電動車型初戰不利
新冠疫情和芯片短缺對奔馳的銷量產生了嚴重打擊。奔馳在2021年的全球銷量為240萬輛,同比下降5%,全球豪車銷冠的位置被寶馬奪去。
奔馳倒不在意。康林松在2020年表示,對奔馳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銷量或者排名。奔馳最重要的工作是實現碳中和與電動化轉型。
為了實現電動化轉型,奔馳在2019年宣布未來幾年將投入超過100億歐元用于擴大電動車型陣容。
作為奔馳的全新純電系列,EQ系列的首款產品EQC在2019年上市后的市場表現不盡如人意,這和奔馳在傳統燃油車市場所展現出的統治力出現了巨大落差。
奔馳EQ系列目前共有四款車型,分別是EQA、EQB、EQC和EQS,最低售價36.58萬元起,2021年的全球累計銷量僅為4.89萬輛,這一成績不但落后于特斯拉(NASDAQ:TSLA)的93.6萬輛,甚至不及蔚來(NYSE:NIO,09866.HK)的9.1萬輛。在德系豪華品牌里,寶馬10.3萬輛和奧迪8.1萬輛的純電車型銷量也領先奔馳。


在中國市場,EQ系列同樣遭遇挫折。乘聯會數據顯示,2021年,主力車型奔馳EQC在華銷量僅為6098輛,甚至不及蔚來的單月銷量。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士華對財經汽車表示:“很多傳統車企的純電車型是在傳統燃油車平臺上改造而來,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油改電,這和純電平臺打造的產品是不一樣的,油改電的競爭力會不足,所以,還是需要全新純電平臺。”
就在EQ系列無法打開市場時,作為奔馳在中國的銷量基本盤,燃油車市場也敲響警鐘。
乘聯會數據顯示,特斯拉Model 3于2020年實現國產后,與其價位接近的奔馳C級在當年便出現了3.8%的銷量下滑。2021年,Model 3銷量的增長以及國產Model Y開始交付,讓奔馳在華的三大主力車型C級、E級和GLC都同時出現下滑,幅度分別為-14.8%、-9.3%和-17.7%。
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2021年初表示,隨著特斯拉國產化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特斯拉Model Y與德系豪華SUV的競爭價格關系發生明顯逆轉。尤其在特大城市中,牌照優勢會讓Model Y有更好的表現。
交強險上險數據證實了崔東樹的預測,作為奔馳在豪華SUV市場的主力車型,起售價40萬元的奔馳GLC受到了特斯拉Model Y的沖擊。
2021年,在奔馳GLC銷量最高的五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成都和杭州的奔馳GLC銷量出現集體下滑,幅度分別為-23.3%、-19.7%、-27.5%、-22.9%和-11.9%。而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了奔馳C級和E級上。
在EQ系列出師不利,燃油車又受到特斯拉沖擊的情況下,奔馳選擇了及時調整戰略。2021年7月,奔馳發布了全新的電動化戰略,此前的“電動為先”轉變為“全面電動”。
雖然全球銷量下滑,但得益于產品組合、單車定價、提高成本效率和二手車業務,奔馳在2021年營收增長9%,達到1679億歐元;凈利潤更是增長484%達到233億歐元。這無疑給了奔馳充足的資金,讓其全力實施戰略轉型。
巨人轉身,走向全面純電
“無論是在中國市場還是放眼全球,我們關注到消費者正在以比我們預想中更快的速度放棄內燃機車型,選擇插電混動車型,甚至跳過插電混動車型,直接選擇純電車型。”今年4月13日,奔馳董事會成員、負責銷售與市場營銷的貝思格(Britta Seeger)對財經汽車表示,“對于梅賽德斯-奔馳來說,我們‘全面電動’的路徑非常清晰,即大力推廣純電車型。”
從貝思格的表態中不難看出,奔馳已經將純電車型視為未來發展方向。但是,作為從燃油車平臺誕生的純電車型,“油改電”的EQC沒有贏得市場青睞,這說明在智能電動車時代,單純憑借奔馳的品牌號召力已不能包打天下。
多位業內人士對財經汽車表示,如果奔馳想將EQ系列打造成豪華純電品牌,不光需要宏觀戰略,更要拿出突破性產品,因為消費者只有通過產品才能了解一家企業,奔馳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在純電市場的反擊。
4月19日,全新EQS純電SUV在中國完成全球首秀。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奔馳亦在早些時候宣布VISION EQXX概念車首次實現單次充電下行駛上千公里。
VISION EQXX概念車自德國辛德芬根出發,以140公里/小時的高速巡航和87.4公里/小時的平均時速,歷經多重路況和復雜氣候,最終抵達法國卡西斯,全程約1008公里,且抵達時還留有約15%的剩余電量。截至目前,包括特斯拉在內的所有新老勢力都沒有做到過單次充電行駛突破1000公里。
VISION EQXX不只是一款僅供演示的概念車。“2025年,VISION EQXX概念車搭載的幾乎所有技術將全部投入量產。”奔馳董事會成員及首席技術官、負責研發和采購的薛夫銘(Markus Sch?fer)向媒體表示。
在新能源汽車快速迭代的大背景之下,奔馳還改變了一個傳統戰略。
在燃油車時代,奔馳會將全新的技術首先應用于S級轎車,然后再逐步下探到低級別車系上。
但薛夫銘表示:“如今的創新和技術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我們不會等到下一代S級問世再將最先進技術加以應用。無論是哪個級別的車型,我們只要研發出最先進的技術,就將對產品進行不斷升級。”
在“全面電動”的戰略之下,S級優先的傳統戰略宣告終結,作為過渡路線的“油改電”會逐步淡出,未來奔馳將專注于以純電優先的全新平臺。

根據規劃,2022年至2030年,梅賽德斯-奔馳計劃在純電動車型方面投資超過400億歐元,旗下所有品牌均將實現電動化。
梅賽德斯-奔馳大型純電車型架構及電力驅動開發副總裁克里斯托夫·斯塔津斯基(Christoph Starzynski)表示,今后新推出的平臺都將是電動車優先的平臺,比如接下來即將推出的專為緊湊及中型車設計的梅賽德斯-奔馳模塊化架構(MMA)平臺,從一開始就是以電動車為先的思路開發的,盡管仍具備燃油車生產能力。
從“油改電”到全面純電,這是外界對奔馳全新純電平臺的直觀感受。而作為奔馳的老對手,寶馬將于2025年推出的Neue Klasse架構也被外界認為是一個類似的平臺。
對于這兩家傳統豪門為何選擇這樣的路線,奧緯咨詢董事合伙人張君毅對財經汽車表示:“電動車銷量畢竟還小,如果只開發電動車平臺,對于一些傳統車企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兼顧純電和燃油既能夠擴大平臺利用率,也能夠分攤成本。此外,不應該把這種做法簡單視作‘油改電’的翻版,二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這種妥協的方式是不是最有效的方式,還需要市場來檢驗,否則是對于三電成本高企的臨時妥協應對。”
小心供應鏈成阿喀琉斯之踵
2021年,中國連續第七年成為奔馳最大的單一市場。同時,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
在兩個“最大”的疊加之下,中國市場對于奔馳的轉型意義非凡。中國將是奔馳發力電動化的重點地區。
2022年,奔馳計劃在華推出八款純電及插電混動車型。其中,首款基于奔馳全新純電EVA平臺的國產純電轎車EQE將在今年上市。
奔馳在3月宣布成立上海研發中心,以進一步聚焦智能互聯和自動駕駛。這也標志著奔馳在華進入北京、上海雙研發中心的時代。
對于這樣的布局,戴姆勒大中華區投資有限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研發、平臺管理、供應商管理負責人安爾翰博士教授(Hans Georg Engle)表示:“關于上海和北京兩地研發團隊的分工,北京仍將是我們在華研發工作的核心陣地,而上海研發中心會聚焦智能互聯和自動駕駛的軟硬件開發和測試。這樣的研發布局將體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進一步提高研發效率。”
在“全面電動”的轉型戰略之下,不論產品還是研發,奔馳都在中國市場做著精心布局。但供應鏈卻越來越像是奔馳在華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從功能汽車向智能電動汽車轉變的時候,傳統車企的轉型不是一個只靠投放智能電動車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包括生產、研發、銷售、供應鏈甚至公司架構的全面轉型。其中,供應鏈是一個基礎。”羅蘭貝格全球高級合伙人、大中華區副總裁鄭赟對財經汽車表示。
而在中國,轉型時期的奔馳在供應鏈這個基礎上遇到了問題。一位北京奔馳人士對財經汽車表示:“現在的生產規劃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內憂來自于上海疫情導致的供應鏈中斷,外患來自俄烏沖突,很多空運航線都變得不暢,包括一些芯片在內的核心零部件供應存在問題。”
應該說,上海疫情和俄烏沖突導致的供應鏈緊張確實是全行業都面臨的問題,但國產化率相對較低也是奔馳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華泰證券在一份研報中指出,2018年奔馳在中國的國產化率為72%。上述北奔人士對財經汽車表示:“目前,奔馳的一些國產零部件也不是完全國產,而是以組裝進口件的方式生產,所以實際的國產化率可能沒有那么高。”
對于奔馳目前的國產化率,財經汽車向奔馳方面進行了求證,但截止發稿并沒有收到相關數據。
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對財經汽車表示:“目前,國內主流合資品牌的汽車零部件國產化率在80%至90%,而奔馳、寶馬這樣的豪華品牌是70%上下。”
作為對比,2020年1月,特斯拉首款國產車型Model 3下線。2021年8月,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袁國華介紹,到2021年底,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國產化率將達到90%左右。同年11月,特斯拉全球副總裁陶琳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國產特斯拉車型可以達到近100%的本地化生產率。
在陳士華看來,現在國際主流的零部件巨頭在中國都有產能,從技術上來講,國產零部件并非替代不了,更有可能是經營上的考慮。
相對較低的國產化率已經影響了北京奔馳的產能。上述北奔消息人士對財經汽車表示:在剛剛過去的3月,北京奔馳曾出現過短暫的停產,目前的生產班次也從此前的每個工作日兩班減至一班。而更讓人擔憂的則是零部件的短缺會不會對全新EQE的上市造成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寶馬在華的生產似乎沒有受到類似的影響。2020年,華晨寶馬表示到2022年自身的國產化率將升至70%。
但在2021年,寶馬在中國的銷量不但實現了增長,還完成了對奔馳的反超。有分析認為,依仗相對穩固的供應鏈和物流體系,寶馬在面對疫情強沖擊時顯得更加柔軟且靈活,即時調整的柔性生產線,也可以將關鍵部件集中在主力車型上,從而提振銷量。
從寶馬的實踐來看,雖然強化供應鏈管理也能夠彌補國產化率相對較低的不足。但張君毅依然強調本地供應商的重要性:“各個國家的市場都在碎片化,那就更需要本地化的供應商,否則就無法滿足當地的需求。”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永遠不要浪費一次危機。對于奔馳來說,供應鏈危機也是其深化國產化率和完善供應鏈管理的良機,如果處理得當將彌補上其在中國業務的一塊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