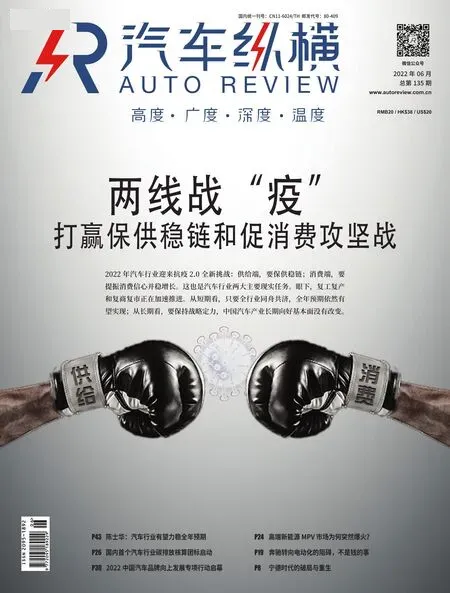博世的防疫保供行動
文 / 本刊記者 趙子垚
疫情反復、供應短缺,博世中國業務正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挑戰,但伴隨復產保供工作推進,除供應困境初步緩解外,其產業布局、本土替代等發展計劃也在著手推進。
2022年第一季度,博世集團實現整體銷售額同比增長5.2%,開局良好。但進入4月,由于新一輪疫情及物流中斷等不確定影響因素加劇,該集團早前預估的全年預期已變為過去式。“從西安、蘇州、長春再到上海,博世的幾大汽車部件生產基地先后經歷了暫時停產和閉環經營,” 博世中國副總裁蔣健接受《汽車縱橫》采訪時表示,“鑒于物流和供應鏈采購的短時影響,我們的產能暫時仍不得不受到制約。”
事實上,博世正遭遇兩頭承壓:上游,供應鏈原材料及次級供應商供給受阻;下游,整車企業正迫切要求博世提供關鍵零部件。這一窘境在今年5月近乎達到頂峰,令博世中國總裁陳玉東不得不感慨“供應不成‘鏈’”。因此,作為一家“承上啟下”的行業頂級Tier1供應商,博世在本輪疫情中面臨的局面要更復雜,其應對舉措也更具參考價值,它的復產保供進程正被賦予更多意義。
抵住沖擊
在復工方面,“得益于此前西安工廠總結的抗疫相關經驗,讓我們有準備相對應的應急管理預案。所以在新一輪疫情中,博世的幾個工廠都嚴格遵守當地防疫規定,迅速地落實各項措施以保護員工的健康安全,實現核心業務的全力保障及運營。” 蔣健介紹道。
而復產方面,截止5月中旬,博世工廠的產出仍處于爬坡階段。“目前,博世位于長春的汽車部件工廠已經恢復生產,在上海和江蘇太倉的三個汽車部件工廠以及位于上海嘉定的熱力技術工廠正進行閉環生產。但由于各工廠及產品供應情況的不同,很難用一個具體數字來說明我們整體的恢復進度。”另據5月10日博世中國2022年度新聞發布會的說明情況,博世工廠的產出約在30%~75%間波動,表明其位于不同地區的工廠仍面臨不同程度的供應和生產困局。
汽車制造并非“孤島”產業,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全行業發展的整體趨勢。對博世來說,盡可能保障主機廠生產不停線是短期內亟待解決的問題,因為放大效應的影響,每少生產1000元的汽車零部件,背后則可能意味著一輛價值數十萬元的汽車無法實現整車下線。上游次級零部件供應的情況同樣如此,再小的零件在經歷層層傳遞、放大后,最終都將影響高價值產品的產出。“所以我們當前的工作重心,就是竭盡所能、不惜成本地保障供貨,盡量降低對整車企業的影響。同時,盡我們所能協助上游供應商的復工復產。”
據悉,從上海復工復產企業“白名單”的設計到報備,博世均參與其中,提交了一份上百家供應商的復工復產名單,包含其直接供應商,還有間接的次級供應商。“畢竟僅靠放開博世這類的Tier1供應商,并不能使汽車供應鏈得以迅速恢復供應。所以在員工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我們建言滿足疫情復工條件的企業只要愿意做閉環生產,便盡可能批準復工安排,以此來打通供應鏈。”當前,博世大約3/4的直接供應商已經復產復工,其余供應商正在逐步恢復中。“但客觀來說,大家的產能均不充足,仍處于一級接一級的傳導狀態。”這里他以一家五級供應商的情況做舉例,“上海的一家小型涂層供應商不復工,它下游某個汽車零部件便進行不了特殊化學物質的涂層工藝,進而我們的生產進程就無法把握。”
與此同時,由于各地趨嚴的疫情管控措施,使得物流不暢問題愈發凸顯。“物流端也是本輪疫情中比較棘手的問題,因為即便我們的第四、五級供應商全部實現工廠閉環生產,但原料無法按需供應,則是在源頭上直接‘斷流’供應體系。”而在這樣的特殊時期里,原料運輸的成本正在急劇攀升,甚至出現有工廠花費平時25至30倍的額外費用來保障緊缺材料的運輸供應。為此,工信部、上海市相關部門、主機廠和各級供應商都在努力推進相關事宜。“我們正盡力與上級供應商和物流合作伙伴保持密切溝通,積極分享疫情防護和閉環生產等經驗,為他們的復工復產提供幫助,盡快熬過保供和產能爬坡的這段時間。”
強化韌性
4月的汽車產量幾近“腰斬”,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當月汽車生產僅120.5萬輛,相較去年同期損失了約100萬輛的生產量。由此,當前汽車工業推崇的精益生產體系以及普遍執行的 “零庫存 ”供應鏈管理模式正面臨著新的風險,如何保證供應鏈不“斷供”,已然成為主機廠和各級供應商需要思考探究的課題。
“誠然,在疫情反復、供應短缺的挑戰下,為了規避可預見的風險,汽車企業和供應商可能會增加相應的庫存,” 但蔣健認為,這并不意味著精益生產方式走到了終點。“博世將根據市場情況靈活調整戰略,并與生產、供應、物流等各個環節的合作伙伴通力協作以保障供應。”
對其自身產業布局,博世正趨向根據下游整車企業的地理區位就近布局,并圍繞當地的產業特點進行投資、產能擴建。“目前,博世的產業布局以長三角地區為主,利用該地區的一體化優勢,我們可以增強人才集聚,進而發展我們的研發和總部基地。當然博世的未來不會局限于長三角地區,而是會根據客戶和市場需求進行布局。”
“目前我們的兩大側重面—氫能和智能軟件同樣在進行布局開拓。”蔣健補充說。在氫能方向,博世在重慶和慶鈴成立的合資企業,和威孚共同成立氫燃料電池零部件業務合資公司,以及和濰柴、Ceres Power成立三方系統合資公司,做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生產。對另一個面向未來的智能駕駛方向,博世已在蘇州成立智能駕駛與控制事業部,聚焦智能座艙、輔助和自動駕駛兩大技術領域。目前,該事業部的中國區團隊成員已超過 1200 人,研發人員占比近88%。
除增加區位分布的布局外,博世也正通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技術創新,為供應鏈“技術賦能”,進一步提高生產和供應的靈活性。“例如今年獲評世界經濟論壇‘燈塔工廠’稱號的博世長沙工廠,便通過數字智能決策、端到端智慧物流中臺等方式,全面打造敏捷、高效的供應鏈網絡。”
轉移替代
缺芯問題是全球行業持續面臨的巨大挑戰。各大整車企業芯片需求的增長,特別是隨著全球疫情反復和新能源汽車產銷量的急劇提升,正導致各種包含芯片的零部件產品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包括博世ESP/IPB等產品。由此,博世為緩解供應壓力,正著手于更多有利保證供貨的計劃。
“首先作為芯片供應商,博世已盡可能擴大現有的生產規模。例如正在擴建的德國德累斯頓和羅伊特林根晶圓工廠,以及對馬來西亞檳城州半導體測試中心的建設規劃。”在國內,博世也對位于蘇州的MEMS 傳感器測試中心進行產能升級,以滿足汽車和消費領域對 MEMS半導體不斷增長的需求。“但我們也同時看到,由于行業結構性問題和一系列‘黑天鵝’事件的影響,芯片供應還未回到芯片危機之前的狀況,僅靠我們自身很難對當前的芯片缺口產生更多積極效應。”

因此,博世正通過另一重的芯片采購商身份,積極評估和探索芯片的國產化替代。“半導體是最全球化的產品之一,相關企業在全球布局非常廣,所以我們也在呼吁和鼓勵半導體供應鏈的國產化,提高車規級芯片的基礎產量。”與此同時,博世也在積極扶持國內的芯片企業。“車規級芯片的制程要求不是很高,工藝要求一般都在48納米以上。而國內的芯片企業雖大部分以芯片設計為主,但仍有相當企業具有代工能力。為此,我們有專門團隊來跟蹤國內芯片企業的動態,了解這些企業的產能及制程工藝情況,通過參股以及技術扶植等方式進行相關投資和布局。”目前,部分國產車規級芯片已經進入博世的芯片供應鏈,但一些涉及車輛安全的芯片短期內仍無法實現本土替代。
在芯片供應鏈替代計劃外,博世近期仍以增強國際物流端的供應暢通作為保障主線。“只要海外封測工廠的芯片可以運出,我們的物流團隊便不計成本地將這些成品芯片運進中國工廠,轉化為急需供應的控制器等產品。”蔣健表示。
事實上,汽車相關業務已占到博世中國業務約75%的銷售份額,2021年,僅汽車與智能交通業務板塊銷售額便達到967億人民幣。博世集團新任董事會主席史蒂凡·哈通(Stefan Hartung)此前表示:“中國繼續保持博世集團最大的單一市場地位。” 雖然復產保供令博世中國業務正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挑戰,但隨著供應端困境的逐步緩解、產業布局的更新以及本土替代發展計劃的推進,其供應鏈的穩定性正在獲得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