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之歌
黃熙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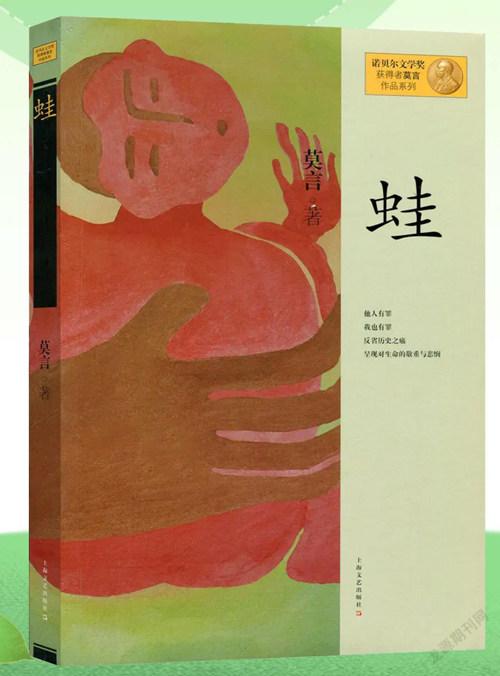

我用幾天時間讀罷全書,竟讀得意外順暢:《蛙》這本書沒有《檀香刑》中血腥重口味的描述,沒有《生死疲勞》里天馬行空的情節,也不像《豐乳肥臀》龐大雜亂的結構,它真實平淡地濃縮了鄉土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圍繞著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展現出各種人群在“計劃生育”大背景下不同的命運。
讀到一半,我便不覺產生了疑問:為何以“蛙”為題?直到接近作品的尾聲,半瘋癲狀態的姑姑才點出:“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狀相當……為什么蛙與娃同音?為什么嬰兒剛從母腹出來時哭聲與蛙聲十分相似?為什么我們東北鄉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許多塑像娃娃懷抱著一只蛙,為什么人類的始祖叫女媧?”“wā”被賦予了各種含義,但由一個喻體引申出的多個本體,都與生命有關。這本書不僅是單純的紀實作品,還記錄了鼓勵多生時期,計劃生育時期和現如今人們對待生命的不同態度,充分演繹出在各種時期“蛙”所喻本體的變化。
在鼓勵生育期間,主人公的姑姑萬心在四年間接生了1645名嬰兒,幾乎為零的失誤率使其被冠以“送子娘娘”的美稱。正如書中的描寫,“她將嬰兒從產道中拖出來的那一刻會忘記階級斗爭,體會到的喜悅是一種純粹的感情”。莫言用無數個動詞“飛車而下”“沖”“搡”“扯”等把一個熱心正義,熱愛生命的婦產科醫生呈現在讀者面前。四年間,高密東北鄉經濟繁榮,新生兒人數倍增,這時候“蛙”是生機勃勃的意象。雌蛙每次能排出大約八千到一萬粒卵子,如此快的繁殖速度象征了生命的強盛和蓬勃。
好景不長,“計劃生育”政策落實后,忠誠敬業的姑姑便從“送子娘娘”變成“殺人的惡魔”。姑姑篤定地響應黨的號召,奔波在每個鄉鎮之間,給男人結扎,給女人帶環,做各種流產手術,成為了公社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實施者,同時也成為了“重男輕女”思想的主導抗衡者。正因為阻斷了一貫的傳統,加大了某些家族“斷后”的可能,姑姑被視為全民公敵。盡管如此,她仍然一絲不茍,盡最大力度打擊超生。這時候的姑姑似乎被新政策“洗腦”,似乎并不像從前那般充滿神圣和敬畏地對待生命。但果真如此嗎?讀到這里,我不禁想起村里同樣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的表哥,他需要做的也是在村鎮里搜查超生的人。實施者往往處在計劃生育工作架構的最底端,這也是政策的優劣之處。這類人受保護程度低,可能會被該家族暗中報復。但也正因如此,想用金錢了事的許多人,無法瞞天過海。可見即便是在現在,社會上也需要有“丑人”和負隅頑抗的落后者作斗爭。何況,當孕婦在逃脫中生命垂危時,姑姑也毫不猶豫地去接生救人,盡管在經歷生死時速的搶救后,只換來一句嘆氣,道:“又是個女孩。”
無數的罵名終究給姑姑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創傷。姑姑噩夢纏身,“那天晚上蛙聲如哭,仿佛是成千上萬的初生嬰兒在哭……對于一個婦產科醫生來說,初生嬰兒的哭聲是世上最動聽的音樂啊!可那晚上的蛙叫聲里,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是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這時候,“蛙”是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被姑姑做流產手術時抹去的生靈,但這又何嘗不是那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下的犧牲品呢?
時代在更替,觀念在轉變,值得肯定的是生命無可比擬的意義。莫言在書中寫道,“生育繁衍,多么莊嚴又多么世俗,多么嚴肅又多么荒唐”,它神圣莊嚴,是因為一個細胞被孕育成熟,脫落母體來到世界上,品嘗酸甜苦辣,體會人情冷暖,何其幸運!它世俗,是因為生育不是空中樓閣不可攀越,它是每一個家庭都應該經歷的。它嚴肅,是因為當一個生命的誕生,就有活著的權利,有獨立的思想,有充沛的情感。它荒唐,是因為總有一些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在生命誕生前后賦予其負面的影響。
在對于蛙的各種隱喻當中,莫言傳達出孕育生命的珍貴與偉大,這種偉大是超越一切的、神靈般的存在物。但令人感到沉重的是,在莫言構造的三個時段中,每個時段的人們都被不同的落后思想纏繞,從而衍生出各種巨大的矛盾,而矛盾背后的人們都沒有給生命以足夠的尊重。莫言在多種沖突的環境中,細致入微地描寫了被腐朽思想蠶食的個體,被貶損的蒼白無力的生命,虛假無效的自我救贖,隱晦地表達出他的生命傾向,謳歌了生命的至高無上。
《蛙》無疑是一本生命之書。書中所描寫的生命形態多種多樣,是尚未出生的嬰兒,是母愛泛濫的小獅子,是秉正無私的姑姑,是中立愧疚的萬小跑……這些角色都會在溫暖的母體中孕育出的細胞,卻對生命有如此迥異的演繹。
生命如蛙,而蛙聲不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