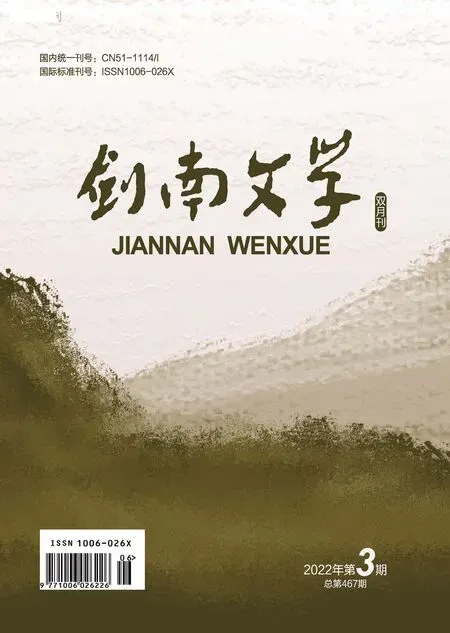遂州詩稿(組詩)
□白鶴林
赤城湖
在一輛開往春天的汽車上,
我坐在一位女士的身旁。
她和另外一個沉默的女人,
來自我向往已久的新疆。
“新疆是個好地方……”
我在心里反復念叨這句歌詞,
手中接過那位漂亮女士,
第二次遞過來的酥油餅。
我們一同要去的縣城蓬溪,
也是我從未去過的地方。
兩個女人要回久違的故鄉,
看望不愿死在新疆的老外婆。
我要去見的幾位詩人,
一位在公安局埋頭讀書,
一位在法院審判欲望,
另有兩位在學校授業傳道……
赤城湖跟我想象中的相差無幾,
家鄉的詩人也都一見如親人。
但多年以后我還一直記得的就是: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
在當年長江賈島主簿治下的詩人中間,
在赤城湖湖中央的那個小島上,
當一片冬天的樹葉緩緩飄落,
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像個外地人。
有朋自故鄉來
有朋自故鄉來,
又喝了一夜的酒。
那些酒,在曲折的身體里——
一天都低吟淺唱,
一天都躊躇滿懷,
一天都不亦樂乎。
好像還在為有朋自蓬溪來
而興奮。散發著
柚子和故鄉的氣息。
登古讀書臺
這些路和樹,
是記憶的標點,
曾給遠行的少年斷句構篇。
而今少年已兩鬢斑白,
它們卻似乎改變無多。
這些山和水,
是沉默的鄉親,
一代又一代無言地活著。
卑微如草木榮枯,
飄零于悠悠天地。
春去春又來,
千年或萬載,
不過是詩人的四行悲嘆。
不過是一個個生命,
往來于人間苦海。
登上那孤絕的峰頂,
俯瞰山下的江水,
恰似時間不舍晝夜流逝。
恰似子昂的憂思傳承,
將我們迷惘與偏狹的心胸舒展。
兩個陳子昂
在射洪,
我見到兩個陳子昂:
山上的陳子昂,
和城里的陳子昂。
金華山上的陳子昂,
坐在山上讀書。
射洪城里的陳子昂,
站在廣場上瞭望。
我感覺山上的陳子昂,
顯得孤獨。
城里的陳子昂,
面容慈祥,
還略微發胖。
這可能是因為,
山上讀書的陳子昂,
依然憂國憂民。
而廣場上瞭望的陳子昂,
看到了鄉親的夢想。
游觀音湖
房子也愛旅游。在悠悠畫舫間,
回屋的人
就漂游在了江湖。
而夜色如酒水,正漫過
幾個偶然歸鄉或故地重游者的
仲夏夢。
穿紗衣的美人兒,都是自家幺妹。
一曲《人間遂寧》的
曼妙清音,帶來別樣鄉愁。
讓我也來卡拉OK。
管他張學友,還是《枉凝眉》,
現代古典都文藝。
移動電話如果不欠費,我可能會接到
剛才滾落的那瓶礦泉水,
從涪江深處打回來的
還鄉報告。
當微風吹拂空調機,
你正朗誦星空詩。
詩酒令:還鄉
“夜色如酒水……”多年前某日,
我在遂州觀江潮。因為人多,孤獨得就像
一首有點醉意的還鄉詩。
好酒就是一首好詩,有個性,有回味,
更有情懷。所以一切盡在不言中。
酒在瓶中,它的情懷無人能知。
人隱于市,我等大可佯裝天真。
酒之所以誘人,全在于它的天真。
李白是個天真的人,所以他最愛的是飲酒。
但李白酒后從不寫詩。他只寫行酒令。
除了李白,杜甫、陳子昂、李調元幾位
好像酒量都高。當然時隔太久,我也只是估計。
靈泉寺前的斷想
不是寺前
金黃的樹葉在落,
而是我們
心中禪宗的思想在飛。
不是我們
趕在黃昏前登上了靈泉山,
而是夕陽
恰好映照到山峰一側。
不是游客
在參拜古老的觀音廟,
而是萬物
一直在惠澤眾生。
在宋瓷博物館碰鼻
歷史是一面
厚重而無形的墻。
沒有色澤,
也無裂隙。
恰如隔離著
那作為鎮館之寶的
青瓷荷葉蓋罐的玻璃。
當我欲近身打量
青瓷的細節時,
歷史便不忘
及時來提醒我——
凡是對美的欣賞與批評,
都必須保持
恰到好處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