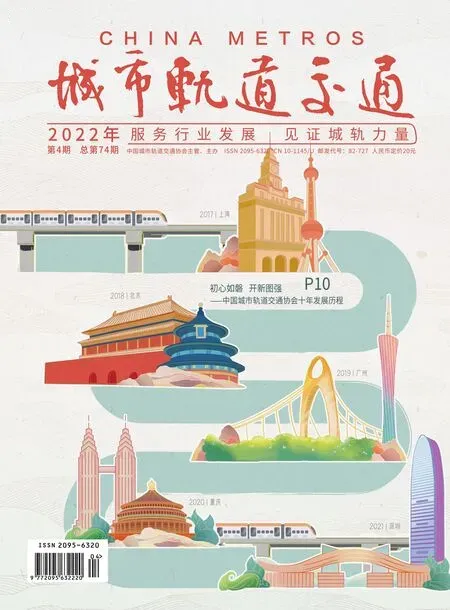中國城軌口述歷史賀長俊訪談錄:地鐵設計實踐出真知

【人物小傳】
賀長俊,原北京城建集團副總工程師,新中國第一代地鐵設計師之一。他是城市軌道交通行業的先驅者和見證者,從業五十余年,親身參與并見證了中國城軌交通從設計圖上的一個點,到如今的星羅棋布。
采訪時間:2020年7月29日
采訪地點:北京·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協會
主持人:您是北京鐵道學院(北京交通大學前身)最早畢業的一批城市軌道交通專業學生之一。
賀長俊:對。我是1957年考入北京鐵道學院,當時學院建筑系包含三個專業——橋梁、隧道、線路,最后我選的是隧道和地下鐵道專業,后來叫地下鐵道專門化。我的畢業設計就是地下鐵道車站。
1962年畢業時,國家還沒有地鐵,我在蘭州做了三年多工程建設工作。那時從測量開始,所有的技術活都是一個人做。那段時間確實鍛煉了人,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主持人:1965年,北京地鐵正式開始招兵買馬,您是怎么從西北回來的呢?
賀長俊:1965年4月,北京地鐵就要“上馬”,到全國鐵路招人。我是學地下鐵道的,而周恩來總理恰巧有個批示,就是學習地下鐵道的人一定要回來。當時地鐵有一些人就是原來的籌備處和地鐵局,后來還成立了設計處,于是,我從西北回到北京,一下車就被拉到設計院,當時的辦公地在北京飯店后面(霞公府4號),西邊那個樓就是設計處。
主持人:那時候的團隊很年輕。
賀長俊:團隊里像王元湘、沈景炎等人,年齡都在二十歲至三十歲,都是那時候從各地調回京的。三十歲回來的老同志很少,我比他們年紀大,因為我家里困難,上大學很不容易,所以比他們都晚了兩年。
我到了設計院以后,當時要求7月1日開工,施工圖設計完成后就得趕緊做。當時我在區間組,組長是王禾,我們倆在一個辦公室,但快就把我調到當時設計處的老三科。老三科即防護科,包括防原子、防化學、防細菌武器等方面。
主持人:那是因為當年我們北京地鐵是戰備為主,兼顧交通,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工程還是很神秘的,這中間有一些國防需求。
賀長俊:沒錯。當時北京地鐵1號線從北京站到蘋果園這一段,代號“401”戰備,但是以戰備為主,還是交通為主,當時是有爭議的。最后是鄧小平講,地鐵是戰備工程也是交通工程,以戰備為主,兼顧交通。所以,1號線的防護標準就比其他的地下工程要高。我調到防護科以后,年輕又是黨員,還要負責保密工作。那時候我們科經常到原來軍委工程兵設計院和防化兵部去做口部防護。為了做好口部設計,我們都是從王府井駐地,騎自行車沿線考察。印象最深的是時任組長孫毓賢帶領我們騎自行車從王府井出發到八寶山,一直往西,針對整條線路的每個站口進行定制出入口防護。
由于當時沒有計算機,復雜的結構計算和斷面是完全靠筆算的,好一點就拉計算尺,個別的用手搖計算機。特別是畫圖,我們要在硫酸紙上畫鉛筆圖,畫完了以后交給復核員,復核員非常負責任,不是隨便看看,他要把圖上每一個尺寸都標出紅點,以此說明完成復核。之后,我們再鋪上硫酸紙描圖,像一些大的設計院,比如鐵一院和鐵二院都有描圖員,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畫出鉛筆圖,交給描圖員硫酸紙描圖;我們沒有,都得自己描。特別是為了趕期出圖,時間十分緊張。那段時間禮拜天都不能休息,把孩子擱到樓道里,我們就在那兒畫圖,經常晚上9點以后才回家。當時這些設計圖就是這樣做成的。
主持人:當年有沒有這種設計標準、設計規范呢?還是邊做邊出規范?
賀長俊:我們是從外面調回來就直接搞設計。但有些老工程師,比如周慶瑞,他們在籌建處編了一個《地鐵隧道結構設計規程》,我們參照這個規程來設計。一邊學一邊設計,做一些樣板,跟部隊的人一起商量著完成一些防護設計。
設計處當時壓力也挺大的,畫圖畫得特別仔細,像現在看圖紙,鋼筋等就簡單一個數字,但那會兒,包括鋼筋彎鉤半徑多大,接線段后空格,都標得清清楚楚。有一些斷面上點一個點兒,就代表縱向鋼筋,可能代表幾十噸鋼筋就沒有了。
按照現在的說法,《地鐵隧道結構設計規程》實際上是一個企業標準,那時國家也沒有搞過國標,就只能是一邊做,一邊制定標準。那個年代可能都是這樣,相當不容易,后來一期二期我們全是用這個規程來搞設計。直到北京地鐵5號線和復八線,才慢慢有了設計規范和施工規范。
主持人:您是搞結構的,這些設計完成后還需要現場配合,那時候經常下工地?
賀長俊:下呀!當時有地鐵工程局,還有鐵道兵十二師,都來參加,有時候我們會去現場技術交底,配合現場施工。為了“七一”開工,大家加班加點搞設計,所有設計人員6月30日晚上都沒回家,幫著曬圖、文整、裝訂,凌晨兩點鐘完成裝車后稍微休息了一下,7月1日五點鐘參加開工典禮。
開工典禮在八寶山舉行,朱德、鄧小平、李先念、彭真、羅瑞卿等中央領導參加。先是現場破土動工,然后在政治學院禮堂做了開工動員報告,由羅瑞卿主持,彭真講話提及蘇聯原來都是深埋,后來他們也搞過淺埋。就深埋和淺埋的問題,我們也做過兩個深埋的試驗井,地下水確實難處理,哪怕是今天百米下做地鐵也很困難,更何況那時。當時采取淺埋加防護的方法是比較符合實際。
主持人:1999年,我到勘測院當院長,在檔案室看到了兩套完整的地質資料,一套紅皮,一套藍皮,其中一套就是我們當年全部完成的北京地鐵1號線的70米勘測。當時要搞深埋還是要搞淺埋,基礎工作都做好了,就等著決策,當然最后選擇淺埋方案。
賀長俊:深埋還是淺埋的方案爭論了很久。1958年成立地鐵局,曾經到蘇聯去訪問過,回來后定的深埋,但深埋確實問題比較多,最后還是從唐院調來北京的施仲衡院士,建議采取淺埋加防護比較合理。北京地鐵1號線通車以后,從1970年開始,我們就開始了2號線的環線設計,從建國門出發,經東二環、北二環、西二環,最后到達復興門,共計12個車站。初步設計是我來組織做的,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很擔心。
主持人:在運動最高峰的時候,生產沒有停,做設計,有些程序比如復核、審核等還能夠保證嗎?
賀長俊:基本程序還是有的,質量絕對還是要嚴格保證。當時組織的人手比較精干,也有1號線的設計經驗了,反正都是明挖車站,區間也是明挖的,沒有什么特殊的、復雜的地段,所以,設計很快就做出來了。為將來的線路也預留了大量換乘節點,像雍和宮、積水潭等都做了預留,當然后來大部分沒用上。
這個期間,環線建設都是明挖,為了保護文物,拖得時間比較長。我印象最深的是雍和宮地鐵站,雍和宮后邊那個大殿有一個很高的檀木站立佛。怕出現問題,我們做了監測,例如在佛手上拴個垂球,一直垂到腳面,用以監測變化情況,比如位移、傾斜等,各項施工都是比較嚴肅、嚴格的。
主持人:搞環線的時候,咱們已經穿上軍裝了吧?
賀長俊:一開始還沒有,我們這批穿軍裝的工改兵是1970年正式劃歸鐵道兵。說起穿軍裝也挺有意思,我當時在的老三科,基本上所有人各方面都經過嚴格考量,家庭出身各方面都比較好,我們科室參軍,第一個就是我,然后一個一個批準參軍。1970年作為鐵道兵,定的部隊代號叫總字507部隊;1976年又改為基本建設工程兵,之后就一直到1983年脫下軍裝。這期間,我們部隊多次搬家,一開始在和平里、陶然亭,之后搬到恭親王府,1976年搬到西二環,一直到1983年兵改工,成立北京城建集團。
主持人:從1970年工改兵,到1983年兵改工,這段時間是不是流失了不少人才?
賀長俊:對,那時候因為家庭問題和社會關系問題,調走了一大批優秀人才。1983年兵改工后,成立了集團,我還是留在設計院工作,地鐵這時候已經沒有什么活干了,設計院就把工作重心轉到房建上了,搞一些房建設計。當然,院里還是留了一批人,繼續做一些地鐵的研究工作,像防水、防護密閉門、軌道的密閉等。
主持人:北京地鐵一二期建成以后停了很長一段時間,后來就有了復八線。復八線建了十年,對施工方法的創新還是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一二期是以戰備為主、交通為輔,到了復八線,就完全是城市交通工程了。
賀長俊:1992年,地鐵復八線開始“上馬”。1986年王夢恕院士引進了淺埋暗挖法,復興門到西單的折返線1.81公里,這一段試驗成功。珠玉在前,復八線基本上都是以暗挖為主的;永安里、大北窯都是蓋挖逆作,只有四惠和四惠東是地面明挖車站。王兆民是復八線的設計總負責人,我是當時現場的指揮長,負責全面組織現場工作。
大北窯車站蓋挖逆作是劉俊卿設計的,這里原來有一個危橋。橋樁是獨立基礎的2米埋深,我們臨近它的基礎,欄桿投影只有1.5米。如果按當時一般的明挖,就會很費勁,橋的安全也會出問題。暗挖也很困難,這個地方地下水比較高,還有流沙什么的,最后定的用蓋挖逆作法施工。地下連續墻做成木結構,施工過程中對這個橋做了很好的保護,不光我們監測,橋洞中管橋的也天天監測,兩邊配合來保證這個橋的安全。
現在國貿橋東南角的匝道橋,按橋梁建設計劃,正好落在地鐵上面。當時我跟建委謝主任提出來給三個月時間,把過三環橋這一段區間用明挖法搶過去,再做橋。謝主任說沒有這時間,先做橋,將來就用暗挖去解決。
第一個面臨的巨大考驗就是樁基的荷載。地鐵蓋完的一座樁基,本來就要承載很大的重量,又要先做這個橋,荷載就更大了。為了達到這個要求,需要用直徑2米的鉆孔灌注樁才行,但當時國內1.5米直徑的鉆孔樁都沒有。我們跟劉俊卿一起研究,最后根據摩擦樁的原理,用連續墻的施工抓斗,搞出了第一個實質性鎮壓樁,這樣承載面積、摩擦面積就比較大,承載就夠了。我們還依次解決了諸如護筒在鋼筋籠子下怎么做等一系列難題。
另一個大的困難是要在飽和水的粉細砂地層暗挖施工。降水沒有條件,需要注漿加固,那時候注漿技術不行,我當時曾經找煤炭研究院的來注漿,沒有注好。最后不得已做了水平凍結,一下要搞40多米長的水平凍結,難度比較大。水平凍結怎么做呢?我找到廊坊一個非開挖技術研究所,說打是可以打,非開挖技術可以用,但是探測技術只有無線探測。當時,大北窯車站的旁邊是一個高壓電力溝,離車站也就1.5米的距離,如果用非開挖技術無線探測的話,無線探測保證不了精度。最后沒有辦法,咱們只能買美國人的有線探測技術來做,這項技術要找我拿70萬美元,那陣兒咱們可拿不出這70萬美元。最后,我跟煤炭院建井所搞凍結的同志(即陳湘生院士),一塊配合,他搞凍結及技術研究,我在地鐵這方面給他出主意怎么樣布置凍結管。我們用常規的水平地質鉆,先在一條隧道里打約50米長的管子,然后再用燈光測距測量每一個管子的精度,確實能滿足要求,就做了45米長的水平凍結,當時是國內最長。
當時,劉建航院士、王振信同志都覺得還是相當不錯,所以地層的凍結施工主要就是水平凍結。我們還在復八線搞了八王墳大平臺,占地36公頃,是當時國內最大的一個車輛段。地鐵上要開發120萬平方米,平臺60萬平方米,上面再蓋60萬平方米的房子,地下兩層是軌道層和辦公設備用房層。我們院葉飛總工程師做總建筑師,東西長2000多米,南北寬300多米,要做一萬七千根鉆孔灌柱樁,是很大的難題。按照樁基規范,每一百根樁要做一組靜載試驗,一萬七千根樁就要做170組。錢、設備、時間,我們都沒有。于是,我跟葉飛商量就沿著全長斜線做了四組試驗。試驗證明都是可以的,我們就用這個結果做的樁基設計。當然,也曾經出現過問題。因為不符合樁基規范,被舉報到建委。建委當時的總工程師袁祖陰組織開會,中國建科院樁基編寫組組長劉金礪、北京地質勘察院的勘察大師張建明參會,我跟他們交換意見,最后都同意四組試驗即可。
還有一個抗震的問題。120萬平方米的建筑下走車,這是個大問題。我們跟設計人員一起到汕頭考察,為什么?因為受臺灣地震影響,汕頭很多房子都出現了裂紋等,只有一座房子沒事,什么問題都沒有。我們就專程去看了這個房子,它是在柱子底下做了抗震墊。這個案例對我們很有啟發,于是把抗震墊引入大平臺項目,在每根柱子下面都放了一個大的抗震墊,抗震性能比較好。復八線1999年9月28日通車,我是2002年退休的。
主持人:您退休以后,實際上并沒有離開您心愛的行業,而是一直在給北京市軌道交通當顧問,尤其是在搶險這些特殊時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賀長俊:退休以后確實沒有閑著,一直在參加設計審查,包括設計院初步設計審查、施工圖審查、施工方案審查、現場問題處理等,幾乎全國所有地鐵設計院的圖紙我都審查過。
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全國地鐵工程建設遍地開花,但是地鐵行業有經驗的人不多,十幾年的時間里的事故不少。其中,我參加了北京所有的土建工程事故搶險,直到今天我的手機還是24小時開機。京廣橋那次塌方,我當時在成都地鐵開會,早晨5點接到電話,立刻飛回來。當時,市里領導都特別重視,每天在京廣大廈開會,布置搶險,此次塌方事故造成整個東三環斷道半個月,做完防范搶險后,京廣橋這個區間,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時間才恢復過來。
21世紀的前十幾年,常有這些事故發生,住建部加大了地鐵建設的安全管理,要求各個地鐵公司都必須加強這方面管理。基于此,我們要求,一個真正好的地鐵設計人員,不僅有理論知識,有計算本領,更要有一定的施工經驗,通過經驗去修正計算,還應該到工地周邊調查和實際考察,用工程類比來修正你的設計,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設計。但是那時候地鐵建設這么快,哪有那么多有經驗的人?怎么辦?培訓!
北京地鐵5號線“上馬”伊始,崔玖江組織我們幾位專家,辦了七期地鐵培訓,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培訓了幾千名地鐵建設人員。我當時的授課就是總結搶險的經驗教訓,給大家講地鐵事故和風險預防。后來,我在很多城市都講過,預防的措施是什么?現在我們怎么辦?
首先,勘測是設計的基礎,如果能把勘測做好了,把地質資料弄得很準確,最起碼就能預防很多起事故。復八線多起塌方事故,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就是城市地下管線滲漏水。如果一開始就把勘測做好,把現場調查清楚,我相信不會發生那么多起因滲漏水導致的塌方事故。
其次,就是設計人員真的要精心設計。施工人員也得有經驗,現在大家的風險預防概念加強了,設計有風險專項設計,施工有專項施工方案,專項方案又有專家去審查。專家定了意見以后,設計和施工人員心里就會有底。這么看來,我還能發揮點余熱。
主持人:您還是要保重身體,您的身體、經驗是行業寶貴的財富。
賀長俊: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去培養年輕人。我們五十年做了五千多公里的地鐵,就各種地層積累的經驗相當豐富。我相信現在已經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地鐵人才,是完全可以把地鐵建設得更加輝煌。
主持人:我們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軌道交通大國,正在向著軌道交通強國的方向前進。這個過程是幾代地鐵人努力的結果,尤其是你們這些老同志,確實是全身心地交給了城市軌道交通行業,使得我們現在后繼有人,有更多的人才涌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