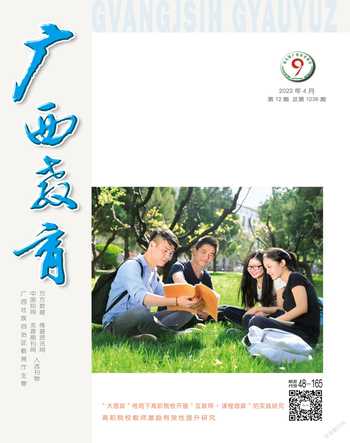小文化 大產業
陳嵐嵐 馬金娟
【摘要】本文從忻城土司文化遺產助推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視角,探究忻城莫氏土司的發展概況,挖掘其蘊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教育引導功能,分析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遺產當代傳承與發展的創新路徑:加強政府主導,拓展宣傳渠道;深挖文化內涵,開發文創產品;完善制度法規,強化支撐要素保障。
【關鍵詞】莫氏土司文化 旅游產業 文化傳承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22)12-0016-04
旅游消費是在人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之后而產生的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如何依托旅游資源,促進文旅融合,推動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鄉村振興步伐,是廣西忻城土司旅游轉型升級的重點。忻城莫土司衙署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較完備的文化遺產基礎和條件,土司文化賦能地方旅游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基于此,筆者在查閱文獻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探究忻城莫氏土司的發展概況,挖掘其蘊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教育引導功能,針對其在發展旅游產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創新路徑,以期忻城土司文化能夠不斷適應新時代的市場需求和游客需要,實現文化遺產傳承與旅游發展的良性互動,也為高職院校更好地進行旅游相關專業的課程改革提供方向指導。
一、忻城莫氏土司概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的地方政權組織形式和制度。
從明代起,中央王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共任命197家土司,忻城莫氏土司便是其中之一,其歷經數百年傳承與發展,積淀了豐厚的歷史文化。
(一)莫氏土司歷史沿革
據《明史·廣西土司傳》和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土官莫景隆修撰的忻城土官《莫氏宗譜》記載,元朝至正年間(公元1341—1367年),忻城莫氏土司始祖莫保(第一任土官)因隨官軍征討粵西有功,官封千戶,屯住慶遠府宜山縣之八仙,奉調協理忻城縣事;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莫賢(第二任土官)被總兵官山云任命為忻城土官知縣,協助流官知縣“撫化”土民;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莫敬誠(第三任土官)被任命為土官協理知縣;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兩廣總督鄧廷瓚上疏朝廷,降忻城為土縣,莫魯接縣印,莫氏世襲為土官。之后,歷由莫廷臣(第五任莫氏官)、莫應朝(第六任土官)、莫鎮威(第七任土官)、莫志明(第八任土官)、莫恩光(第九任土官)、莫恩輝(第十任土官)、莫恩達(第十一任土官)、莫猛(第十二任土官)、莫宗詔(第十三任土官)、莫元相(第十四任土官)、莫振國(第十五任土官)、莫景隆(第十六任土官)、莫若恭(第十七任土官)、莫世禧(第十八任土官)、莫昌榮(第十九任土官)、莫繩武(第二十任土官)世襲。直到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最后一任土司莫繩武因“縱匪殃民”被撤職止,莫氏土司持續統治忻城近500年。
(二)莫氏土司文化遺產
歷史文化遺產不僅生動地述說著過去,也深刻影響著當下和未來,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子孫后代。從元至清,在近500年的莫氏土司統治歷史長河中,忻城縣積累了豐富的土司文化資源,形成了獨特的土司文化遺產,對忻城人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主要形態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種。
1.物質文化遺產形態
忻城莫氏土司文化主要包括土司建筑、文物資料、文化遺跡三種物質文化遺產形態。
(1)土司建筑文化遺產。莫土司衙署位于忻城縣翠屏山麓,于明朝萬歷十年由第八任土官莫鎮威始建,之后經過歷任土官不斷修繕和擴建,逐漸形成了以土司衙署為建筑中心,以圍繞衙署而建的祠堂、官邸、大夫第、參軍第、三界廟、練兵場等附屬建筑物,向東西方向延伸的主要建筑群。衙署總面積 38.9萬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積4萬平方米,是全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土司建筑群,被譽為“壯鄉故宮”。
(2)土司統治實物資料。忻城莫土司衙署同時也是忻城縣土司博物館所在地,目前館內共有3 000多件藏品、16個大小展覽室、1 000多件展出文物,這些文物包括金器、銀器、玉器、兵器、竹木器、墨寶、手稿、文書等。與全國其他景區挖掘、搜集、整理出的土司實物資料相比,忻城莫土司衙署的原始實物資料比較完整。豐富完整的實物資料對研究忻城乃至我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土司的機構設置、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3)土司歷史文化遺跡。莫土司衙署與翠屏山混為一體,山上林木蒼翠、怪石林立、植被豐富,如一天然屏障環護著土司衙署,在明清時期就被列為廣西慶遠府名山。在翠屏山的右山腳下,有由五座珍木構架的建筑物組成的三界廟,山側精心修建了“龍隱洞”和“三清觀”;毗鄰的麒麟山上有1 000多年歷史,號稱“忻城小布達拉宮”香客如云的“通天寺”。此外,還有建于明萬歷年間思練鎮牌坊村的雙拱石橋、建于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古蓬鎮滂江河上的永吉橋、周安街的八寨農民起義古戰場、北更鄉的壯族干欄式民居、城關鎮內城的莫曼壯錦源等,都極富壯鄉情調。
2.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
忻城莫氏土司文化主要包括民歌文化、節慶習俗、傳統工藝等三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
(1)忻城民歌文化。自古以來,壯族就有唱歌的習俗,唱歌已經成為壯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壯族文化也得以通過歌聲傳承下來。唐以來,忻城的壯族人民就開始借助民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記載自己的生活和抗爭經歷。忻城文化工作者先后編撰出版了《廣西忻城民歌選》和《忻城壯族古代山歌》,這些山歌文化作品是展現當地社會生產生活形態的有力載體。
(2)忻城節慶習俗。節慶習俗是反映民眾對生產生活的追求和審美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忻城的歲時節日非常隆重和有特色,以農歷九月初九為例,《忻城縣志》中對“九月九”重陽節的描述是這樣的:“舊時,農村在此日舉行祭祀,祈求‘村主’保佑全村老少安康,萬事遂意。并在當日閹牛,撿墳。50至70年代(注:20世紀,以下同),祭‘村主’的陋習已革除,但家家戶戶以新豆腐圓,慶祝大豆豐收。80年代起,農村個別村屯復立‘村主’,行香供奉。登高賞菊之俗如故,并定這個節日為‘敬老節’。”這一天的白天,街上商鋪店面多關門歇業,人們回家過重陽;翠屏山、森林公園則游人眾多,人們或賞菊飲酒,或登高賦詩。重陽節在忻城成為全家團聚、上香拜祖的文化符號和標簽。
(3)忻城傳統生產工藝。忻城特產眾多,如壯錦、紅糖、蠶絲被、乳鴿酒、金銀花等,都遵循傳統工藝,制造精良。以壯錦為例,它和云錦、蜀錦、宋錦被譽為中國四大名錦。據《慶遠府志》記載:“壯女作土錦以棉為經,以五色絨為緯,縱橫繡錯,華美而堅。維忻城、永定花樣更佳,做工更巧。”被譽為“學有專著、詩成專集第一人”的清代忻城舉人莫震,在《忻城竹枝詞二首·七月》中描寫了忻城織錦的盛況:“十月山城燈火明,家家織錦到三更,臨雞乍唱停梭后,又聽砧聲雜臼聲。”精美的壯錦不僅是忻城兒女必備的嫁妝,也是各朝各代指定的貢品,基于這些因素,官方非常注重壯錦生產,壯錦因此成為忻城的支柱產業。現在,忻城壯錦品種主要有背帶、被面、抱褸面等,每逢節日或婚宴,當地居民就會把它送給親朋好友或者愛人,壯錦成為傳遞情感的珍貴禮物。
二、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遺產的旅游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莫氏土司歷經近500年,其留下的豐富歷史文化遺產,對研究地方旅游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體驗中感受鄉村治理的內在機理
鄉村治理是穩定國家基層政權的重要基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封建王朝為了實現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因俗而治,齊政修教,采取“以夷制夷”“以蠻治蠻”的政策。土官除負擔中央王朝規定的貢賦和征調外,其他事務自行決斷。封建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土司制度為何得以延續近500年,值得研究和思考。
(二)在旅游市場中助推鄉村振興產業發展
莫氏土司在探索“走出去”和“引進來”方面做了許多積極有效的探索。如組織民眾修筑橋梁、開辟道路、使縣境內各里堡之間道路通達,推動了忻城的壯錦、棉紗、紅糖、百合粉等往外銷售,并引進了外地的鋤頭、鐮刀、絲絨等生產生活日用品。在國內國際雙循環時代背景下,汲取土司文化有益的經濟養分,暢通產業鏈、供應鏈,有利于推動區域市場的調節合作,促進縣區經濟發展。
(三)在旅游文化中引導鄉村教育健康發展
莫氏土司任職早期,征調繁多,因此精通文墨的人較少。第五任土官莫廷臣上任后,認為“操弓挾矢,絕少文字”不利于地方治理。于是在明嘉靖初年,在縣城首辦官塾,延請名士,教授子侄。之后的歷任土官,大都愛好詩文,重視教育,特別是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國曾于康熙五十三年襲職后,捐建義學三間,“聚官族子弟、選堡目和土民中較聰穎之少年入學,聘名士以教”,并著有《教士條規》十六則懸于署外,以期感化。從此,文教之風漸起,鄙陋之弊漸除。土官對教育的重視,為忻城培養了不少人才。土司教育文化作為土司文化體系中的寶貴遺產,蘊含豐富的內涵。在當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之際,合理利用土司教育文化資源開發鄉土教育功能,意義重大。
三、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遺產發展存在的問題
從忻城縣對土司文化助推旅游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主要存在文化品牌塑造不力、文化內涵挖掘不足和文化保護傳承力度不夠等問題。
(一)文化品牌塑造不力,品牌效應有待提升
廣西本土旅游文化資源豐富,既有桂林山水、德天瀑布、北海銀灘等一批全國知名的旅游資源,也有三江、金秀、融水等獨具廣西民族特色的民俗旅游勝地。相比之下,忻城對文化旅游的開發相對較晚,其知名度不夠高,對外宣傳力度不夠大,表現在對土司文化的宣傳內容、宣傳載體、宣傳方式以及宣傳途徑嚴重滯后,游客對土司文化的認知和了解還比較淺顯,需要一定時間以培育當地旅游品牌,著力提升旅游品牌效應。
(二)文化內涵挖掘不足,文創產品有待創新
忻城的特產主要是蠶絲被、金銀花、珍珠糯玉米、紅糖和百合粉等,但都只是依托自然資源進行簡單加工,和莫氏土司文化相關的產品開發較少。如在莫土司衙署的旅游產品開發方面僅能提供土司文化書籍、蠟染民族服飾、包包、鑰匙扣、竹筒等。這些旅游產品既無文化內涵,又缺設計創意,更沒有收藏價值。與其他景區相比,更顯得莫氏土司文化旅游開發深度不夠,可體驗和參與的產品有限,滿足不了游客的深度體驗需求,還處在表面的觀光旅游狀態,無法吸引游客留下來進行深度體驗和消費。
(三)保護力度不夠,代際傳承有待加強
2018年1月1日《來賓市忻城土司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的頒布實施,為保護土司文化遺產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但該條例頒布實施的政策力度較小,加上當地對土司文化遺產的內涵挖掘不夠深,宣傳力度不夠大,以致保護效果不明顯。很多當地居民只知道土司衙署的建筑好看,卻并不知道其文化內涵和歷史源流。再加上土司衙署經過一次次的翻新與復古,缺乏歷史滄桑感;許多老一輩的民俗文化繼承人相繼離世,在世的多為高齡人群,極少有年輕人愿意加入民俗文化傳承的隊伍,以致土錦、山歌、戲劇等民俗文化面臨傳承中斷的危機。
四、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創新路徑
(一)加強政府主導,拓展宣傳渠道
隨著旅游消費需求的增加,如何有效切分、細化旅游業市場尤為關鍵。首先,要加大土司文化旅游宣傳的力度。近年來,忻城縣打造包裝“三節一會”(土司文化旅游節、金銀花節、桑蠶節暨招商引資洽談會),籌辦召開高層次的土司文化研討會,進一步搭建土司文化宣傳推介平臺,特別是善于借助《劉三姐》《石達開》《一代廉吏于成龍》等多部名影視劇在莫土司衙署拍攝的機會,提高忻城莫土司衙署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其次,建立研學實踐教育基地。隨著旅游業業態的不斷豐富,研學旅行已成為旅游行業新的風向標。研學旅行成為培養中小學生愛國情懷、增長中小學生社會閱歷、提高中小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有效途徑。為此,要聚焦研學實踐教育基地的需求導向,精準承接莫土司衙署的功能供給,構建課堂教學和校外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進一步推動學校教育和學術研究的互動,豐富教學內容、優化教育體系、深化教育改革。同時能夠切實帶動莫土司衙署的人流量,刺激消費帶動忻城縣域經濟發展。最后,注重發揮互聯網和大數據等媒介的作用。信息化時代,忻城縣要充分借助互聯網、新媒體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如借助微信、抖音、“網紅”效應等,努力擴大忻城土司文化的知名度。
(二)深挖文化內涵,開發文創產品
忻城縣擁有獨特的土司文化旅游優勢,但由于沒有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導致其知名度和影響力無法和國內其他知名景區相提并論。因此,要立足于莫氏土司文化和其他景區土司文化的差別,探索、挖掘獨具莫氏土司文化特色的旅游優勢。一是圍繞旅游項目強化游客深度體驗。抓住土司文化的內涵與外延,注重從頂層設計土司文化的旅游場景,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旅游深度體驗項目。首先,精心研究和發展土司審案等項目,讓游客參與到土司治理體驗活動中,思考土司文化在治理地方時的作用;其次,精心設計土司家宴和大型實景演出,還原當時的土司生活,讓游客有身臨其境之感,激發游客繼續探究土司文化的興趣;最后,深入挖掘與莫氏土司文化內涵相匹配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莫氏土司后代,引發游客對莫氏土司歷史功過的內在思考。二是圍繞文創產品強化旅游附加值。隨著旅游業的轉型升級,旅游消費者更加注重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并向集實用、藝術、情感于一體的方向轉變。忻城縣擁有獨特的土司文化遺產,相關部門可以建立完善的文創產品開發機制,深挖土司文化內涵,選取典型文化符號進行整合提取,精心打造出一批外觀與內涵有機結合,具有典型莫氏土司風情、有文化意義、有紀念價值的文創產品。比如:采用當地獨有的織錦工藝,將具有典型莫氏土司風情的圖案繡在圍巾、手提袋、扇子等產品上,實現產品使用功能、品位度和附加值的疊加聚集;或以忻城莫土司衙署為原型,經過比例縮放形成具有收藏價值的仿真紀念品。如此不僅能夠迎合游客的消費心理,受到游客的歡迎,而且能夠加深游客對忻城土司文化的認識和了解。
(三)完善制度法規,強化支撐要素保障
一個地方的特色文化是地緣文化的根本,也是地方民俗旅游經濟發展的源頭。對此,要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土司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法規,健全相關的獎懲機制,有效激發當地群眾參與土司文化遺產保護的熱情,避免土司文化遺產遭到破壞與流失。還要建立長效資金投入機制,增加資金投入,在財政投入中設置專項管理和獎勵資金,積極引導當地群眾參與土司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保護工作中,要進一步修整和保護土司建筑群,加大搶救和保護土司文化遺產的力度,構建傳承人命名與保障體系。此外,還要借助新媒體拓展工作機制。充分挖掘土司文化遺產的歷史內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模擬展示莫氏土司變遷歷程,全方位介紹土司文化遺產,增強當地群眾對優秀土司文化遺產的認同感。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忻城莫氏土司在近500年的歷史長河中,在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文化發展等方面發揮過積極作用。近幾年來,忻城縣委縣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在保護和開發土司文化資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借助全國各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春風,不斷整合土司文化優勢資源,切實提升了莫土司衙署的知名度,帶動了地方旅游產業發展、助推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相信在各方人士的繼續努力下,忻城縣將進一步保護和利用好土司文化資源,不斷適應新時代的市場需求和游客需要,實現文化遺產的有序傳承與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覃錄輝.廣西忻城土司文化對地方發展旅游經濟的意義[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9(4).
[2]忻城縣志編纂委員會.忻城縣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3]黃維安.忻城土司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
[4]彭丹.貴州海龍屯土司遺址文化旅游品質提升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20(6).
[5]龍曉添.土司文化遺產與當代日常生活:以廣西忻城為例[J].地域文化研究,2016(2).
注:本文系2021年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旅游資源開發下的廣西忻城土司文化價值研究”(2021KY0914)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陳嵐嵐(1985— ),廣西忻城人,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馬金娟(1987— ),廣西隆安人,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
(責編 蔣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