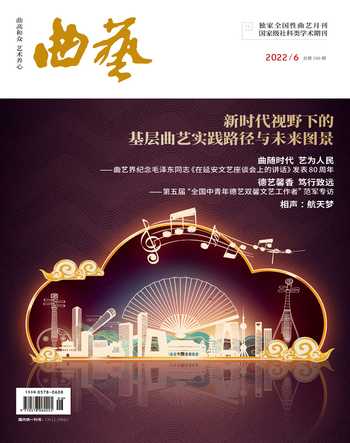“曲藝”命名隨想
姜昆
且越來越迷。他查了一下,古代的說
文解字中,對于這個“曲”字兒的解釋是這樣的: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
用白話解釋就是:像器具凹曲以承載物品的形狀。有人解釋作:養蠶薄。
養蠶薄是養蠶用的平底竹編器具(估計是取形容把竹篦子彎曲編織之意)。這是古代人以“曲折”的“曲”字的釋義。
后又有人逐漸又把“曲”的多種用意加以解釋:古代的“曲”字就像是彎曲的東西,像一塊有拐角的田,后來變得又像是被揉彎的一截竹子,再后來變成了“∪”形,像馬蹄鐵。
這個字還有一個讀音,念qǔ(3聲),是樂曲的意思。歌曲和樂曲的節奏多變,聲音高低起伏,所以曲折的曲后來有了樂曲的意思,也是一種韻文形式,如元代的元曲。
他問我,按照這說法,不是直白,是有藝術性、曲折的娓娓道來的一種韻文形式的藝術,如果是這樣的話,“曲藝”兩個字概括在中華民族口頭說唱藝術種類上,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他問我,是不是這么來的。
這個問題還真把我問住了,我一下子,想起了許多。
在中國諸多的藝術種類名稱中,“曲藝”這兩個字兒應該是最有特點的。
它不像音樂、舞蹈、戲曲、戲劇、雜技這么鮮明,可以讓人望文生義,一看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樣的藝術門類。
“曲藝”,得需要那些“研究藝術理論”的人,用非常規范的專業術語,全面準確好好地闡釋一下。
標準的專業權威說法,應該是:曲藝,是中國說唱藝術的總稱。
如果,要進一步具體展開來說,那就是:曲藝,就是一種用“連說帶唱的形式”,既有一定之規,又可以根據現場效果隨時即興發揮,更能依據舞臺下的觀眾反響,產生積極的良性互動。演出時長和情緒節奏均可微調,極其生動靈活,充分體現創作智慧,在對觀眾審美心理的把握和挑戰中,甚至能享受到那種完全不可預知的意外樂趣,是一種“集知識廣博、技能嫻熟、應變能力于一身”的,臺上臺下有互動、有共鳴,有拘無束的說書講故事。
可以這么說,中國曲藝是由民間口頭文學,與極具地域方言特色的民間歌唱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這兩者,在長期發展中不斷相互磨合、相互適應、相互照顧,在追求“相互烘托、盡善盡美”的演繹和升華進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非常獨特的“連說帶唱、兼顧肢體造型,節奏韻律、相得益彰”,“老少婦孺皆能懂,鴻儒白丁都喜歡”,極富感染力、深受社會大眾擁戴的,既普惠又走心的藝術形式。
曲藝,在電視化以后,漸漸忽略了最有生命力的舞臺互動,光靠小編在剪輯、配動漫方面下功夫,人為地配一些劇場效果。由于對曲藝客觀規律的掌握上功力不夠,往往導致千篇一律、隔靴搔癢,甚至是本末倒置,導致神采全無。豐滿的劇場效果,被干癟的、生編硬套的、“苦惱人的笑”給活生生地扼殺了,真是: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在百度上查,你會看到這樣的文字:富有地方色彩的各種說唱藝術,如彈詞、大鼓、相聲、評話、琴書、道情、快板等。
說得比較直截了當,但是不像理論家們概括得那么規范。就那一個“等”字,你知道它包括多少種類的曲藝形式嗎?
有的說400多種,有的說300多種。
按中國的曲藝志上進行的統計,中國曲藝幾乎數不勝數。
“曲藝志”,又是分省(自治區、直轄市)立卷編纂,完成時間先后不一(全國曲藝志從1986-2011共花25年時間才陸續編纂出版)。
所以,無法完全統計并判定確切的數字。一種統計和估算認為:已知中華各民族古今(有些古代曲種已消亡,而新曲種又陸續形成)擁有的曲藝品種,“連死帶活”,約為1000種,這也是一種說法。
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老編輯陳連升回憶:“恩師王決20世紀60年代中期統計有260多個曲種。我1976年6月在文化部舉辦曲藝調演期間統計了一下是348個曲種。”
還有一種說法,現在存活的曲種,至少在500個以上。其中,已知浙江省最多,有97個;云南、新疆次之,各有八九十個;西藏較少,有10個……幅員遼闊的華夏大地,“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天然稟賦,造就了中國曲藝和戲劇在世界上的王者風范。
博大精深、傳承有序的中華文明體系,必然會有千姿百態的文化多樣性。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沒辦法:存在,決定意識!如果不是這樣,反而不正常了……
為這么多種類的說唱藝術統一起個“凝練精當無比”的名字,區區“曲藝”二字,便可“一覽眾山小、天下美景盡收眼底”,全包括進來,多不容易!
我們的前輩,定下“曲藝”這個名稱的人們,真了不起,值得后人發自內心地頂禮膜拜!
我們的曲藝理論家戴宏森先生有一篇專著,《試談“曲藝”的定名》(《戴宏森說唱藝術論集》,中國民間文藝出版1989年),我當曲藝研究所所長期間,主編的《中國曲藝概論》,戴宏森先生對于“曲藝”一詞產生、由來、定義都有詳細描述。(《中國曲藝概論》,第一編第10-11頁)。
曲藝專家常祥霖先生告訴我,中國曲藝家協會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專門召開了一個名為“曲藝的定名與曲藝本質特征”的研討會。當時健在的曲藝理論家和相關領導出席了會議。會議主要組織者是當時的中國曲協研究部、羅揚、沈彭年、戴宏森、盧昌五、郭鴻玉等諸位,天津的薛寶琨、倪鐘之、劉梓玉,山東張軍,遼寧耿英,河南張凌怡,河北鐘聲,湖北賀鐵肩、蔣敬生等很多人出席,這是中國曲藝家協會非常重要且有影響的一次會議。
戴宏森先生的《曲藝的定名》一文也是那次會議的發言稿。
記得,我和戴宏森先生在編纂和研討《中國曲藝概論》稿件時,戴宏森先生除去講了他的研究成果,還講了1949年7月22日中華全國曲藝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之前,周恩來總理帶著趙樹理、羅常培、老舍等文藝名家討論定名時,一致認為將中華民族說唱藝術的總稱定名為“曲藝”是合適和恰當的。除了這個以外,他還給我講了曲藝與雜技、雜耍互相涵蓋的分分合合的歷史。
他還曾經跟我講過,現在有一種說法“曲藝藝術怎樣怎樣”,這是一個病句。曲藝,就是曲藝藝術的準確稱法,沒有必要再重復出現,可見前輩們非常認可和尊重這個名稱的內涵。
當然,曲藝學者鮑震培教授認為,曲藝是典型的“古詞今用”,是“雜耍”的雅稱,包括了所有以口語說唱敘事的曲種,不是唱曲+藝術,所以加藝術是沒有問題的。
有時候,曾經想過,和雜耍分家,太有必要。尤其是一個“耍”字,實乃“罪魁禍首”是也!“耍”的評價體系的內心認證處,已經把曲藝打入藝術的“另冊”、視為“下九流”的“地攤文化”。從根本上,嚴重忽略了新中國在對5000年文化進行“根本性改造”之后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換了人間……
人,還是那些人。事,卻不是那些事了。
舊社會的“雜耍”命名是被動的,而新社會的“曲藝”才是人民的選擇。而如今將“曲藝”等同于“雜耍”,甚至要讓“雜耍”取代“曲藝”,這其中是否包含了“自甘墮落”,是否給“原本就該如此”的人士提供了“理論上”的托詞,成了一大塊“既讓人心安理得、又讓人十分體面”的、彼此心照不宣、自欺欺人的遮羞布……
不能玩,不能玩。
真的,就是不能這樣玩……
應該下力氣,從理論上說清楚道明白:
曲藝就是曲藝,曲藝不是雜耍。
雜耍就是雜耍,雜耍永遠不是曲藝……
扯得有點遠。
鮑震培教授也有關于“曲藝”一詞的歷史由來的專著,她的論文里探討了1900年以來,曲藝定名的3種路徑:一是技術路徑,曲藝為雜技;二是歌唱路徑,戲曲、昆曲、京劇甚至歌舞劇曾被稱為曲藝;三是和今天的曲藝大致相同,指代說唱藝術、曲藝家、曲藝場、曲藝界、曲藝比賽、曲藝社等用于機構名稱,如北平曲藝公會、電臺曲藝節目等。
從雜耍和曲藝的關系來看,它和雜耍都是總稱,而雜耍主要是當時北方曲藝的總稱,“曲藝”一詞較“雜耍”莊重,所以全國性總稱非“曲藝”莫屬了。
前兩天,評書后起之秀王玥波給我發來一個文物的照片,是1946年北京成立北平曲藝公會成立的會員名冊,曹寶祿先生是會長。那時候,“曲藝”一詞,已經派上用場了。
緊接著天津的孫福海先生發來了1942年北京鼓曲長春職業公會會員證書的文物照片,嘿,又早了幾年。
文字、文物的探討、佐證,反映了曲藝人對自己行業的熱忱,也反映了曲藝藝術工作者認真嚴肅的藝術態度。
而一些自媒體上討論“曲藝”相關文字的時候,似乎未能做到嚴謹準確,甚至影響了一些主流媒體,不同程度地造成歷史虛無、以訛傳訛。
在某主流媒體的戲曲專場賽事中,地方曲藝登臺表演,居然沒有一個評委講出曲藝和戲曲兩個不同門類的區別。
就像演員拿著竹板,在演唱根本沒有韻腳,不合轍押韻的一段詞一樣,聽得渾身上下不舒服,您要說您是“RAP”也還差強人意,您千萬別說唱的是快板。否則,就成了張震岳的“RAP”愣說是李潤杰創作的快板書——“張冠李戴”了。
希望曲藝從業者和愛好者以及媒體朋友攜起手來,讓曲藝根深葉茂、錦簇花紅。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