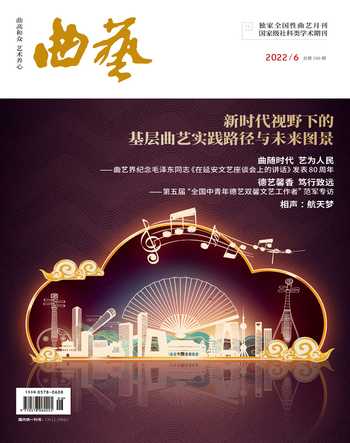成功收臺灣
王封臣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因為是塊寶地,所以每當國力衰弱時,往往會被外國勢力竊取,被迫脫離母親的懷抱。這不,明朝末年,朝廷腐敗,軍備廢弛,又給了外國勢力可乘之機,荷蘭殖民者霸占了臺灣島,對臺灣實行了殘酷的殖民統治。他們強征重稅、大肆搜刮、劫商掠貨、奴役華人,可謂無惡不作,無所不為!臺灣和福建沿海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恨透了侵略者,都罵他們是“紅毛番”。臺灣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反抗,但都遭到了荷蘭殖民者的血腥鎮壓。面對殖民者的暴行,臺灣人民無比仇恨,“天哪,天哪!咱們中國的軍隊什么時候能來趕走‘紅毛番’啊!”
中國軍隊來了!
1661年,一支船隊浩浩蕩蕩從金門料羅灣出發,乘風破浪,橫渡臺灣海峽,直取臺灣!沖在最前面的是一艘虎頭戰船,船頭之上站定一人。只見此人:
細腰乍背,雙肩抱攏,方面大耳,準頭端正,四方海口,虎目如燈,三縷須髯,飄灑前胸。
頭戴金盔,簪纓朱紅;龍鱗寶甲,密布緊釘;腰中懸劍,可斬蛟龍;戰袍半掛,大紅披風;傲然屹立,氣勢恢弘!
好威武的一員大將!
他是誰?正是當時被兩岸百姓稱之為國姓爺的鄭成功!怎么叫國姓爺?因為鄭成功文武雙全,長得還帥,深得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鍵的喜愛。隆武皇帝感慨自己沒有女兒,不能讓鄭成功做自己的女婿,所以就賜他明朝國姓,這就是鄭成功“國姓爺”的由來。
“姓為國姓,自然要許身國家社稷。‘紅毛番’竊據臺灣已有30多年,是割我中華血肉!父老兄弟飽受欺凌,我豈能袖手旁觀!傳我命令,點齊人馬,舟船并進,打敗‘紅毛’,收復臺灣!”
“啊?”有些將領一聽,有些害怕,都吐舌頭了,“什么?要打‘紅毛’?哎呀,國姓爺啊,使不得,聽說‘紅毛番’他們有紅夷大炮,神仙難逃一溜煙兒啊!”
鄭成功一笑,“沒什么好怕的,別忘了,正義在我們這一方。更別忘了,我名叫成功,就一定能成功!把我的戰船排在最前頭,你們跟著我向前進!”
眾將士一看,“主帥這樣的勇往直前,我們還怕什么?跟著主帥沖!”“唰——”25000人,幾百艘大小船只一齊前行。
開始幾天順順利利,但臨近臺灣島時,天氣突然巨變,雷雨交加,風大浪高,“嘩——嘩——”,船只被打得上下起伏,幾乎都要翻了。
眾將嚇壞了,“國姓爺,別走了!現在風雨交加,很難前進啊!”
鄭成功一擺手,不為所動,“收復臺灣,是本次出征的目的,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點風雨焉能動搖我志!”
鄭成功這份自信,除了是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還建立在他對臺灣水文條件的了解上。中國軍隊要走鹿耳門航道登陸臺灣,雖然出其不意,但著實是步險棋。航道水淺,如果不能乘著漲潮通過,中國軍隊就很容易陷入進退維谷的險境。現在風雨大作,正是漲潮的先兆,也是一舉通過鹿耳門的大好時機。此時此刻,如何能輕易退兵!
傲立船頭的鄭成功遠望海天,命令部下,“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鳴炮三聲,繼續前行!”
“咚!嗒——嗒——嗒——”三聲炮響,金鼓震天,“咚咚咚……”中國艦隊破浪前行,與此同時,鹿耳門潮水大漲,把中國艦隊送到了臺灣島沿岸。
說來也神奇,中國軍隊通過后不久,風雨平息,云開日出。“哎呀,這真是老天有眼,是老天爺在幫我們啊!”“是啊,收復臺灣有望了……”士兵們一個個歡欣雀躍。
荷蘭侵略者早就聽說鄭成功打來了,嚇壞了,趕緊把軍隊集中在臺灣和赤嵌兩座城堡中,架起大炮,嚴陣以待,又在港口沉了好多破船,干嗎?想阻擋鄭成功的船隊登岸。
可萬沒想到,鄭成功沒去硬碰硬,而是利用海水漲潮的時機,巧渡鹿耳門,兵臨臺灣島。
臺灣百姓聽說鄭成功來了,高興壞了!成群結隊推著糧食,提水端茶,迎接親人。其中的4位百姓,手里各自端著一個盤子,里面分別放著金、銀、野草和泥土。
“國姓爺,感謝您能遠涉江海拯救臺灣。我們是高山族的,代表我們族人感謝您的大恩大德!”
鄭成功看了看盤子里的物品,微微一笑,“高山族也是我中華民族的一支。我到臺灣來就是為了驅逐‘外夷’、收復國土、拯救百姓的,而不是為了金銀。臺灣的野草和泥土,我收下了!但金銀,請你們還帶回去,還給同胞!”
鄭成功的這個舉動感動了高山族同胞,“請國姓爺放心,我們高山族族人也是響當當的中國人!都聽您的號令,驅逐‘紅毛’,收復我們中國人的土地!”
正是在臺灣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鄭成功一次又一次地打敗了荷蘭侵略者。最后,荷蘭侵略者被打得滿頭是包,龜縮在兩座城里不敢露頭了,趕緊派出使者向鄭成功求和。
“鄭將軍,只要您能夠帶兵退出臺灣,我們愿獻上白銀十萬兩!”
“哼!”鄭成功冷笑數聲,威嚴地說,“臺灣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我們收回這里,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我勸爾等趕緊投降,以免葬身臺海!”
荷蘭侵略者一看,“中國人真惹不起,想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實乃癡心妄想,現在不可能,以后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他們最后還是舉白旗投降,灰溜溜地滾出了臺灣!
這正是:
民族英雄鄭成功,
抗擊侵略動刀兵。
只為華夏金甌統,
收復臺灣留美名!
賞析:
同一個主題應根據預設受眾群體的不同而增刪繁簡,在具有基本藝術規律的基礎上呈現為不同的作品,以契合不同群體的心理需要和接受能力。而本作正是作者為其臺灣學生量身創作的,并曾在北京少兒曲藝大賽中獲獎。
少年兒童對藝術作品的情趣傾向比較強,相對缺乏深度欣賞的能力。而我國美學家李澤厚先生認為,“主觀感情必須客觀化,必須與特定的想像、理解相結合統一,才能構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藝術作品,產生相應的感染效果。”這是一種對集體記憶的美學層面闡釋。少兒的感情是純真、濃烈的,對家庭的依戀、對朋友的渴求、對師長的敬愛、對英雄純粹的崇拜等,都是他們情趣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類型作品的重要創作依據。從內容來說,本作的遣詞造句有著豐沛的感情,而如“臺灣的野草和泥土,我收下了!但金銀,請你們還帶回去,還給同胞!”等說理也是明快易懂,符合少兒的情趣需要。從結構上來說,本作的扣子分布較為密集,且拴解扣子的手法比較干脆,在觀感上營造出了一種跌宕起伏的效果,相當程度上加強了作品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更重要的是,這個作品主題,實際上是一個集體記憶層面的“最大公約數”——所有的中國人都將鄭成功奉為中華民族的英雄,而瑞典心理學家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始終在發出召喚,誰能發出它的聲音,誰的聲音就將被無數倍地放大,并得到千萬人的響應。”鄭成功就是一個生發于中華民族集體意識深處的形象,他的故事就能很容易地得到廣泛響應。這一點對臺灣同胞,特別是對臺灣地區少年兒童來說,是尤為重要的。
個人認為,一個作品應該考慮到其成長性,以契合人成長階段的不同接受能力,這既是對文本的合理挖掘與不斷利用,也是對一個題材的收束規整。這有助于相關受眾階段性統一意識。
(賞析:本刊編輯部)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