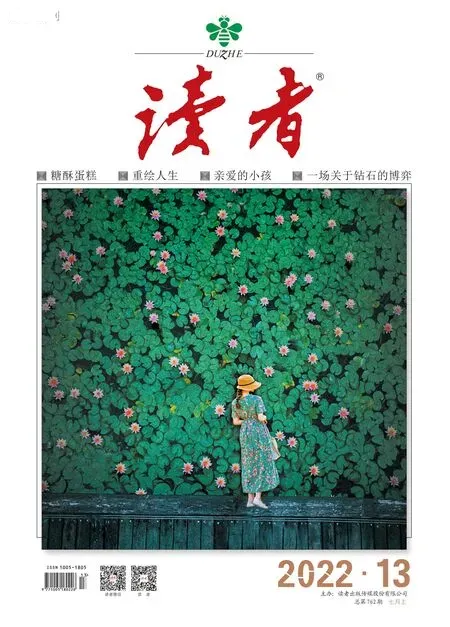書之痕
☉桂 濤
什么樣的書最迷人?是纖塵不染、滿紙墨香的新書,還是歲月留痕、滿是批注勾畫的老書?這雖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卻是藏書人的必答題。
我認識的許多藏書人只藏新書,對書的品相要求甚高。他們視“在書上寫字”為大忌,認為簇新狀態的一版一印的書才最值得收藏、最有價值。
但我認為,那太無趣了,那樣“干凈”的書少了煙火氣,缺了情感,沒了生機。
有奇書讀本已勝過觀花,更何況書上的留痕又能讓人分享前人的閱讀感受,引發二次思考。與百年前的讀書人在燈下同捧此書,心照神交,妙不可言。
我的書架上常年放著兩本清代木印本《聊齋志異》。雖是不成套的散冊,也非名貴版本,但我總愛拿出來翻翻。不是因為書本身,而是因為書上留有前人的墨筆批點。
留痕的先賢不見姓名,只留下滿頁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批注的內容很精彩,有感于書里的人鬼之情、人狐之戀,或擊節叫好,或扼腕嘆息,將內心真實的閱讀感受和盤托出。
比如,《庚娘》寫機智敏銳、膽識過人的庚娘為報家仇灌醉敵人、從容殺之的故事。讀至庚娘勸酒處,批注為:“有識有膽,有心有手。讀至此,忽為之喜,忽為之驚,忽為之奮,忽為之懼,忽而愿其必能成功而助之,忽而料其未能成功而欲阻之……”

讀到庚娘手刃仇敵時,批注寫道:“及觀暗中以手索項,則為之寒噤。怕往下看,又急欲往下看。看至‘切之,不死’數句,強者拍案呼快,弱者頸縮而不能伸,舌伸而不能縮,只有稱奇稱難而已……及行之者從容顧盼,談笑自如,是唯不作兒女態者,乃能行丈夫事。豈但不敢雌之,直當圣之神之,恭敬禮拜而供養之,而禱祀之……”
這就是書之痕帶來的樂趣。曾經的擁有者通過留痕——不管是留下批注、簽名、藏書票、藏書印,還是隨手涂鴉、隨筆勾畫——與這本書產生了某種聯系,生發了某種情感。這種情感又被永久地封存在書中,流傳下去,成為這本書作為文字載體之外的另一種價值。
在我的藏書中,就有裝幀精美的祈禱書,扉頁上寫著爺爺對剛出生孫女的祝福,并解釋他送給還在睡夢中的孫女這本書的原因;還有一本晚清詩集,不知名的狂生興之所至,在書頁上寫下“一拳打倒東坡老(蘇軾),一腳踢翻方望溪(方苞)”。
即使在書上留下痕跡的不是名人,這本書也會因歷史留痕變得比一本新書更加有趣,變得獨一無二、與眾不同。
我曾和英國著名的書籍史學家、擔任過英國國立藝術圖書館收藏部主任的大衛·皮爾森聊書,他也認為有之前藏家留痕的書更有趣。
我在皮爾森的藏品中,就發現了百年前戲劇彩排時使用的戲劇腳本,上面有各種記號,標明需要修改或刪節的地方,表演者在舞臺上的位置以及導演的要求。書之痕的價值正在不斷被發現。1997年,英國歷史學家羅斯的藏書被出售時,被提及的賣點之一就是,羅斯“評論及批注的習慣隨著年齡和智慧的增長而增長,他的藏書空白處也布滿了他的評論,智慧、譏誚,有時不乏嚴厲”。
(楚 山摘自《環球》2022年第8期,宋曉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