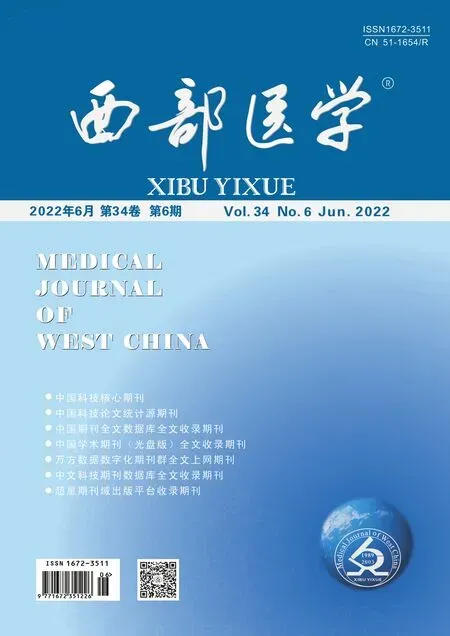腦梗死患者血清miR-181c、miR-21水平與頸動脈狹窄及其不良預后的相關性預測*
馮程程 朱瑞霞 何志義
(1. 遼陽市中心醫院神經內科,遼寧 遼陽 111000;2.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遼寧 沈陽 110000)
腦梗死是臨床較為常見的腦部局部血流供應缺失的重要疾病之一[1],隨著疾病的進展,患者的腦部組織出現缺血缺氧性壞死,進而造成神經功能的損失[2]。頸動脈是腦組織的重要供血血管之一,同時頸動脈狹窄也是造成臨床腦卒中或腦梗死的重要原因。頸動脈的狹窄可通過對其有效的治療,進一步降低腦缺血患者的發生率。微小核苷酸可通過對轉錄或者降解微小核苷酸的降解靶基因的顯著抑制性作用[3],另外,微小核苷酸可通過對血管形成以及氧化應激反應水平的顯著刺激性作用,進而調節缺血性腦卒中的疾病進展[4]。有研究[5-6]報道顯示,miR-181c、miR-21水平是影響頸動脈粥樣硬化穩定性的重要基因,其可通過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受體的顯著性抑制作用,調節缺血性腦卒中的疾病預后。本研究探討腦梗死患者血清miR-181c、miR-21水平與頸動脈狹窄的關系及對預后不良的預測分析,為臨床治療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2015年1月~2019年6月在遼陽市中心醫院診斷的腦梗死患者120例作為研究對象,行前瞻性研究。納入患者中男59例,女61例,年齡53~66歲,平均(60.22±2.09)歲,體重指數平均(24.26±1.69)kg/m2,糖尿病患者44例,高血壓患者71例,高脂血癥患者55例。通過對患者的頸動脈檢查,依據北美癥狀性頸動脈內膜切除實驗法[7],對患者的頸動脈的狹窄情況進行評價,頸動脈狹窄患者58例(輕度狹窄患者24例,中度狹窄患者22例,重度狹窄患者12例)設為頸動脈狹窄組,非頸動脈狹窄患者62例設為非頸動脈狹窄組。本研究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論證通過。納入標準:①所有患者均符合腦梗死診斷標準[8]。②均經頭顱CT或MRI診斷為腦梗死。③所有頸動脈狹窄患者均符合北美癥狀性頸動脈內膜切除實驗法標準[7]。排除標準:①合并嚴重精神疾病患者。②無法配合本研究檢查患者。③出血型腦血管病、顱內動脈瘤、腦動靜脈畸形。
1.2 研究方法 對所有患者均開展頸動脈超聲檢查,行仰臥位,充分暴露頸部,頭偏向被檢查部位的對側,在安靜狀態下,對頸總動脈(CCA)、頸內動脈(ICA)以及椎動脈(VA)、頸動脈內的中膜厚度、斑塊的形態、大小、邊緣情況、回聲情況進行檢測,依據北美癥狀性頸動脈內膜切除實驗法標準對患者的頸動脈狹窄情況進行比較。已經動脈膨大部位遠處的管腔內徑作為基礎值(A),以頸動脈內部最狹窄的寬度作為測量值(B),狹窄度=1-(B/A)%,狹窄度在30%以下則為輕度狹窄,狹窄度在30%~69%則為中度狹窄,狹窄度在70%以上則為重度狹窄[7]。所有患者在入組研究后,均進行靜脈采血4ml,以Trizol進行總RNA提取,以PCR方法進行擴增,miR-181c上游引物設定為5′-TACATCTGGCTACTGGGTGTCGTATC-3′,下游引物設定為:5′-TCGCAGGGTCCGAGGTATTC-3′,miR-21上游引物設定為5′-GTCGTATCCAGTGCAGGGTCCGAGGTATTCGC ACTGGATACGACCGACCATG-3′,下游引物設定為:5′-CAGTGCAGGGTCCGAGG-3′,以U6作為內參基因,使用2-△△CT計算miR-181c、miR-21水平的相對表達量。反應條件設定為95℃下5 min,95℃下40 s,60℃下20 s,72℃下15 s;共計完成42個循環。
1.3 觀察指標
1.3.1 頸動脈狹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分別對頸動脈狹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及慢性病情況進行比較。
1.3.2 不同頸動脈狹窄嚴重程度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分別對輕度頸動脈狹窄、中度頸動脈狹窄、重度頸動脈狹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以及慢性病情況進行比較。
1.3.3 頸動脈狹窄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患者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1.3.4 不同頸動脈狹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分別對輕度頸動脈狹窄、中度頸動脈狹窄、重度頸動脈狹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1.3.5 不同預后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分別對所有研究對象入院后進行Rankin量表評分比較。Rankin評分在2分及以下患者為預后良好組(76例),Rankin評分在2分以上為預后不良組(44例)。比較兩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差異。
1.3.6 預后不良組與預后良好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分別對預后不良組與預后良好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 Stroke Scale,NIHSS )以及慢性病情況進行比較。
1.3.7 預后不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s多因素分析,對造成患者不良預后的多因素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頸動脈狹窄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及體重指數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頸動脈狹窄組患者的糖尿病、高血壓及高脂血癥患者的比例顯著高于非頸動脈狹窄組(P<0.05),見表1。

表1 頸動脈狹窄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and non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2.2 不同頸動脈狹窄嚴重程度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不同頸動脈狹窄程度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高血壓及高脂血癥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患者的頸動脈狹窄情況的加重,患者的糖尿病發病情況顯著升高(P<0.05),見表2。

表2 不同頸動脈狹窄嚴重程度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verity of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2.3 頸動脈狹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患者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頸動脈狹窄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顯著高于非頸動脈狹窄組(P<0.05),見表3。

表3 頸動脈狹窄組與非頸動脈狹窄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2.4 不同頸動脈狹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不同頸動脈狹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患者的頸動脈狹窄程度的加重,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顯著升高(P<0.05),見表4。

表4 不同頸動脈狹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2.5 不同預后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預后良好組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顯著低于預后不良組(P<0.05),見表5。

表5 不同預后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
2.6 預后不良組與預后良好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預后不良組患者的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癥發生率及NIHSS評分顯著高于預后良好組(P<0.05),見表6。

表6 預后不良與預后良好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6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poor prognosis and good prognosis
2.7 預后不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 通過多因素分析,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癥、NIHSS、miR-181c、miR-21均是造成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7。

表7 預后不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國內外研究證實[9-12],腦梗死的發病與頸動脈狹窄顯著相關。有研究[13]顯示,在頸動脈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造成的血栓脫落極易造成患者的血栓栓塞性腦梗死。微小核苷酸是造成頸動脈粥樣硬化形成血栓的重要基因。mRNA具有顯著的基因調節能力,通過對患者的3’非翻譯區的顯著抑制作用,進而調節患者的胚胎發育以及細胞分化[14]。在心腦血管疾病的進展過程中,mRNA可通過對粥樣硬化及腦缺血缺氧的耐受能力的調控作用,進而影響患者的預后[15]。
本研究中,通過對不同頸動脈嚴重程度的miR-181c、miR-21水平比較,隨著頸動脈狹窄情況的顯著升高,患者的miR-181c、miR-21水平顯著升高。動物實驗研究[16]顯示,在腦卒中小鼠的腦組織以及血液中的miR-181c、miR-21水平呈現顯著的異常變化[17]。而在對腦梗死實驗大鼠的再灌注損傷分析中,實驗大鼠的mRNA顯著升高。在病理生理學的研究[18]中,miR-21可通過對PTEN/AKT的顯著性調控作用,進而影響機體對缺血以及缺氧環境的順應性,進而降低由于缺氧或者缺血造成的應激反應,內皮細胞的炎性水平顯著降低,對于局部頸動脈已形成的斑塊的穩定性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19]。向偉等[20]通過對腦梗死患者的miR-21的水平分析中,隨著腦梗死疾病的進展,miR-21水平顯著相關,與本研究相互印證。而miR-181c與細胞的線粒體的穩定性相關。在腦梗死患者的疾病進展中的新陳代謝能力的顯著作用,進一步影響患者的疾病進展[21]。而從病理學的研究中,隨著局部病灶部位的氧化應激反應以及炎性反應水平的顯著升高,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局部病灶部位的血管老化以及纖維細胞對的增生[22]。王志等[23-24]在腦梗死患者的miR-181c與疾病的預后分析中,患者的miR-181c與不良預后呈現顯著相關性,與本研究相互印證。
而在不良預后的多因素分析中,通過多因素分析,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癥、NIHSS、miR-181c、miR-21均是造成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分布認為,慢性疾病的發展過程中,高血糖、高血脂以及高血壓均會對患者頸動脈血管內皮的炎性反應水平造成影響。而動脈粥樣硬化疾病的不斷進展,血液粘稠度呈現顯著升高趨勢,毛細血管的堵塞風險也進一步發生變化[25],血管內壁的斑塊風險顯著升高,血管表面的光滑性顯著下降,炎性因子對于血管壁的侵襲作用顯著升高,凝血系統顯著激活,最終造成斑塊的不穩定性,而在疾病的進展中,由于斑塊的不穩定性,遠端血管的灌注能力顯著下降,極易造成腦組織低灌注區域的壞死[26]。在疾病發展的早期,機體可通過自身的代償作用,進而對狹窄部位進行擴張,但是隨著代償能力的顯著下降,最終造成腦梗死疾病的進展。
但是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樣本量較小,在對患者的多因素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偏倚,有待在日后的研究進一步完善。
4 結論
隨著腦梗死頸動脈狹窄情況的加重,局部病灶部位的炎性反應水平顯著升高,血清miR-181c、miR-21水平顯著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