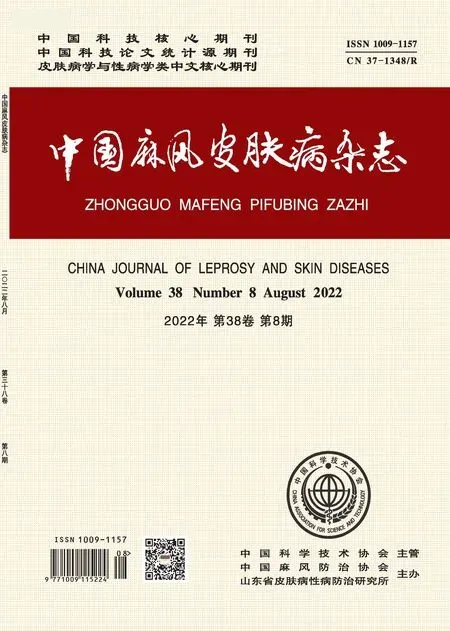瘤型麻風氨苯砜單療復發一例
葉 星 盧憲梅 劉 芳 槐鵬程 初同勝 劉殿昌
1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皮膚病醫院(山東省皮膚病醫院),山東省皮膚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濟南,250022;2榮成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威海榮成,264333
臨床資料患者,女,75歲,山東省榮成市人。因“面部紅斑伴口唇麻木、雙眼疼痛3個月”就診。自述2021年2月始面部出現紅斑,伴口唇麻木,雙眼不適,疼痛流淚,自己懷疑麻風復發。2021年5月12日曾于當地醫院就診,考慮麻風復發,轉診至我院。患者于1957年6月首次確診為LL型麻風,次年3月入駐麻風村,全程予氨苯砜(DDS)單療,于1964年10月臨床治愈;1972年3月確診為LL型麻風復發,再次予DDS單療后于1980年7月判愈。患者本次復發前已存在雙眼、雙手及雙足畸殘。無藥物過敏史。2年前行股骨頭置換術,否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個人史無特殊,配偶及兒子均有麻風史。其配偶于1963年3月確診為TT型麻風后駐村治療并與患者結識,予DDS單療后于1966年12月判愈;1975年12月確診為TT型麻風復發,經DDS單療2年后判愈。其兒子也于1977年6月確診為BT型麻風并經DDS單療2年后于1979年7月判愈。同村無其他麻風患者。
體格檢查:T 36.5℃,P 73次/分,R 15次/分,BP 129/87 mmHg。皮膚科檢查:患者面部彌漫性浸潤,雙側眉毛、睫毛脫落,雙耳垂無肥厚;雙眼瞼外翻,閉合不全,輕閉左眼2 mm、右眼5 mm,伴紅眼、眼痛,雙眼視力正常。左后腰部見一直徑5 cm大淡紅色斑片,邊界不清。雙手爪形指,部分手指攣縮吸收(圖1)。淺表神經未捫及粗大,無觸痛。面部及皮損處觸覺正常,右手淺感覺缺失,左手感覺功能正常。左手小指內收及拇指對掌運動功能減弱,右手癱瘓,其余運動功能檢查無異常。

圖1 1a:面部彌漫性輕度浸潤,雙側眉毛、睫毛脫落;1b:左側腰背部見一直徑5 cm大的淡紅色斑片,邊界不清;1c:手爪形指,部分手指攣縮吸收 圖2 2a:(背部)表皮萎縮,真皮淺中層血管周圍輕度泡沫化細胞及淋巴細胞浸潤(HE,×200);2b:泡沫化細胞及淋巴細胞(HE,×400);2c:抗酸染色:抗酸菌6+,系顆粒狀菌(×400)
實驗室檢查:血常規、生化常規、凝血常規均未見明顯異常。葡萄糖6磷酸脫氫酶無異常,HLA-B*1301陰性。組織液抗酸菌檢查:左眶上(3+),右耳垂(-),下頜(5+),右手腕(5+),細菌密度指數(BI)為3.25。組織病理示:(背部)表皮萎縮。真皮淺中層血管周圍輕度泡沫化細胞及淋巴細胞浸潤(圖2a、2b)。抗酸染色:抗酸菌6+,系顆粒狀菌(圖2c)。皮損麻風分枝桿菌qPCR檢測陽性。
診斷:結合患者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結果,確診為瘤型麻風。收住濟南市麻風院,按MDT-MB方案治療,并囑患者出院后定期隨訪。
討論麻風的復發可能由耐藥菌的存在、持久菌的復蘇暴發、再次感染以及治療不規范或由于錯誤分型而導致的治療不足等因素引起。有研究表明,DDS單療復發率高達38.3%。直至1987年我國正式推廣使用WHO推薦的MDT聯合化療方案,化療藥物包含氨苯砜、利福平、氯法齊明等多種作用機制不同的有效藥物,大大降低了由于耐藥菌、持久菌的存在等原因引起的麻風復發。
本例患者為既往DDS單療治愈者。患者在判愈40年后出現新的活動性麻風皮損,皮膚涂片查菌持續陰轉后又重現抗酸桿菌,且任一部位查菌菌量均2+,皮損活檢組織病理學檢查示活動性麻風特異性病理改變,符合WHO麻風復發的診斷標準。提示我們各地區仍要加強對治愈存活者的定期隨訪,尤其是復發率較高的既往DDS單療患者,及時發現復發情況,避免麻風損害的進一步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