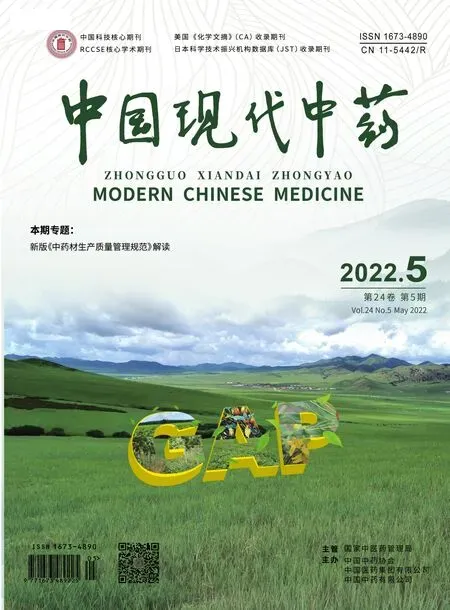經典名方化肝煎的古今文獻研究
楊海菊,黃嘉怡,楊艷玲,李花花,杜守穎,白潔
北京中醫藥大學 中藥學院,北京 102488
中醫藥文化源遠流長,其發展一直以來秉承著承古創新的宗旨。為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推動來源于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復方制劑穩步發展、為人民群眾健康提供更好保障,2018 年4 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會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制定并發布了《古代經典名方目錄(第一批)》(以下簡稱《目錄》)。《目錄》所收載的100 首方劑均在臨床中應用廣泛且療效顯著,在清代甚至以前的醫籍中有詳細記載[1]。
化肝煎作為《目錄》中明末時期的代表方劑,以同基原的青皮、陳皮共為君藥,兩者相輔相成,使全身氣機條達。本文通過對化肝煎的處方來源、歷史沿革、度量衡等方面進行考證,為后期藥材、飲片和物質基準的質量標準研究及制劑二次開發研究提供古代文獻依據。
1 處方來源
化肝煎首載于明代張景岳所著的《景岳全書》卷五十一,原文記載“青皮,陳皮各二錢,芍藥二錢,丹皮梔子(炒)澤瀉(如血見下部者用甘草代之)各錢半,土貝母二三錢,水一盅半,煎七八分,食遠溫服。主治怒氣傷肝,因而氣逆動火,致為煩熱脅痛,脹滿動血等癥。如大便下血者,加地榆,小便下血者,加木通,各一錢五分,如兼寒熱,加柴胡一錢,如火盛,加黃芩一二錢,如脅腹脹痛,加白芥子一錢,脹滯多者,勿用芍藥”[2]。
2 歷史沿革
隨著方劑理論體系的完善和醫家對于疾病的認識日漸深刻,化肝煎的臨床使用發生了變化。通過對明代至近現代應用情況進行梳理,結合當代使用情況進行分析,為該方度量衡和本草考證提供參考。
2.1 明清時期
本方證為怒氣傷肝、氣逆動火所致,脅為肝之分野,肝氣郁則脅痛、脹滿,肝郁化火則煩熱,火熱破血妄行則動血,肝經氣火上逆犯肺則咳吐痰血,治當調氣疏肝、清瀉肝火。方中青皮、陳皮苦溫而疏肝理氣,共為君藥;因肝經郁火用丹皮、梔子苦寒清瀉肝火,火動而傷血,故用芍藥、丹皮入血分,清血熱、瀉肝火、養血行滯,則郁熱自解,因氣火能使痰濕阻滯,故加貝母祛痰解郁,加澤瀉滲濕泄熱,共為臣藥。諸藥相配伍,重在治肝,疏散之中有清瀉之意,剛中有柔,祛邪而不傷正,共奏疏肝理氣、清火解郁之功。由于該方成方年代并不久遠,關于其記載多集中在清代,且以原方入藥的較少,多為加減方。現對相關醫籍整理見表1~2。

表1 明清時期化肝煎原方的臨床應用
《景岳全書》中記載化肝煎主治怒氣傷肝所致的脅痛等,后世文獻多沿用此說法。《類證治裁》《葉天士醫學全書》《成方切用》《醫學全書》《張聿青醫案》中化肝煎原方主治病癥為怒而傷肝所致的脅痛、肝郁所致的血瘀氣滯等,與原記載一致[3]。
由表2 可知,化肝煎加減方在古籍中應用廣泛,加入其他藥味可用于肝郁導致的其他病癥的治療。例如,加赤苓增強祛濕功效;加麥冬、蛤殼入肺經,養陰生津、化痰,用于肝火過旺反克肺金所致的肺陰不足、津液不足等。

表2 明清時期化肝煎加減方的臨床應用總結
2.2 近現代
2.2.1 臨床應用 近現代,化肝煎臨床使用形式多為加減方或聯合臨床常用藥對肝郁所致的胃炎、消化性潰瘍、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疾病進行治療,臨床療效顯著。臨床服用的劑量、煎服法和藥味組成見表3。

表3 近現代化肝煎的臨床應用總結
胃炎在中醫范疇內表現為“痞滿”“胃脘痛”,與脾胃、肝臟有關,治療主要以通為法。由于脾胃疾病的誘發因素較多,臨床常使用化肝煎加減方或與其他臨床常用藥聯合治療。例如,加柴胡協同青皮、陳皮增強疏理肝氣功效;當歸補血活血,加當歸用于腸胃內出血癥治療;白術和雞內金健脾益氣、健胃消食,加白術和雞內金用于恢復脾胃功能;黃連、黃芩苦寒,共用可協助梔子、丹皮增強清熱能力。
肝性屬木,主化育,主藏血。非酒精性脂肪肝發生的主要病因為飲食無度、肝郁氣結、濕熱內蘊等,治療主要從清熱利濕、疏肝健脾著手。經化肝煎治療的患者各項生理指標恢復正常,且與傳統臨床用藥對比發現,化肝煎組治療后的患者脂肪肝、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等各項指標均比對照組低,說明化肝煎在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肝臟病變方面有良好的應用前景。
女子以肝為先天,肝經病則肝郁化熱、氣滯血瘀、月事不調、難于產育。肝藏血,主疏泄,喜條達,若其疏泄功能失常,女子可見經行不暢、痛經、閉經等。乳腺增生多屬肝氣郁結、肝郁化火或痰氣郁結。化肝煎臨床治療效果顯著。原方加香附,用于治療痛經、經行不暢,加桃仁、紅花、丹參可活血化瘀、通經止痛。
對目前查閱到的25 個臨床案例中各藥味的劑量進行統計,其中貝母多用浙貝母,少用土貝母,芍藥多用白芍,少用赤芍,其他5 個藥味的基原與原文記載一致。臨床使用中各藥味的劑量隨證加減,但貝母和芍藥最常使用劑量為15 g,其他均為10 g。
2.2.2 質量及制劑開發研究進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研究人員對經典名方的質量標準及制劑展開了研究。化肝煎作為明末時期的方劑,歷史并不久遠,且在后來無廣泛應用,因此對于其質量的相關研究較為缺乏,僅聶欣等[40]通過超高效液相色譜法(UPLC)對化肝煎建立了特征圖譜并建立了芍藥苷、橙皮苷和丹皮酚含量測定方法。該研究對化肝煎物質基準進行質量把控,同時為后續的制劑開發提供研究標準。
目前,化肝煎無上市制劑,根據文獻,僅有李兵等[41]將其研制成為膠囊劑,以出膏率為指標,通過對提取工藝、輔料種類和用量的考察,確定了最佳制備工藝。
3 單味藥的本草考證
3.1 青皮、陳皮
陳皮最早稱為橘柚,見于《神農本草經》。王瑜真等[42]經過考證發現,陶弘景所用橘柚即為現今之陳皮,且說明陳皮“陳久者良”的特性記載始于當時。宋代“青橘皮”和“黃橘皮”的產生[43],為兩者基原相同提供證明,后《本草征要》[43]、《本草綱目》[44]、《本草圖經》[45]等書中有兩者藥效、采收期的記載,均與現在相同。
陳皮和青皮在《本草圖經》[45]和《本草崇原》[46]中的原植物記載與現在所用陳皮的原植物橘樹一致。綜上所述,陳皮與青皮的原植物形態與現在所用一致,因此本方中兩者基原同為蕓香科植物橘Citrus reticulataBlanco,陳皮的藥用部位為成熟果皮,青皮為未成熟果皮和幼果。
3.2 芍藥
芍藥的入藥部位首次于《名醫別錄》中記載為根[47],此后記載未發生改變。從梁代出現赤、白之分,宋代至明代以花色和根皮顏色進行區分[48],該分類方法經考證存在錯誤。化肝煎主要用于肝郁氣滯所導致的脅痛、腹脹等,芍藥與丹皮同入血分,清血熱、瀉肝火、養血行滯,該功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以下簡稱《中國藥典》)2020 年版中赤芍的功效記載一致[49],與白芍的柔肝止痛區別。因此,本方中所用為赤芍。綜上所述,本方中的芍藥藥材基原為芍藥科植物芍藥Paeonia lactifloraPall.的干燥根,飲片為赤芍。
3.3 丹皮
丹皮入藥最早載于《神農本草經》[50],記為牡丹。本方中丹皮功效為與芍藥同入血分,清血熱、瀉肝火、養血行滯,這與《中國藥典》2020 年版中牡丹皮功效記載一致。《新版國家藥典中藥彩色圖集》中關于牡丹原植物的描述與古代記載一致[51],因此,本方中的牡丹皮與現用的丹皮基原一致。經考證,明代產地主要集中在山西、陜西、安徽、山東等地[52],與現今之產地一致。其藥用部位自有記載以來一直為根,藥材名稱為牡丹,后來隨著實踐發展,明代醫家發現藥材中間的木心大大延長干燥時間,且去除后臨床療效無差異,因此藥用部位逐漸轉為根皮。綜上所述,本方中丹皮為毛茛科植物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Andr.的干燥根皮。
3.4 梔子
3.4.1 梔子的基原考證 梔子最早記載于《神農本草經》,位列中品[53]。古籍中提及的梔子性味,功效與現在的瀉火解毒、清熱利濕的功效相似。古籍中用于入藥的山梔子以七棱或九棱為佳,程大昌曰:“樗蒲子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符合現用梔子果實的形態”[54]。所以,梔子的藥用部位從古至今一直為果實。
關于梔子植物形態的描述,《本草圖經》和《本草綱目》中的記載與《中國植物志》中相似[55],可見當時所用梔子基原與現在相同。梔子的產地經考證有河南、江蘇、四川、云南等中部和南部地區,與現今產地基本一致。目前所用多為上述產地的栽培品種[56]。綜上所述,梔子為茜草科梔子Gardenia jasminoidesEllis的成熟果實。
3.4.2 梔子炮制方法的考證 梔子最早記載于《神農本草經》中,但未提及其炮制方法。經考證,梔子的炮制方法有“擘”“燒末”“酒炒”“炒制”等[57]。本方中梔子注明“炒”,由于明代后期“炒”的工藝已經相當成熟,且當時對炒制程度有詳細記載,《本草蒙筌》中提到“止血用須炒黑色、去熱用但燥而已”[53],可知當時的“炒”即為炒黃。結合本方中梔子的功效為清熱,因此本方中梔子的炮制方法為炒黃。
3.5 澤瀉
關于澤瀉植物形態的描述,《本草圖經》與《本草綱目》中記載的植物圖與《中國植物志》中所載澤瀉幾乎相同[58]。《本草經集注》中記載的藥材形態“尾間兩歧”,符合野生和多年生川澤瀉的藥材特征[58]。明代《救荒本草》中對于澤瀉原植物的描述與現今之澤瀉和東方澤瀉十分接近,并且與《本草經集注》中的描述也十分相似[59]。本方中澤瀉的功效為滲濕泄熱,與《中國藥典》2020 年版中澤瀉功效記載一致,因此方中的澤瀉與現在所用澤瀉原植物相同。澤瀉的藥用部位自《神農本草經》記載以來,一直為“根”,但“形大而長,尾間兩歧”和《植物名實圖考》中的“其根圓白如小蒜”經對比發現實際是塊莖的形態特征[60],所以藥用部位與《中國藥典》2020 年版所載一致,均為塊莖。明代澤瀉產地多為之前的總結,這些產地目前仍有澤瀉出產,并且以四川和福建所產為道地,即川澤瀉和建澤瀉。綜上所述,化肝煎中所用澤瀉為澤瀉科植物東方澤瀉Alisma orientale(Sam.)Juzep.或澤瀉A.plantago-aquaticaLinn.的干燥塊莖。
3.6 土貝母
貝母類藥材自秦漢時期就一直存在基原混亂的問題。經考證,唐代至明末時期貝母類藥材種類達到巔峰,有浙貝母、川貝母、蕎麥葉貝母、土貝母、湖北貝母和安徽貝母等,品種繁雜,使用混亂[61]。本方成方于明末,此時交通較為便利,已出現藥材集散地,因此只能根據方中藥物的功效解析來確定。本方中的貝母作為臣藥,清熱、祛痰、解郁,輔助君藥疏肝解郁,與《中國藥典》2020 年版所載浙貝母功效相似。魏夢佳等[62]考證認為,這里的土貝母即指現在的浙貝母。因此,化肝煎中所載貝母為現今之浙貝母。綜上所述,本方中的土貝母為百合科植物浙貝母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的干燥鱗莖。
4 度量衡考證
化肝煎出自明代末期的《景岳全書》,其中需要考證的度量衡為錢和盅。
4.1 錢的考證
將本方中各藥味的用量進行疏理,相關的記載較少,除《景岳全書》外,僅見于《類證治裁》和《竹林女科證治》,兩者中的芍藥和貝母的用量均與原文記載不同。前者的芍藥用量與原文的二錢一致,后者減為一錢半,方中芍藥與丹皮為清血熱、瀉肝火,后者針對孕育中的婦女施藥,對于寒涼藥物要酌量減少。兩者中貝母的用量分別為二錢、三錢,原方為二三錢,貝母在方中用于祛除因氣火所致的痰濕阻滯,由于孕期婦女體熱,易生痰濕,所以加大貝母的用量[6-7]。綜上所述,與原文對照,方中的芍藥和貝母均為二錢。
本方中的錢作為一個衡量單位,是由唐代初期推行的“開元通寶”這個貨幣名稱——“錢”轉化而來的。當時設計“開元通寶”時,選定一兩作為這個銅幣的質量,并命名為錢[63]。此時的度量衡經考證與東漢時期的保持一致,即一錢合1.38 g[64]。宋金元時期,宋太宗統一度量衡,以2 種小型精密的戮子作為國家級的標準器[65]。據考證,宋時所用度量衡換算關系沿用了唐代。
由于宋元時期度量衡進行了大的變革,因此明代的度量衡在考證時多數依據來源于漢代,但各家之言都不盡相同,只能根據明代出土的實物來進行具體測量[66]。《景岳全書》成書時期為明朝萬歷年間,即明朝后期。據考證,明朝后期與清朝對權衡標準遵循《大清會典》中的規定,以黃銅一立方寸質量為六兩八錢作為衡量一兩的標準[67],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 年)工部制造的“伍百兩銅砝碼”,每斤折合596.8 g[68],一斤合十六兩,一兩合十錢,最終確定一錢合3.73 g。
在現代臨床使用中,貝母和芍藥最常使用劑量為15 g,其他均為10 g,均稍高于上述考證結果,猜測原因為現代臨床使用的劑量未經考證,默認一錢合5 g 所致。這種換算關系是近代才開始使用的,并不適宜運用在該方中,因此還是以考證結果為準。
綜上所述,一錢為3.730 g,即化肝煎中青皮、陳皮、芍藥、土貝母各7.460 g,丹皮、梔子、澤瀉各5.595 g,全方總藥量46.625 g。
4.2 盅的考證
關于化肝煎的加水量,目前有記載的書籍中均沿用了原文記載中的“一盅半”,但對于盅的大小無詳細說明,在同時期的書中也未發現相關解釋。
據考證,盅作為容器量詞首次出現于唐代,此時的“盅”可用“鐘”或“中”代替[69],多作酒器。后至明代服用方式轉變為以湯劑為主,藥量和加水量增大,為了實際操作的方便,盅、碗、杯等量器逐漸被用于醫藥方面[70],《景岳全書》《溫病條辯》等書中均有相關使用。但此時“盅”多為民間使用,其量值大小也因地區而存在差異[71]。金代也存在“盅”的廣泛使用[72]。
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論合和法方中》中記載:“一大盞者,約一升也,一中盞者,約五合也,一小盅者,約三合也”[69],只能得知“盅”是介于“中盞”與“合”之間的單位,即一盅為70~350 mL,此處的一小盅為210 mL,但“一小盅”與“一盅”的概念是否一致,未經考證。顏文強[73]考證,一盅折合為現在的150~300 mL。表3 中多數文獻未標明加水量,或直接采用加水量200 mL,且無文獻考證。現代約定俗成的盅是為口徑9 cm 以下的碗,其容積約為200 mL。
本方加水一盅半,全方46.625 g,藥味來源為根莖或果實。王鳳秀等[74]通過對《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中的經方各加水量及其飲片量進行統計,結果表明,對于根莖、果實、種子類飲片入藥的加水量為藥量的6~8 倍,即一盅為210~250 mL。綜上所述,結合古籍及現代文獻考證結果,一盅為210~300 mL。本方加水量一盅半,即315~450 mL,煎至七八分,即170~240 mL。
表3 中現代臨床對加水量無詳細描述,但多為單煎,且所得水煎液多為200~300 mL,1 日服用2次,飯后溫服,與考證結果170~240 mL 接近,說明上述考證的合理性,因此本方中的“盅”定為210~300 mL。
5 總結
本文通過查閱古籍及相關文獻,確定了化肝煎的處方來源、臨床使用變遷,最終確認的詳細信息見表4,可為后期全方指紋圖譜摸索、煎煮工藝考察及制劑研究提供參考。

表4 化肝煎關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