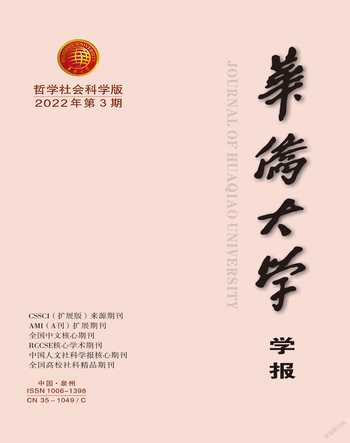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了嗎



摘 要:在世界經濟的新格局下,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水平在各方力量的影響下不斷重塑,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參與國,具有追求經濟收益和經濟增長迫切需求,而對外直接投資是GVC分工水平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探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對沿線經濟體產業分工的影響效應,對檢驗“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踐行其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初衷具有重要意義。以“一帶一路”沿線44個經濟體為研究樣本,利用兩步SYS-GMM模型探析中國OFDI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中國OFDI可以從增加資本存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基礎設施水平四個渠道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但是受中國和沿線國家產業發展水平、投資類型以及“倡議”推行時間所限,提升技術水平尚未成為其機制之一。因此,在與沿線國家產業協作中,要因地制宜,相機抉擇地調整投資對象與內容,積極引導GVC分工的互補合作,保持長效投資與長期合作。
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一帶一路”;價值鏈分工水平;SYS-GMM
作者簡介:丁杰,福建江夏學院金融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合作、金融監管、金融創新、績效評估、可持續性發展等(E-mail:85383813@qq.com? 福建 福州 3501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監管科技在‘自貿區銀行風險控制中的運用研究”(20BJL125)
中圖分類號:F740.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2)03-0079-14
一 引 言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外交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下簡稱“倡議”)的理念就是要創造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其主要目標是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互惠合作、資源互補、共同發展。“倡議”提出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下簡稱“沿線國家”)的政治交流、經濟合作、文化交流顯著增加。中國與沿線國家漸近深入的產業、金融、能源合作亦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肯定“倡議”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的同時,“經濟脅迫論”“資源掠奪論”等論調也時有發聲。鑒于國際上一些觀點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要通過地緣政治來轉移產能過剩的觀點,本文通過驗證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是否促進其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調整,探討其影響機理,分析了在“一帶一路”經濟交流中,是否通過加快資源與技術轉移,提高區域合作強度,重新調整了產業鏈的分工布局,提升了資源流轉效率,為加快“一帶一路”經濟合作提供理論支撐,并針對上述質疑提供有效的反證。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席卷下,全球經濟復蘇緩慢,逆全球化主義逐步蔓延;而隨著2020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新冠肺炎對全球生產體系與供應鏈的強大沖擊,都使得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危機中育新局?自2013年提出“倡議”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實現以“五通”為目標,不斷提升沿線國家的投資便利化水平。2014—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由
136.6億美元增至167.1億美元,年均增長7.0%,顯著高于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2.4%的年均增速。在投資增速的同時,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在出席 “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會時指出“道路通,百業興”,大力支持資源互通帶動區域發展。2018年,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4.8%,其中向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同比增長8.9%。2019—2020年,中國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逐年增長,為構建經濟共同體,提供堅實的合作基礎。截至2021年11月20日,中國與14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6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隨著“倡議”的覆蓋面拓寬,區域內融合度的加深,OFDI為加速我國資源互補,產業升級與全球化分工結構調整提供了契機。因此充分發揮OFDI與GVC分工的互動作用,在國內和國際雙循環中重構GVC分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區域合作加快GVC分工的背景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 中國外商投資是否有助于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中國外商投資影響 GVC分工地位提升的傳導途徑是什么? 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共建“倡議”背景下值得探討的研究課題。因此,本文針對此問題力圖運用沿線國家的面板數據,在實證層面進行驗證,以期形成有效經驗進行推廣。結合相關研究文獻,可以看到,蔣納和董有德(蔣納、董有德:《對外直接投資與境內生存擴延: 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的實證檢驗》,《世界經濟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7—119,136頁。)認為企業可以通過對外投資提升其盈利能力,從而延長企業生命周期;加速國際國內雙循環的聯動效應,通過“倡議”推動企業走出去,從而激發企業生命力。一方面有的學者從國際分工格局(盧偉、李大偉:《“一帶一路”背景下大國崛起的差異化發展策略》,《中國軟科學》2016年第10期,第11—19頁。)、經濟發展水平(郭愛君、朱瑜珂、鐘方雷:《“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沿線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效應評估———基于“準自然實驗”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19年第9期,第59—71頁。)、產業升級(楊玲:《生產性服務進口復雜度及其對制造業增加值率影響研究———基于“一帶一路”18省份區域異質性比較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6年第2期,第3—20頁。)(馬曉東、何倫志:《融入全球價值鏈能促進本國產業結構升級嗎———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據的實證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8年第7期,第95—107頁。) 、全球價值鏈(劉志彪、吳福象:《“一帶一路”倡議下全球價值鏈的雙重嵌入》,《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第17—32頁。)等方面探索“倡議”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學者從公司角度探討“倡議”的實施效果。如孫焱林和何覃飛(孫焱林、覃飛:《“一帶一路”倡議降低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嗎》,《國際貿易問題》2018年第8期,第66—79頁。)通過雙重差分模型,發現通過“倡議”的實施與推進有利于降低投資風險,規避政治風險。這些研究均驗證了“倡議”的正向效果,強調了“倡議”的提出對于降低投資風險、促進投資盈利的積極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另一個關鍵的問題: “倡議”對其沿線國家的價值鏈分工影響如何?具體影響機理是怎樣的?這是加速區域經濟融合、促進價值鏈分工關鍵問題,也是促進生產要素交換,提升企業投資的盈利能力,激發技術交流的持久動力。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通過構建兩步SYS-GMM模型,進一步探討:中國投資對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價值鏈分工水平的影響如何?具體影響機理如何?在影響因素中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具體的傳導路徑是什么?相比現有的研究,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1)研究視角創新。現有學者,多是站在東道國角度,通過資本流入來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影響,而不是從資本流出角度來探討對流入各國的產業鏈分工的影響,著重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文獻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以外商投資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互動關系為研究范疇,探討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產業鏈分工的促進作用。在此基礎上,本文還探討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沿線國家的GVC分工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為提高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提供了理論依據,并為GVC分工水平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視角。(2)研究方法創新。本文通過梳理研究者們對于“一帶一路”區域合作中關于全球產業鏈分工的相關文獻,以44個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基于2003—2017年UN Comtrade數據庫,創新性地使用東道國勞動力稟賦、東道國自然資源稟賦等數據構建兩步SYS-GMM模型,探究中國投資對提高沿線國家價值鏈分工水平的影響,深入探討其作用機制。同時,拓展分析了中國投資對沿線國家價值鏈分工水平差距的影響,為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提供有效的經驗支持。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倡議”的提出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效應的研究,從宏觀、中觀、微觀層面對OFDI對母國經濟增長(隋廣軍、黃亮雄、黃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增長》,《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7年第32卷第1期,第32—43頁。)、產業升級(徐敏、姜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能縮小城鄉消費差距嗎?》,《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年第32卷第3期,第3—21頁。)和企業發展(羅偉、葛順奇:《跨國公司進入與中國的自主研發:來自制造業企業的證據》,《世界經濟》2015年第12期,第29—53頁。)等的影響展開一系列研究。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國際分工和貿易形式發生巨大變化,GVC分工在新生產條件進步和社會分工下由此形成(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4), pp.857-880.)。隨著對GVC研究的不斷深化,學者們對價值鏈升級進行了研究,探究價值鏈重構(劉源丹、劉洪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重構全球價值鏈:基于二元邊際的實證研究》,《國際經貿探索》2021年第37卷第11期,第20—36頁。)(唐宜紅、張鵬楊:《FDI、全球價值鏈嵌入與出口國內附加值》,《統計研究》2017年第34卷第4期,第36—49頁。)、制度質量(李建軍、孫慧:《全球價值鏈分工、制度質量與中國ODI的區位選擇偏好——基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研究》,《經濟問題探索》2017年第5期,第110—122頁。)、政府行為(查日升:《全球價值鏈治理的影響因素與政府作用機理》,《宏觀經濟研究》2016年第6期,第49—57頁。)、產業集聚(謝子遠、張海波:《產業集聚影響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內在機理——基于中介變量的檢驗》,《國際貿易問題》2014年第9期,第24—35頁。)和勞動生產率(張志明、周彥霞、張建武:《嵌入亞太價值鏈提升了中國勞動生產率嗎?》,《經濟評論》2019年第5期,第110—122頁。)(Halpern L, Koren M.Szeidl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2(3),pp.9.)等因素對本國價值鏈升級的影響作用。從前人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影響GVC分工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吸引外資是一國提升本國GVC分工水平的重要舉措,由此也引起了學者對FDI與GVC分工關系的研究。FDI增加資本、提升技術水平是其提升中國GVC分工地位的兩條機制,增加資本為主要促進機制,應在引進FDI基礎上,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各級政府應提供財政支持,提高待遇吸引人才(蔣鵬飛:《FDI對中國GVC分工地位的影響——基于價值鏈升級的視角》,《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年第9期,第21—27頁。)。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OFDI 顯著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GVC 地位指數(姚戰琪、夏杰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攀升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55卷第4期,第35—46頁。)。
(一)FDI與GVC分工水平
FDI對區域合作中的沿線國家GVC地位影響顯著。FDI的規模、領域、政策和東道國情況等會影響一國的GVC分工地位,FDI對中國整體、三大產業、制造業以及不同技術類別制造業的GVC分工地位提升都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王暉:《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影響研究》,北京:中國地質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第86頁。)。一方面中國的FDI通過就業替代效應、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東盟GVC地位的提升(汪瑞英:《FDI對東盟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安徽:安徽大學經濟學院,2021年,第36頁。);FDI對于中國的GVC分工除了在地位上有所提升,還對其參與國際垂直分工和前向參與度的提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對GVC的占比在不斷擴大(蔣鵬飛:《FDI對中國GVC分工地位的影響——基于價值鏈升級的視角》,第21—27頁。)。通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形成全球性生產與服務網絡,鞏固并提升了其GVC分工位置(鐘祖昌、張燕玲、孟凡超:《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網絡構建對其全球價值鏈分工位置的影響研究——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國際貿易問題》2021年第3期,第93—108頁。)。另一方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較高的技術吸收能力能夠強化GVC分工的地位影響,借助資本的跨國流動促進技術溢出效應的轉向(劉景卿、于佳雯、車維漢:《FDI流動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變化——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財經研究》2019年第45卷第3期,第100—113頁。)。FDI增加就業、降低人力成本,從而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技術外溢提高地方全要素生產率(衣長軍,杜鑾燕:《FDI對福建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區域吸收能力的視角》,《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第4期,第73—81頁。)。區域經濟生產活動中,引入FDI,通過財政政策支持與人才吸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從而顯著提高省域全要素生產率(魏下海、林孔團、李冠:《FDI技術溢出、人力資本與海西崛起》,《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28—34頁。)。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
關于外商投資對于GVC升級影響的實證研究,大部分研究結論認為外商投資對東道國GVC升級具有正面影響(CHEUNG K Y,LIN P.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Innov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 Data.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15(1),pp.25-44.)(SANJAYA LALL, RAJINEESH NRRUL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o We Need a New Agenda.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4,16(3),pp.447-464.),但亦有學者得出相反結論(唐宜紅、張鵬楊:《FDI、全球價值鏈嵌入與出口國內附加值》,第36—49頁。)。一方面跨國企業一般通過國外中間品和關鍵零部件在企業內部的跨國流動不斷提高東道國的GVC嵌入度,其通過外資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提高企業對GVC的參與(李磊、劉斌、王小霞:《外資溢出效應與中國全球價值鏈參與》,《世界經濟研究》2017年第4期,第43—58,135頁。)。另一方面一國融入GVC國際分工程度越深, 其產業尤其是制造業配套水平越完善,其GVC分工水平也越高。GVC的嵌入程度是由一國出口的最終產品中,國外生產環節產生的價值所占的比重決定的,因此,多數研究均將出口品的國外附加值占總出口的份額作為衡量GVC嵌入度的重要指標,進而代表其GVC分工水平(李建軍、孫慧:《全球價值鏈分工、制度質量與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偏好——基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研究》,第110—122頁。)。再則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增加東道國“低端鎖定”的風險,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外資對其直接投資大多流入低技術行業,價值鏈高端及核心環節卻被跨國企業牢牢掌控,使東道國日益嚴重地嵌入到低附加值環節,抑制其GVC分工地位的攀升(張淼:《“一帶一路”國家雙邊投資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山西:山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第47頁。)。
具體到本文的研究對象——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方面,首先,美國、日本和西歐牢牢控制了GVC中的研發、設計環節,處在GVC的上游,而中國位于GVC的中上游,更多地從事生產、制造、組裝、加工環節,被視為“世界工廠”,接觸到價值鏈中的高端核心環節不多,而沿線國家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處于GVC分工的中下游水平。因此,中國向沿線國家投資,與沿線國家組成GVC后,將沿線國家嵌入到更高層次的GVC中,顯著增加其國內中間品的附加值,助其實現向更復雜和更高層次的生產網絡邁進,有利于提升沿線國家的GVC地位指數。由此,本文提出假說1:
假說1:中國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地位攀升產生促進作用。
(二)資本積累機制
一國擁有的資本由國外資本和國內資本兩部分組成,FDI進入必然增加了東道國擁有的國外資本數量,但FDI還可能會對東道國國內資本產生擠入(擠出)效應。若產生擠入效應,FDI將使東道國資本增加;若產生擠出效應,FDI將使東道國資本減少。因此,FDI對東道國資本的影響將取決于FDI帶來的國外資本與FDI擠出的東道國國內資本的相對多少。FDI帶來的國外資本多于FDI擠出的東道國國內資本,FDI將使東道國資本增加;反之,則減少。東道國充分使用外資進行本國的產業升級改造,不僅可以解決資金不足問題,還可以在擴大資金規模的過程中,提升資金質量,通過兼并、收購與重組,提升資金使用效率,加快東道國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欒申洲:《對外貿易、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工業技術經濟》2018年第37卷第1期,第86—92頁。)。因此,引進外資帶來的資本增加、資本質量提升以及資本利用效率提高,均會提高東道國GVC分工地位(蔣鵬飛:《FDI對中國GVC分工地位的影響——基于價值鏈升級的視角》,第21—27頁。)。
沿線國家多屬于發展中國家,國內資本存量較小,市場發展潛力大,且“一帶一路”建設為基礎設施建設、自貿區與產業園區投資、能源等產業合作、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等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投資需求。即沿線國家基本處于資本需求大于資本供給的狀態,因此,中國向其投資不僅防止對東道國國內資本產生擠出效應,也會通過與國際資本和東道國國內資本合作的形式引導更多內資和外資的流入,大大增加其資本積累。據此,本文提出假說2:
假說2:資本積累是中國投資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機制之一。
(三)技術創新機制
FDI對東道國技術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技術轉移、技術溢出以及影響東道國自主研發水平等渠道。技術轉移包括水平和垂直兩種方式。水平技術轉移是指跨國公司向東道國子公司進行內部化技術轉移,垂直技術轉移是指跨國公司對其東道國上游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自下而上的供應鏈技術轉移和平行的跨國企業間的技術支撐,都會使東道國企業技術提升,促進FDI技術外溢。但是,這樣的技術轉移效果并不確定,這與東道國自身的技術掌握水平、是否有配套的產業布局、完善的政策支持與健康的金融生態環境有關。FDI對東道國自主研發水平的影響存在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兩個方面。首先,跨國公司通過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進行自主研發的行為本身會拉低或抬高東道國的整體研發水平。其次,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產生的競爭效應、溢出效應和關聯效應亦會對相關產業本土企業的研發行為產生影響。此外,技術溢出的實現往往存在行業異質性(洪世勤、劉厚俊:《中國制造業出口技術結構的測度及影響因素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年第3卷第3期,第77—93頁。),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充分利用各國的創新比較優勢,總體上可以提升中國制造業的GVC分工地位,進一步分析發現在不同類型的行業之間存在異質性(林學軍、官玉霞:《以全球創新鏈提升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研究》,《當代經濟管理》2019年第41卷第11期,第25—32頁。)。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受到行業本身的要素密集度和技術水平的影響,這兩個因素是由行業自身的適應能力決定的。總的來說,不同的行業屬性對應不同的技術要求。資本密集型行業所處的GVC級別高,而知識密集度低的行業所在GVC層次較低。對于外資企業的投資,流入“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資金會帶來高的技術附加值,而內資企業通過自身的技術水平與行業競爭力,將吸引更先進的技術與產業進入東道國,這樣就有利于形成行業內的有效競爭,提升業內綜合水平。即FDI在知識與資本較高的行業中將發揮更大的技術溢出效應。FDI對東道國技術的影響也是這些力量的相對強弱決定的,若FDI使東道國技術水平提高,那么其GVC分工地位亦隨之提高,反之則降低(蔣鵬飛:《FDI對中國GVC分工地位的影響——基于價值鏈升級的視角》,第21—27頁。)。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
沿線國家眾多,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產業發展階段參差不齊,市場開放程度、投資便利化水平不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利益訴求亦存在差異,因此對中資企業的技術吸收水平必不盡相同。技術創新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產生的中介作用存在異質性,在發達國家中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但在發展中國家中其中介作用并不顯著;技術創新在不同制造業的服務化影響中產生的中介作用也存在異質性(潘安、郝瑞雪、王迎:《制造業服務化、技術創新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中國科技論壇》2020年第10期,第104—113頁。)。此外,由于沿線國家自然稟賦和相對優勢差異大,中國向其投資行業分布廣泛,但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度較低的領域,因此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程度應較為有限。鑒于沿線國家的復雜性和中國投資行業的多樣性,本文提出假說3:
假說3:技術創新是否為中國投資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一大機制存在不確定性。
(四)勞動生產率機制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個角度提高東道國的勞動生產率。在外部方面,生產活動往往具有規模效應,隨著市場的擴大,相關產業將在一地區高度集聚,產業生產要素專業化程度提高,內部規模效應和外部規模效應得以發揮,有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成本的降低。GVC對生產率既產生地區內溢出,也產生地區間溢出,且這種空間溢出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改善鄰近地區資源再配置結構實現的(邵朝對、蘇丹妮:《全球價值鏈生產率效應的空間溢出》,《中國工業經濟》2017年第4期,第94—114頁。)。此外,垂直型OFDI通過對產業間及關聯企業的交流合作,可以有效整合資源,提升生產效率;水平型OFDI通過產業內生產與競爭,實現產業鏈上下游的整合與資源調配,從而提高資源利用率,加強管理水平提升,促進全行業的生產效率提高與產業升級。各國加強生產合作,充分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和最大限度享受價值鏈嵌入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實現生產率持續提升(鐘世川、梁經偉、毛艷華:《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對生產率提升的影響機制研究——基于技術創新方向和資源配置效應的視角》,《國際貿易問題》2021年第6期,第110—125頁。)。此外,與當地同類外資公司的競爭,會倒逼東道國企業加大研發力度,更新技術設備,吸收優秀人才和總結管理經驗,并最終促進本國相關行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和生產率水平的上升。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亦會帶來GVC分工水平的提高。
沿線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普遍較低,中國對其投資會促進產業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的發揮,并通過關聯效應和競爭效應促進東道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推動其GVC分工水平的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說4:
假說4: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中國投資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機制之一。
(五)產業結構優化機制
根據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案例,日本學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認為,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開放市場,當國內產品和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擴大本國生產規模,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隨后得到一個國家產業的發展大致經歷四個階段,即: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出口。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強調了從學習模仿到自主生產,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機理。由此可知,產業轉移是資源優勢、稟賦優勢和市場優勢差異引起的產業從一個地區轉移至另一個地區的現象,其主要表現形式是資本流動,核心內在機制是利益驅動,引進與利用外資是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王全春:《產業轉移與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46頁。)。產業轉移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與對外投資的方式息息相關,順梯度的專業轉移使東道國接觸到更為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使東道國企業能通過“干中學”效應加快與外資企業進行產業關聯,進而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關于產業結構與GVC分工地位關系研究方面,多數學者持產業結構升級會促進GVC分工地位提升的觀點(張輝:《全球價值鏈理論與我國產業發展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4年第5期,第 38—46頁。)。
由于沿線國家多屬于產業發展水平不高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其進行的也主要屬于順梯度投資,通過向沿線新興國家適宜地轉移部分產業,一方面契合了沿線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會對沿線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產生積極效應(張江馳、謝朝武:《“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東盟旅游產業合作:指向、結構與路徑》,《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25—34頁。)。由此,本文提出假說5:
假說5:產業結構優化是中國投資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機制之一。
(六)基礎設施機制
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為分工水平攀升提供基礎的支撐作用,是一個國家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物質基礎,有利于推動一國或地區生產專業化和產品價值鏈的高端化進程。基礎設施對GVC分工地位的影響效應呈現“倒U”型,中國和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具備一定的規模,但是還存在很大的缺口,總體上尚處在“倒 U”型拐點值的左側(郝曉、王林彬、孫慧.等:《基礎設施如何影響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國際經貿探索》2021年第37卷第4期,第19—33頁。)。另外,“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不完善的現實,則成為其價值鏈升級推進丞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利用和發揮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人才和技術優勢,“基建先行”也就成為“倡議”實施的理性和現實選擇,并且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徑,基礎設施結構具有門檻效應,基建投資占比超過達到一定程度后,其對 GVC 地位的中介效應才能凸顯(邱雪情、卓乘風、毛艷華:《“一帶一路”能否助推我國全球價值鏈攀升——基于基礎設施建設的中介效應分析》,《南方經濟》2021年第6期,第20—35頁。)。《2018年度“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顯示,2014年以來,尤其是2017和2018年度,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指數大幅提升。現有實證研究也表明(李建軍、李俊成:《“一帶一路”倡議是否增進了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績效?》,《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6卷第4期,第61—73頁。),“倡議”顯著促進了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據此,本文提出假說6: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
假說6:基礎設施改進是中國投資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機制之一。
具體影響機理及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三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在時間選擇上,本文采用2003—2017年UN Comtrade數據庫BEC分類法下的中間產品貿易數據,確保了時間跨度的長期性、有效性和即時性;在樣本選擇上,本文以4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確保了樣本對象的全面性。本文數據均源于UN Comtrade、WDI、wind官網等網站,使用stata15進行統計分析。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為驗證假說1,分析中國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影響,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GVCi,t表示i國在t年份的GVC分工水平。鑒于WIOD或TIVA數據庫數據的陳舊性,且不能涵蓋大多數沿線國家的樣本,所以本文借鑒李建軍和孫慧(李建軍、孫慧:《全球價值鏈分工、制度質量與中國ODI的區位選擇偏好——基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研究》,《經濟問題探索》2017年第5期,第110—122頁。)的做法,采用沿線國家中間產品貿易額占該國貿易總額比重,作為衡量GVC嵌入度的替代變量。GVC嵌入度代表一國融入GVC分工水平,一國融入GVC國際分工程度越深,其GVC分工水平也越高。
investi,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表示中國在t年份向i國的投資水平。為保障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選擇中國向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存量作為代理變量,并使用直接投資流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另外,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GDP、人均GDP、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勞動力豐富程度、自然資源稟賦水平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由于GDP和人均GDP數值較大,本文對其進行了對數處理。T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變量的具體含義說明見表1。
為驗證本文假說2—6的正確性,本文構建了交乘項invest×infru、invest×indus、invest×produc、invest×capital、invest×patent,分別表示基礎設施機制、產業結構優化機制、勞動生產率機制、資本積累機制以及技術創新機制,并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mechanism代指infru、indus、produc、capital、patent。infru表示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指數。在參考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選取每百人固定電話訂閱數、每百人固定寬帶訂閱數以及港口基礎設施水平三項指標,借助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數據降維生成。indus代表產業結構指數,本文借鑒徐敏和姜勇(徐敏、姜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能縮小城鄉消費差距嗎?》,《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年32卷第3期,第3—21頁。)的做法,將一、二、三產業均納入指標測算中,構造產業結構指數:
indus=∑3[]m=1ym×m,1indus3
m=1、2、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ym為第m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indus數值越大,表明該國家的產業結構層級越高。produc表示勞動生產率。本文參考張志明等(張志明、周彥霞、張建武:《嵌入亞太價值鏈提升了中國勞動生產率嗎?》,《經濟評論》2019年第5期,第110—122頁。)的做法,選取勞均總產值即總產出與總就業人數的比值作為其代理變量。capital表示資本積累,選用不變LCU的總資本形成來表示。patent表示技術創新,選用東道國當年的專利申請數來表示。上述數據均來自于WDI數據庫。
四 回歸分析
由于將滯后解釋變量納入了回歸方程,使解釋變量與隨機擾動項間存在相關性,并產生內生性問題,故采用標準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會導致參數估計具有不一致性(徐云松:《貨幣政策、影子銀行與銀行流動性》,《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8年第20卷第5期,第18—27頁。)。本文選擇GMM方法進行估計,該方法解決了內生性問題且在單位根存在的情況下依然有效。GMM方法主要有DIFF-GMM和SYS-GMM兩種。由于SYS-GMM可以估計不隨時間變化的系數,同時還可以克服弱工具變量問題,符合本文對數據分析的需要,故而本文選擇SYS-GMM方法。同時,為克服本文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截面相關性問題,保障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選取兩步SYS-GMM進行估計。
表2模型(1)展示了中國投資對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影響的回歸結果。從Sargan檢驗、Hansen檢驗以及AR(2)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模型選擇的工具變量都符合外生性條件,且模型不存在過度識別和二階自相關問題。L.GVC的系數顯著為正,且系數值達0.764,說明一國GVC分工水平的近80%是由其前期基礎水平決定的。invest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中國投資顯著提升了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驗證了本文假說1的正確性。從各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來看,lngdp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體量越大,市場規模越大,其GVC分工水平也越高,也從側面說明了國內消費需求對培育本國產業發展和升級的支撐作用。lngdpp系數不顯著為負,說明對于沿線國家而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帶來GVC分工水平的提高,甚至會降低其GVC分工水平,這可能與其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很多“一帶一路”經濟體過多依賴自然資源稟賦去獲取經濟發展,容易陷入“資源詛咒”陷阱。故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并未帶來本國工業系統的升級和GVC分工水平的提高。gdpg系數顯著為負,說明經濟增長較快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普遍具有較低的GVC分工水平。這與發展中國家產業發展水平普遍不高的現實相符。gdpgg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處于經濟深化發展階段的國家傾向于取得更高的GVC分工水平,亦說明了經濟深化發展對于GVC分工水平攀升和產業升級的重要作用。rural系數不顯著為負,說明勞動力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普遍具有較低的GVC分工水平。這與沿線國家中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資源較為豐富的事實相符。nature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自然資源稟賦豐富的沿線國家普遍具有較高的GVC分工水平。自然資源稟賦作為國家發展的相對優勢之一,會對其GVC分工水平提升產生一定的拉動作用。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
表2模型(2—6)展示了機制檢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invest×infru、invest×indus、invest×produc、invest×capital的系數顯著為正,invest×patent的系數不顯著為正,佐證了本文假說2—6的正確性。說明資本積累、勞動生產率提升、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是中國投資促進沿線國家GVC分工升級水平的四個機制,與Halpern(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2(3),p.9.)、胡昭玲和宋佳(胡昭玲、宋佳:《基于出口價格的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3年第3期,第15—25頁。)、楊高舉和黃先海(楊高舉、黃先海:《內部動力與后發國分工地位升級——來自中國高技術產業的證據》,《中國社會科學》 2013年第2期,第25—45,204頁。)、蔣鵬飛(蔣鵬飛:《FDI對中國GVC分工地位的影響——基于價值鏈升級的視角》,《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年第9期,第21—27頁。)等的研究結果相一致。而技術創新機制尚未成為其機制之一,與唐宜紅和張鵬楊(唐宜紅、張鵬楊:《FDI、全球價值鏈嵌入與出口國內附加值》,《統計研究》2017年第34卷第4期,第36—49頁。)、羅偉和葛順奇(羅偉、葛順奇:《跨國公司進入與中國的自主研發:來自制造業企業的證據》,《世界經濟》2015年第12期,第29—53頁。)的研究結果相符。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向沿線國家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強。這可能與沿線國家產業結構不完善、市場化程度較低、政府管制較多有關。
五 研究拓展
當前沿線國家在GVC分工的地位較低,中國的GVC地位也遠低于美、日等國。但是中國處于“一帶一路”區域合作的價值鏈高端。中國在進行“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中,通過投資顯著提高了GVC分工水平。那么,中國投資是擴大、還是縮小中國與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差距呢?這對于分析中國投資對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業互補性和競爭性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若中國投資擴大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差異,說明中國投資可能增強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業互補性,反之則說明加大了雙方的產業競爭性。鑒于此,筆者通過將中國GVC指數與沿線國家GVC指數相減,得到GVC分工差距水平指數diff,分析中國投資對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差距的影響。為此,本文構建了以下模型:
表2模型(7)展示了相關回歸結果。invest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中國投資減小了與沿線國家在GVC的分工程度上的差異性,也進一步說明中國向沿線國家的投資,對東道國的GVC提升作用大于對中國的提升作用。“沿線國家中不乏勞動力資源豐富、產業結構較為完善的國家和地區。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國內產業的升級轉型與國內外貿易的頻繁摩擦,中國大量的產業逐漸向沿線國家轉移,其中不乏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投資。這些行業企業的引入,促進了東道國GVC分工地位的提高。但處在經濟發展動能轉化階段的中國,雖正經歷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快速發展,但其尚未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仍不可小覷。加上近年來國際經濟環境低迷,貿易摩擦頻發,以及國內傳統產業去產能等政策的推行,傳統產業發展態勢亦不樂觀。在此情況下,中國大舉對外直接投資反倒會加劇傳統產業空心化程度的提高,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會加劇負面影響,不利于GVC分工水平的提高。這也導致中國與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差異減小,不利于中國在“一帶一路”價值鏈中主導地位的保持和核心地位的形成,亦可能會加劇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業競爭性,影響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長期產業協同發展。
六 穩健性檢驗
為了更全面保證本文研究結果的穩健性和可信度,本文采用改變代理變量和改變回歸模型的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分別使用直接投資流量作為代理變量,使用一階SYS-GMM模型和DIFF-GMM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限于篇幅,僅在此展示部分回歸結果。表3和表4展示了使用直接投資流量作為代理變量和使用一階SYS-GMM模型的回歸結果。其結果與使用兩步SYS-GMM模型大致相同,佐證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但是使用DIFF-GMM模型得到的結果標準誤更大,亦說明兩步SYS-GMM在保障回歸結果較強穩健性的同時,會低估標準差。
七 結論與啟示
“倡議”提出9年間,愿景和理念迅速轉化為行動和成果,為參與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祉。本文以4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基于2003—2017年UN Comtrade數據庫BEC分類法下的中間產品貿易等數據,通過構建兩步SYS-GMM模型,探究中國投資影響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的提高程度,深入探討其作用機制,并拓展分析了中國投資對中國與沿線國家GVC分工水平差距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中國投資顯著提高了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且增加資本存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基礎設施水平是其四個作用機制,提升技術水平尚未成為其機制之一。同時,中國投資減小了與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差異,可能會造成中國與沿線國家在產業方面的競爭增大。隨著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加深與經濟融合,GVC分工將從合作型走向競爭型。因此在現階段,應因地制宜加強GVC分工的長遠布局。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結合“倡議”宗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加強制度支撐,提升投資效率。中國投資有效提升了沿線國家的GVC分工水平,因此在現階段,中國應立足全球視野,展現大國擔當,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合作環境。并且要積極加強政策指引與支撐,提升政府服務效率,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簽訂雙邊投資合作協定,從而提高中國企業赴“一帶一路”投資的便利化水平,使中國發展紅利更多惠及沿線國家和地區。同時,加強交通的“互聯互通”,建立完備的物流體系與聯運系統,通過港口、鐵路、公路、航空等多渠道進行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聯通,創新區域內外貿易合作模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與資源整合。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
二是加強企業創新,促進產業協同發展。中國企業在向沿線國家投資進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亦要注重加強企業的研發創新。通過要素的創新,提升產業的綜合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從而進一步推動國內產業的轉型升級。改變國內經濟結構,加速供給側的改革,加快新興產業的成長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銜接好新舊動能的轉化,進而提升在GVC分工中的地位,減弱中國向沿線國家投資過程中可能帶來的產業競爭效應,確保我國在對沿線國家的投資中處于核心區位。積極推進產業發展,形成區域內協同產業鏈,加快生產要素周轉效率。在創新過程中,要注重服務領域的創新與人才的交流發展,通過設立創新園區,以點帶面輻射至沿線國家。根據不同國家、不同領域人才需求,制定吸引人才政策,為產業協同發展助力。
三是構建區域價值鏈,促進價值鏈升級。在發達國家主導的GVC中,美日等發達國家掌握著GVC的核心環節,主要是產品的研發與設計處在GVC分工的上游。發展中國家要在GVC分工中掌握主動權,相當有局限性。而以“一帶一路”為發展契機,重新構建區域內產業鏈,縮短制造業的分工進程,提升市場反應效率,結合沿線國家的資源稟賦與技術互補,有利于實現產業分工重組與升級轉型。另一方面價值鏈的重新整合又進一步促進了中低技術制造業發展。構建區域價值鏈,提供了中國參與分工的高附加值環節,有利于促進中國主導區域的價值鏈發展,并提升中國在GVC分工的主動權,形成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生產要素互動,加速區域內產業鏈價值循環。這將有利于促進中國和沿線國家的產業升級轉型,以及加速產業核心價值的創新與提升。
四是深化交流合作,提高企業盈利能力。中國在“一帶一路”投資建設中,加速了資源的互聯互通,也促進了投資效益的提升。深入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和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投資的互動,形成投入產出的高效閉環;另一方面降低了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的成本和風險,進而提高中國企業的投資盈利能力。通過“倡議”加強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度,深化政府間的“倡議”交流,增加國家高層互訪頻率,形成良好的政治合作體系。積極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效率,通過政策支持與文化交融,促進形成良好的貿易投資氛圍。在合作中,積極提升中國與沿線國家間的經濟融合,加快雙邊國家交通基礎設施和網絡設施的建設,提高運輸效率; 主動推進雙邊國家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提高海關檢驗檢疫的合作程度,降低交易成本; 加速推動沿線國家建立代理金融機構,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構建良好的合作環境,加速企業間的技術資源交流,促進盈利能力提升。
Does Chinas OFDI Improve the GVC Division Level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 Dynamic Panel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44 Countries
DING Jie
Abstract: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GVC) is constantly resha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orces, and Chinas 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GVC.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hinas OFDI on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o test wheth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fulfilled its original intention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aking 4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inas OFDI on the level of GVC division of labor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using the two-step SYS-GMM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OFDI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GVC division of labor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four channels: increasing capital stock,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pgrading infrastructure. But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level has not yet matured due to limit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investment type and implementation time of the “initiative” i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 should adjust investment objects and content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ctively guide the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of GVC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intain long-term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s OFDI; “Belt and Road”; Value Chain Division Level; SYS-GMM
【責任編輯:吳應望】
收稿日期:2022-03-14EB67B8F1-1565-490F-B944-B66ACF789F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