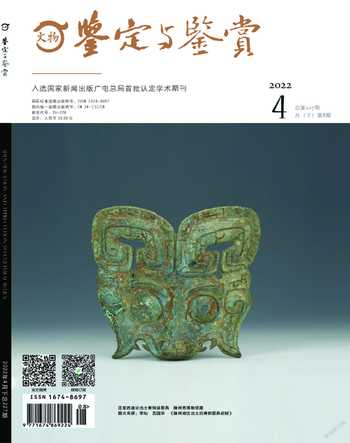紙質明器起源與流行的社會成因探析
朱謹 左堃鈺
摘 要:紙質明器作為一種從魏晉時期流傳延續至今的喪葬習俗,其背后一定隱含著特殊歷史背景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文化需求的轉型。文章通過實物資料的舉證和史料分析,還原紙質明器從誕生到興起的過程及發展方向,從社會需求角度分析紙質明器普適化發展的原因,探索古代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和風俗習慣,為明器演變和葬儀發展變遷史建立基礎。
關鍵詞:明器;喪葬;紙質明器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8.024
紙質明器以冥幣或文書為主,在唐宋時期出現了較為系統的分類,并逐漸演變至今。紙質明器的傳播范圍及運用可以表現出社會風氣的轉變,即基層民眾對紙質明器的出現呈現出接納采用并不斷將其完善發展的態度。在宋朝這一禮俗極為普遍,甚至出現了相關的生產行業。
目前,考古發掘中關于紙質明器的實物資料最早出現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年代從西晉時期延續至唐朝,代表著中國葬儀在形式上的革新,對其起源探究已然成為明器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環。
1 紙質明器的起源與功用
《封氏見聞錄》載:紙錢,今代送葬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加雕節,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后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后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已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涂車芻靈之類。古埋帛金錢,今紙錢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也①。從中可以看出紙錢是由漢代瘞錢演變而來,唐宋時期大多數墓葬仍采用紙錢和錢幣并用的隨葬方式,且對紙錢的顏色也有較高的要求,以黃色為主,這點可能是為體現出對死者的尊敬,用金黃色的紙錢代替黃金陪葬②。《太平廣記》中也有相關記載:“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云:“世作錢于都市,其錢多為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于家中密室作之。”③可見唐代已經出現了專門制作紙錢的手工作坊,并有了相對應的稱呼和獨特的產業模式,這也反映出紙質明器的發展以及其更加廣泛地被應用在葬禮中。
另外,紙錢這一概念也頻繁出現在唐詩之中,如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中所寫:“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王樊志所作“只得紙錢送,欠少元不知。門前空言語,還將紙作衣”這首詩不僅提到了紙錢,還提到紙質明器中的紙衣。但由于紙制品不容易保存,目前出土數量較少,且大多分布于西北地區。
考古資料顯示,紙質明器最早出現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高昌故國北部,現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吐魯番市三堡鄉向北2.5千米。阿斯塔那墓葬群自1959年開始發掘至今,已經先后對其進行過13次考古發掘,發掘墓葬近400座④。其中出土的紙質文書對該墓葬群斷代問題提供了較大的幫助。
2 紙質明器起源問題探究
紙質明器的種類多樣,但其中紙錢的作用相較于其他紙質明器的運用范圍更廣,且具有更多的實物資料。關于紙錢的最早出現時間學界尚無定論,但大致在魏晉時期。由于其“紙質”的特殊性,常常流傳出和蔡倫相關的志怪故事。其起源于祖先崇拜,體現出對死者獨特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對死后世界的構想及崇敬。紙錢的發展與演變根本上是時代對民俗的積累與淘汰,最后呈現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而不是某個歷史人物的功績。如唐代王玙改革并完善了民間喪祭中的焚紙錢之俗,使喪祭具有官方禮儀的性質,后世便認為這是其個人的功績,這樣的觀點是不全面的⑤。
從中國古代喪葬習俗的趨勢來看,紙質明器的出現也體現了社會階級在一定程度上的割裂性。從整體上看,中國古代的喪葬禮俗還是厚葬、久喪占主導地位⑥。而對于唐代貴族而言,紙質明器的流行及紙錢的應用并不影響其實際隨葬品的種類及數量,而紙錢僅作為一種葬儀上的新形式,以此體現出其對死后世界的尊重及更加“文明”的喪葬觀念。以一些貧困地區或貧民墓葬為例,其中不乏一些類似于紙棺、紙偶的隨葬品出現,這說明對于百姓而言,紙質明器已經成為一種可代替其他陪葬品的物品,受厚葬這樣的社會風氣影響,選擇用紙質明器來代替其中超過墓主人能力之外的陪葬品。
3 紙質明器的功能考
由于唐代有寒食節禁止焚火的律例,所以人們常常選擇瘞埋或直接將紙錢放置在墓葬附近,以此來表示對死者的尊重。《舊唐書》描繪出當時中元節的熱鬧景象:賣明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彩衣服。以紙糊架子盤游出賣⑦。
到了宋代由于沒有法律的限制,焚燒這一方式便逐漸流行起來,甚至宋孝宗在祭祀自己祖先時也會焚燒紙錢。在宋代,紙錢在葬禮上的應用已經較為普遍,漸漸在宗教活動上人們也開始使用紙錢作為一種祭祀手段。北宋初期,福州的東岳行宮舉行祭祀儀式,人們都用紙錢去祭神祈福⑧。而紙質明器開始更廣泛的代替其他材質類型的明器出現于宋朝。在長安民間遇喪葬時會陳列“偶像”,其中外表用綾紗金銀做成的“偶像”稱“大脫空”,外表用紙并著色的“偶像”稱“小脫空”,長安城里有許多專門生產和經銷“脫空”的店鋪,組成“茅行”,這也促成了相關手工作坊的發展,比如紙馬鋪的出現。
紙質明器的廣為應用更多體現了宋代喪葬觀念的進步化趨向,當然這和當時的科技文化發展也有相當大的關系,比如紙質明器就離不開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正如用石傭等人形雕刻物來代替活人殉葬一樣,祭祀形式的去野蠻化和便捷化更多是隨著社會發展的。人們逐漸開始反思與改變固有習俗,這一過程也許會非常漫長,但也必將導向社會意識在某一方面的完善與進步。
4 出土紙質明器種類與形制分析
國家文物局“中國古紙的科學價值挖掘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表明,新疆吐魯番地區墓葬群的出土古紙年代從十六國時期至唐代不等,大多使用抄紙法或澆紙法制作,少量使用抄造法制作而成⑨,為研究西域造紙技術提供了較大的幫助。
阿斯塔那墓葬群所見紙質明器數量龐大,由于新疆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干燥的氣候,使墓葬群中的紙質明器保存得非常完整。根據用途可分為紙鞋、紙冠、紙棺、剪紙、紙衾、紙錢五類。
在06TAM601至06TAM605號墓葬中出土紙鞋制作工藝較為簡單,表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傷,但總體呈現較為完整的形態。另外,在363號唐開元年間的墓葬中發現了紙靴一雙,其制作工藝較為特殊,目前僅此一雙出土。紙棺、紙帽的出土數量較少,但整體保存完整。紙棺目前僅發現一座,因紙質棺材無法起到保護墓主人遺體的實際作用,似乎僅起到一種流程上的儀式功用。
哈拉和卓古墓出土七枚人形剪紙⑩。此類習俗最早在三國至魏晉時期的中原地區流行,大致起辟邪或作為奴婢存在的作用,表現出與活人祭祀類似的目的與功能。紙衾即紙被,多用廢舊紙張制作而成,少量出現在阿斯塔那墓葬群中。阿斯塔那墓葬群第521號墓葬發現了最早的紙錢,其年代大概在魏晉至初唐時期。紙錢仿銅錢而制,且大多隨葬在墓室,并未采用焚燒的方式。陸錫興認為這是早期紙錢的特征,是當時焚燒紙錢的習俗尚未傳入西域的結果k。
5 紙質明器的發展及使用考證
紙質明器的變化呈現出種類更多樣、制作工藝更精致的趨勢。如新疆阿斯塔那墓葬群中382號十六國墓葬用舊文書折疊粘貼成鞋幫,外面糊裱紅地白方形絹鞋面,其與貞觀十七年(643)301墓中出土紙鞋制作方式與造型相像,均與當時布鞋相似l,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進步,紙鞋的制作也趨于更加美觀的態勢,采用縫制的方式代替曾經的折疊粘貼更加牢固。在哈拉和卓墓葬群中,其中在盛唐到中唐時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人形剪紙,這也許是一種用于招魂的剪紙m,這就體現了紙質明器在種類上的豐富,側面反映出人們給予了紙質明器更多的意象與“寄托”。吐魯番木納爾墓地出土紙質明器的數量和種類較少,且均以紙錢為主。M102號墓出土過一組用唐代官府牒文剪成的剪紙冥幣n,并出土部分文書及衣物疏。該墓葬位于一處家族墓葬區中,通過還原墓志銘得出該墓主人姓宋,年代大致在顯慶元年(656)二月。
與木納爾墓地相比,阿斯塔那墓葬群與哈拉和卓墓葬群中出土的紙質明器不管是從數量或種類上都要更多,也因此更具備研究價值。斯坦因在進行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進行了部分發掘,獲得大量文物,其中就有一件紙錢,這是新疆地區第一次發現的紙質明器。從現存狀態看,這與木納爾新出的紙錢一樣,也是一件正在制作中的半成品,并且整體形貌俱在,可謂難得o。
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紙鞋、紙帽、紙棺、剪紙、紙衾、紙錢。哈拉卓和古墓葬群還發現了7枚人形剪紙p,出土此類紙質明器的墓葬大多處于盛唐至中唐這一時間階段,制作工藝也逐漸成熟。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紙錢制作基本有兩種方式:一是剪制而成,效率較為低下;另一種是鑿制而成,簡單來說就是用刻刀進行鑿刻,而新疆地區的紙錢基本呈現出兩種模式混合生產的狀態。但總體來看,鑿制法似乎更加常用一些。
從新疆地區出土的紙錢形制來看,中原地區的風俗習慣尚未完全傳入西北地區。且由于經濟原因,當地人常常選擇使用廢舊紙張來進行紙質明器的制作。但不管是怎樣的使用方式,最后都體現出中國古代人民對于鬼神之說的敬畏及對祖先的崇拜和尊重,包括紙質明器的誕生也正是適應了這一需要,而之后不斷豐富的種類和形制,也正體現了人民的需求在不斷地隨著社會經濟變化而產生變化。
6 古代社會的否定與認同評價
伴隨著紙質明器的興起與流行,結合宋代出現的獨特階層—士民階級對這一現象呈大范圍接受并廣泛應用的態度,導致“紙錢”這一代表性明器物品流行于社會各階層之中,改變了人們的社會生活。當然,該類現象也引起了上層階級的注意,即引起了士大夫階層對這一現象的批判與再討論。
古有“含襚赗賻”之禮,珠玉曰含,衣裳曰襚,車馬曰赗,貨財曰賻,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殮葬也。今人皆送紙錢贈作,諸為物焚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賻襚之禮q。上述其本質上是對紙質明器的抵制,原因有二:一是認為紙錢不如金錢實用;二是認為有失儒家所信奉的“禮”。“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r,例如朱熹在其母親去世時都未曾使用紙錢祭祀,并對紙質明器持批判態度。陸游在《放翁家訓》中寫道“近時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當一切屏去。”可知陸游不僅反對紙質明器,更反對奢靡成風的葬儀和葬禮,崇尚簡樸的喪葬儀式。
從文獻所載不難看出對紙質明器的批判,但亦有支持者。邵雍辯護道:“明器之義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s可知邵雍在祭祀使用紙質明器。戴植也認為紙質明器的出現是社會進步的體現t。究其本質,士大夫階級對紙質明器問題的探討,根源在于已經產生轉變的社會風俗,其變化和宋代高度發達的經濟狀況、佛教觀念的轉變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離不開關系,而紙質明器就是這幾種觀念糅雜后的外在表現,代表著社會意識和風俗習慣的發展與轉變,不論士大夫階級接受與否,這種在當時看來具備進步性的現象都難以消失,并最終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模式。
7 紙質明器盛行的原因分析
紙質明器的興起與盛行首先離不開科技水平的進步與發展,即造紙術和雕版印刷術的大規模應用。唐代皮紙已經開始大量生產,而“竹紙”的發明造價低廉,紙質明器趨于多樣化。吳自牧在《夢粱錄》中的記載:“遞年浙江諸富家舍錢作會,燒大燭數條如柱,大小燭一二千條,香紙不計數目。”香紙作為一種人們在燒香時使用的紙類,可見其用途之廣泛。由于社會需求量的增大,唐代出現了專門進行紙質明器制作的手工作坊,隨著宋代對紙質明器分類的精細化和工藝上的精致化,出現了專門售賣喪服、紙人等明器的店鋪。
用紙質明器代替部分真實貨幣更為經濟實惠,這可能也與當時社會風氣的變遷有關。唐代雖然對葬儀有著階級屬性上的明確規范,但當時的陪葬品也多以玉器、瓷器等做工復雜的手工藝品為主,較為奢侈。相比之下,紙質明器無論從工序到成本都更加契合人民的生活需求,也因此得以更好地發展。
紙質明器的流行與發展也起到一定程度上阻礙盜墓行為的發生,具有保護財產的作用。中國古代的葬儀普遍呈厚葬、久喪這一趨勢。在宋代理學思想的再度發展和孝道思維的引導下,人們往往將喪事和孝道相結合,使其成為一種衡量倫理道德的標準。在這樣的價值倡導下,陪葬品的種類和數量也大大增多。因此盜墓行為也蔚然成風,唐代便有多座陵墓被盜,五代時期更甚,并延續到宋代,這與大眾對“入土為安”的思想觀念相悖,為尋求解決措施,在保證祖先不被打擾的前提下,盡可能體現后代的美德。
8 結語
紙質明器的誕生是為了適應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需求,當社會意識觀念與社會現實產生對沖時,人們往往需要謀求新的解決方式,因此,選用一種既可以減少經濟成本避免盜墓行為侵擾先祖“安寧”,又可以體現出個人對孝道等儒家傳統道德標準追求的祭祀手段是非常必要的。貫穿中國古代的這種厚葬、久喪的喪葬傳統最早誕生于原始人類對死亡的不客觀認知及祖先崇拜。殷商之后受“尚文”觀念影響,即社會認知轉變,隨即演變成一種階級概念,《周禮》中對諸侯列鼎制度的明確規范正體現出這一點,直至孟子將喪葬習俗與“禮”相結合,直接影響到秦漢儒學家喪葬觀念的轉變。
在當時社會的現實要求下,紙質明器的出現確實迎合了社會階層中大部分人群的需要。對于普通百姓而言,紙質明器足夠經濟實惠,且具有進步性。而對于上層階級而言,紙質明器僅作為祭祀或喪葬環節中的一環,不與原有規格產生沖擊,甚至可以更便利的進行應用。到了今天,紙質明器更多地體現出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比如不同膚色的紙人或各式紙錢等,這是我國民俗文化中常見的現象,應當進行深入研究與再討論。
注釋
①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②夏金華.紙錢源流考[J].史林,2013(1):69-76,189.
③李昉.太平廣記:卷381[M].北京:中華書局,2013.
④魯禮鵬,玉素甫,馬金娥,等.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考古發掘報告[J].考古與文物,2016(5):31-50.
⑤趙睿才,楊廣才.“紙錢”考略[J].民俗研究,2005(1):115-129.
⑥⑧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王曉波,李勇先,張保見,等,點校.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⑦劉昫,等.舊唐書:卷48[M].北京:中華書局,1975.
⑨李曉岑,鄭渤秋,王博.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古紙研究[J].西域研究,2012(1):62-68,143.
⑩p李征.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1963—1965)[J].文物,1973(10):7-27,82.
km陸錫興.吐魯番古墓紙明器研究[J].西域研究,2006(3):50-55,119.
ln李肖,張永兵,張振峰.新疆吐魯番地區木納爾墓地的發掘[J].考古,2006(12):27-46.
o余欣.冥幣新考:以新疆吐魯番考古資料為中心[J].世界宗教研究,2012(1):172-181,194.
q司馬光.司馬氏書儀:卷7[M].北京:中華書局,1985.
r黎靖德.朱子語類:卷89[M].北京:中華書局,1986.
s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集[M].影印本.[出版信息不詳].
t戴埴.鼠璞: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