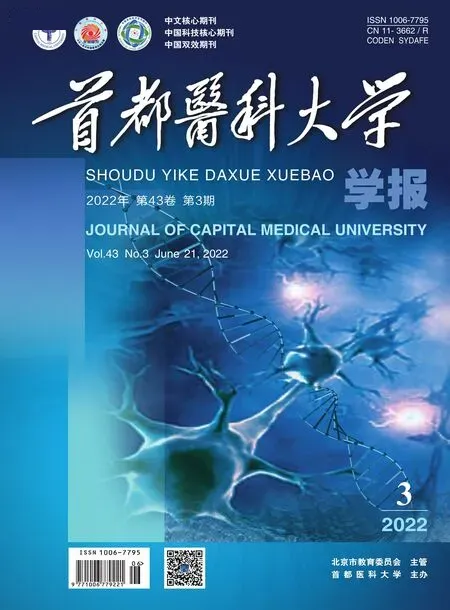2010年和2019年雙相情感障礙住院患者的臨床特征和未治療持續時間的因素分析
劉珊珊 房 萌 朱 虹 尹冬青 趙 燕 趙 爽 賈竑曉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 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精神疾病診斷與治療北京市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088)
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BD)是一種病因未明的高度異質性疾病[1-2],包括一些閾下障礙,影響全球約2%的人口[3-4]。BD至今仍是對個體(尤其是年輕人群)和社會造成重大負擔的精神疾病之一[5]。盡管人們從疾病基因學、行為學、生理病理學、影像學等角度對此病進行了相當多研究,但仍未取得進展[3, 6-8]。當前針對BD的診斷和治療仍然主要依賴于現象學特征和疾病自身發展特點,所以找到準確的臨床資料尤為重要。在臨床實踐中,很難預測BD的發病,原因一方面是疾病早期癥狀包括抑郁、輕躁狂或混合癥狀,有時與正常的情緒波動難以區分;另一方面部分BD患者癥狀隱匿、不典型,或伴有精神病性癥狀,也容易被忽視或不被正確識別。此外,很多BD患者以抑郁癥狀首發,且抑郁期的發生頻率高于輕躁狂或躁狂期[9],尤其是BD Ⅱ型,患者大多數時間處于抑郁期,臨床醫生常常會忽略輕躁狂病史。以上因素都可導致BD的高誤診率、漏診率,導致對BD不恰當的診斷和治療時間的推遲。
BD的未治療持續時間(duration of untreated bipolar disorder,DUB)是對BD病程和預后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之一[10-11]。有研究[12-14]表明過長的DUB在心境不穩定、抑郁/輕躁狂發作頻次增加、更多的殘留癥狀和自殺行為、更多的住院概率和后續的社會功能障礙方面顯示出長期不利影響。無論是在疾病急性發作期還是長期預后,對DUB提高重視、及時診斷和有效干預會讓BD患者直接獲益。國內針對BD的DUB的研究不多。國外研究[10, 15-16]DUB數值在6~20年不等,而最近在中國進行的一項關于DUB的多中心研究[9]顯示中國BD患者的平均DUB時間為3.2年,也有報告[17]顯示是6年。為進一步探索,本課題組收集了2010年和2019年BD住院患者的病歷資料,比較不同年代的BD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及可能影響DUB長短的相關因素,以期為臨床提供更多指導。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來自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的住院患者,根據本院電子病歷的運行時間及防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住院患者的影響,本研究分別選取了2010年和2019年的住院患者。入院時間為2010年4月至8月、2019年4月至6月。根據電子病歷記錄,納入的患者均經過三級醫師查房,且依據《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10次修訂版[18]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對于反復住院的患者以最近一次住院資料為準。排除物質濫用或依賴、伴發嚴重軀體疾病、軀體疾病所致情感障礙、住院時間過短、臨床資料不全且無法聯系患者及家屬進行核實的病例。
2010年納入患者302例,其中男性130例,女性172例,年齡13~59歲,平均年齡(32.3±12.7)歲,總病程(9.1±9.4)年。2019年納入患者328例,其中男性130例,女性198例,年齡12~59歲,平均年齡(32.8±11.3)歲,總病程(8.9±7.6)年。
所有采集的數據會嚴格保密,僅限于本研究使用。本研究已通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批件號:(2019)科研第(90)號]。作為歷史性研究可免除研究對象知情同意。
1.2 資料收集
由2名主治或以上級別的精神科醫師調閱電子病歷,對符合要求的住院患者,用自制的調查表采集患者相關資料。如果住院材料不夠完整,可直接電話向患者和直系親屬核實,同時結合患者在本院或外院的所有病歷記錄,以盡量保證收集資料的準確性。
1.3 DUB的定義
國際上對于DUB的定義并未得到廣泛共識,本研究借鑒既往研究[17, 19]將DUB定義為BD患者首次出現情緒發作到首次使用心境穩定劑(丙戊酸鹽、鋰鹽、拉莫三嗪、卡馬西平)治療時的時間間隔。以月為單位,記錄每位入組患者的DUB數值。結合國內外報道[9, 19],將DUB平均界值定為3.5年,以此將患者分為較短DUB組(short-DUB,S-DUB<3.5年)和較長DUB組(long-DUB,L-DUB≥3.5年),并探討不同年代中影響DUB長短的相關因素。2010年,S-DUB組和L-DUB組各151例;2019年,S-DUB組189例,L-DUB組139例。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定量數據以M(P25,P75)表示,組間中位數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如Mann-WhitneyU檢驗。定性資料組間率比較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篩選L-DUB相關的因素。采用雙側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年代BD住院患者臨床特征比較
兩組患者臨床特征比較結果顯示,與2010年的患者相比,2019年BD住院患者的整體受教育程度、來自于其他省份的患者比例、伴自殺觀念/行為的患者比例及患者服藥的依從性均較高,而住院時間、DUB明顯縮短,總的住院次數增多,伴精神病性癥狀的患者比例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不同年代BD住院患者的人口統計學資料及臨床特征比較Tab.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data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inpatients with BD in different years [M(P25,P75),n(%)]
2.2 不同年代影響DUB長短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分別以2010年和2019年患者DUB的長短為因變量(長=1,短=0),2010年以居住地、婚姻狀況、總病程、首發癥狀、首次(輕)躁狂年齡、首次確診年齡、總住院次數、總發作次數、抑郁次數、躁狂次數、混合次數、精神病性癥狀、服藥依從性為自變量;2019年以婚姻狀況、總病程、首發癥狀、首次(輕)躁狂年齡、首次確診年齡、抑郁次數、躁狂次數、季節性特征為自變量,分別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結果顯示,2010年未婚、病程長、首發抑郁癥狀、住院次數少、躁狂次數少是L-DUB的影響因素(P<0.05),詳見表2。

表2 與L-DUB相關的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2010年)Tab.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lated to L-DUB(2010)
2019年病程長、首發抑郁癥狀、首次躁狂時年齡偏小、首次確診BD時年齡偏大是L-DUB的影響因素(P<0.05),詳見表3。

表3 與L-DUB相關的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2019年)Tab.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lated to L-DUB(2019)
3 討論
本文分析了2010年和2019年BD住院患者的一般資料特征、臨床特征及可能影響DUB長短的因素。結果顯示隨著年代的發展,BD住院患者的受教育水平逐漸增加,來自除北京外其他省份的患者增多,提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進步,精神衛生問題日益得到民眾和社會的重視。在臨床特征方面,筆者發現BD患者的住院時間顯著縮短、總住院次數顯著增多,這與近十年來BD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與重視有關。其次,隨著BD診斷標準的不斷細化、治療理念不斷更新,包括無抽搐電痙攣治療的普及和完善,有助于盡快幫助患者度過急性期、縮短住院時間。而伴有精神病性癥狀患者比例的顯著減少也體現了治療干預手段的進步,盡早識別及對癥治療可預防疾病朝著更嚴重的方向發展, 避免癥狀進一步惡化[20-21]。雖然跟十年前相比,患者整體的服藥依從性有明顯的提高,但表現良好的患者比例卻增加有限,提示仍需在患者群體、家屬群體,甚至普通人群中提高精神衛生健康宣教,在國家層面上繼續加強公共衛生政策制定,進一步改善患者服藥治療的積極性。
根據流行病學研究數據,BD患者自殺企圖的終生風險約為29.2%[22],大約1/3到1/2的BD患者至少有一次試圖自殺的行為[23]。產生自殺觀念/行為的原因比較復雜,涉及生物學機制、精神狀態不穩定、家族史、社會環境因素等。BD患者自殺風險增高的原因除去生物學因素外,推測可能與長期的家庭、社會壓力和不良的生活事件所致的心境不穩定相關,尤其在現代社會。
此外,與預期一致的是,隨著年限的增加,BD住院患者的DUB明顯縮短,從縱向維度看,體現了精神衛生事業的進步。從橫向維度看,本研究得出的DUB數值短于國外的數據[14],但與國內報道[9]接近。這可能與DUB的定義不同、不同診療機構和醫生對BD的識別能力存在差異、雙相類型以及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有關[9, 14, 17, 24]。
研究[12]證實L-DUB是BD消極預后的因素之一,并且與住院頻率增加、癥狀更嚴重、自殺嚴重程度更高和較差的社會經濟狀態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現在還是十年前,以抑郁癥狀首發、病程長均與L-DUB相關。相對于首發癥狀為躁狂、混合狀態的患者,抑郁癥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較小,就診時間更容易被拖延。在抑郁發作的背景下很大一部分患者并未被正確診斷(尤其是BDⅡ型),造成L-DUB的潛在風險。病程長短與DUB的相關性也得到其他研究[10, 25]的支持,有報道[25]顯示BD的誤診率可高達69%,且通常在疾病第一次發作后5到10年才會確診,DUB的延長影響患者的臨床穩定性且促進病程的延長。而病程越長的患者年齡可能越大,在BD發病早期難以得到有效規范的診療,導致L-DUB,這與早期的研究[10]一致。
在調查與DUB顯著相關的其他變量中發現婚姻狀況類型對BD患者的結局有可變影響,有研究[26]顯示存在婚姻關系與L-DUB相關,但本研究顯示了不同的結果,已婚狀態的患者可能更加注重健康狀況,也有利于伴侶及時發現異常盡早就診,能夠為醫生提供較為客觀的資料,進而縮短DUB。但在2019年的數據中,筆者沒有發現該相關性,提示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婚姻觀念的改變會影響DUB。與既往研究[13]一致,在2010年的數據中筆者發現住院次數和躁狂次數越少越容易導致L-DUB。考慮到輕中度的抑郁或輕躁狂通常被患者及家人視為正常狀態,即使出現嚴重抑郁也容易忽視對BD的甄別,直到出現明顯躁狂時產生危害社會的行為,才會引起重視或送住院,造成L-DUB。在2019年,躁狂首發時年齡偏小、首次確診BD時年齡偏大都是L-DUB的有利因素,原因可能是躁狂發作年齡越小,癥狀可能越不典型(沖動、情緒不穩、激越),且處于輕躁狂的個體并不積極尋求治療,造成診斷失敗。此外,早在BD確診之前患者可能已經接受過一系列針對癥狀的非藥物或藥物干預,療效欠佳、病情反復及對治療的偏見促使DUB延長。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樣本資料的采集來自于同一家精神專科醫院,患者大多數局限于北京及周邊省份,不能代表全國的精神衛生水平。其次,不同年代納入的患者的入院時間不嚴格一致,但大部分集中在4月至6月,可能會對某些變量,如季節性特征造成混雜影響。最后,病史資料均是家屬的主觀表述,不能完全保證真實的發病過程,在有限的病歷資料記錄中有時也難以界定具體的癥狀。
總之,隨著年代的發展,BD患者的DUB明顯縮短。首發抑郁癥狀、病程長是2010年和2019年L-DUB的相同影響因素。應重視DUB及相關因素,提高對BD的甄別和正確診斷,努力縮短DUB,為早期干預提供時機以改善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