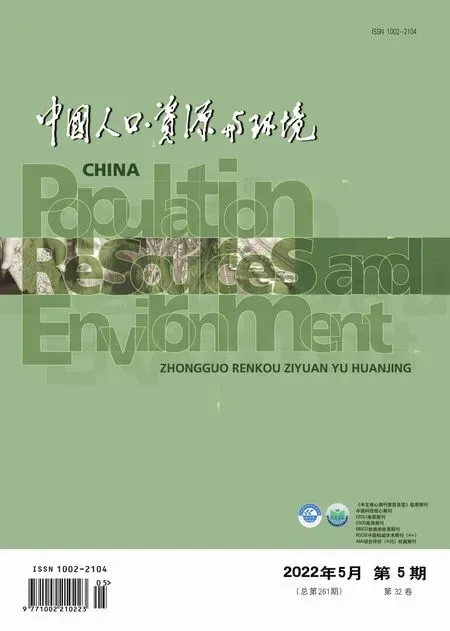基于不同生計類型的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測度與影響機理
劉愿理,廖和平,蔡拔林,石永明,邱繼勤
(1. 重慶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0067;2. 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重慶 407407;3. 重慶市九龍坡區銅罐驛鎮人民政府,重慶 400050;4. 重慶工商大學經濟管理實驗教學中心,重慶 400067)
2021 年2 月25 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布,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標志著中國歷史性地消除絕對貧困,農村貧困進入了相對貧困階段[1]。針對農村貧困問題重心轉移,中國政府提前謀劃部署,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這為新時期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指明了方向,標志中國農村貧困問題從收入貧困治理轉向多維貧困治理,從集中式減貧轉向常規化減貧。較絕對貧困而言,相對貧困治理從解決人的生存問題轉向了關注人的發展問題,覆蓋范圍和貧困維度更廣,致貧因素更復雜,導致絕對貧困評價體系和標準已不能適應相對貧困問題。因此,探討農村相對貧困,尤其聚焦不同生計類型農戶的相對貧困狀況,探究影響機理,對構建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20 世紀70 年代,英國學者Townsend 首次提出了相對貧困概念,為貧困內涵增添了社會屬性。阿瑪蒂亞·森引入了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完善了相對貧困概念,并提出了測算相對貧困的方法。部分學者進一步拓展了相對貧困的內涵。李英坤[2]從自然資源與物質條件是否達到社會公認的基本生活水平,凌經球[3]是否能夠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務,Evcim等[4]是否有同等就業機會,到吳國寶[5]和楊力超等[6]是否可以公平接受教育等。隨后,有學者引入多維相對貧困概念,王曉林等[7]從“貧”和“困”兩個層面梳理了相對貧困多元化的內涵,劉愿理等[8]、Ward等[9]和汪三貴等[10]為新時期農村相對貧困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時,多維貧困理論具有綜合性、動態性特征,涉及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生態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逐步形成了多學科、多視角的評價指標體系,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熱點[11]。因此,文章基于多維貧困理論探討農村相對貧困問題更具科學性[11]。
農戶生計是農戶個人或家庭謀生的方式,它取決于個人或家庭的資產、從事的生產活動以及從事生產活動所具備的能力[12],將影響農戶個體或家庭的生活水平、發展機會和可行能力。學術界關于不同生計類型農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計可持續性[13]、土地利用[14]、家庭能源消費[15]等方面。蔡進等[16]探討了不同生計類型農戶易地搬遷意愿及影響因素,李靖等[17]貧困農戶生計資本、生計方式和生計效率的個體和空間差異性。但是,2020 年后關于不同生計類型農戶脫貧或相對貧困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把握不同生計類型農戶行為策略的規律性和差異性,探究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程度及其影響機理,對于農村相對貧困治理至關重要。
國內外學術界關于農村相對貧困的研究成果頗多,主要集中在標準、評價指標體系、影響因素等方面,但是基于多維度、分類型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農村相對貧困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可能存在拓展空間:一是基于多維視角研究農村相對貧困問題,目前農村相對貧困標準主要以收入單一維度,未能體現多維貧困思想;二是探究不同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狀況,分門別類劃定標準和識別影響因素更具適用性和科學性;三是深入剖析不同生計類型農戶相對貧困影響機理,為針對性地制定治理措施提供科學依據。基于此,文章從不同生計類型農戶視角出發,以貴州省天柱縣為研究區域,以5 502 戶樣本農戶為研究對象,基于多維相對貧困理論,構建農村多維相對貧困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多維相對貧困測度模型、Dagum 基尼系數和地理探測器識別不同生計類型相對貧困戶,探究影響因素,剖析相對貧困形成機理,為提高農村相對貧困治理效率和構建長效機制提供科學參考。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與驗證
天柱縣地處貴州省東部黔東南州,全縣下轄3 街道11 鎮2 鄉117 個 行 政 村,2020 年 全 縣 戶 籍 人 口41.91 萬人,其中城鎮戶籍人口16.29 萬人,農村戶籍人口25.62人,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8.20%,是中國典型的少數民族地區。天柱縣作為2012 年國務院確定的832 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縣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2014 年全縣共有28 606 戶建檔立卡貧困戶,貧困發生率為25.66%,到2020 年貧困人口全部消除。因此,文章選取天柱縣為研究對象,結合已有研究成果[18],按照“村-組-戶”多階段抽樣方法,于2020 年1 月和7 月先后組織60名調查員前往研究區開展預測問卷和正式問卷調查工作。文章樣本量覆蓋研究區全部鄉鎮和行政村,抽樣調查5 735 戶農戶,其中有效樣本量5 502 戶,問卷有效率達到95.94%。為了確保問卷和數據的科學性,文章進行預測問卷和正式問卷調查,測算問卷信度和效度,以期達到研究要求[19]。結果顯示,文章量表整體信度達到0.735,各子量表均大于0.700,樣本數據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達到0.754(大于0.6),Bartlett 球形度顯著(P<0.05),符合科學研究要求[20-21]。
2.2 農戶類型劃分
梳理國內外研究成果,農戶生計類型劃分形式多樣,尚未形成明確的分類標準,學者根據不同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劃分不同農戶生計類型。常用的方法是以農戶生計方式、就業狀況、經濟狀況和農戶屬性來劃分農戶類型[22-23]。因此,文章借鑒現有研究成果,根據農戶生計方式、經濟來源等因素,將農戶分為傳統務農型、外出務工型、兼業型和政府兜底型。其中,傳統務農型農戶為務農(種養殖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60%,外出務工型農戶為外出務工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60%,兼業型農戶為務工和政府補貼收入均小于50%,但都兼有,政府兜底型農戶為政府各類補貼占總收入的比例≥60%。
2.3 研究方法
(1)多維相對貧困測度模型。文章借鑒多維貧困測度方法,從單一收入維度轉向自然、經濟、能力、機會和社會等多維度,構建多維度視角下的相對貧困測度模型,測算研究區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RPI)。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n 為維度個數;m 為相應維度下的指標個數;Fij為標準化后的指標值;Wij為指標權重;Wi為維度權重。
(2)Dagum基尼系數驗證。Dagum將基尼系數分解為群內差距貢獻、種群之間超變凈值差距貢獻和群體間超變密度貢獻3 個組成部分[24]。因此,文章借助基尼系數測算群體組間差異的優勢,驗證抽樣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中位數40%、50%、60%和70%結果的差異性,確定研究區農村相對貧困戶的標準。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Gjh表示j和h兩個群體之間的組間差距,其值越大表示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化程度越大;nj和nh表示j和h兩個群體的戶數;yji和yhr分別表示j(h)類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Yˉj和Yˉh是j和h兩個群體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均值,n是農戶總數。
(3)地理探測器模型。地理探測器打破傳統回歸分析方法的局限,無須設置過多假設條件,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等影響因素研究[25]。因此,文章借助地理探測器模型[26],引入多維相對貧困決定力指標q,通過分異及因子探測工具探測各指標對相對貧困的影響。各指標對多維相對貧困的決定力大小為:

式中:nh為因素B 的類型h(對應一個或多個子區域)內的樣本數;n 為在整個研究區所有樣本數;σ2為整個區域的離散方差,當維度對相對貧困具有決定力時,每個類型(對應一個或多個子區域)的離散方差σ2會較小,類型(對應一個或多個子區域)之間的離散方差會較大。
3 結果分析
3.1 多維相對貧困戶識別
3.1.1 指標體系
農村多維貧困測度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實現了多學科、多角度交叉融合,呈現多元化特征。因此,文章基于多維貧困理論,根據已有研究成果[27-28],結合發展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和可持續生計框架模型等,構建了農村多維相對貧困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指標體系主要由物質資源、經濟條件、可行能力、發展機會、社會保障和內生動力6 個子系統組成,通過R 聚類-變異系數方法篩選30 項指標候選集,運用SPSS10.7軟件進行線性分析,剔除共線性指標,最終確定了22 個度量指標(表1)。文章選取指標既有正向指標,又有負向指標,因此選擇采用極差標準化法對各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達到研究需求。同時,指標權重確定基于博弈論思想,結合層次分析法和熵權法的優點,確定一個最能接近實際情況的指標權重值,提高研究結果的穩健性和科學性[29]。
3.1.2 多維相對貧困指數
運用多維相對貧困測度模型,測算研究區5 502 戶抽樣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其值越小表征相對貧困程度越深。研究結果顯示,天柱縣農戶多維相對貧困程度較深,差異性較大。其中,外出務工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低,兼業型和傳統務農型農戶次之,政府兜底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高(表2)。具體而言,外出務工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平均值為0.61,除了物質資源和可行能力外其他維度相對貧困指數均高于其他類型農戶,物質資源和可行能力維度相對貧困指數與傳統務農型農戶基本持平。兼業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為0.58,僅次于外出務工型農戶,6 個維度相對貧困指數均低于外出務工型。傳統務農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為0.57,與兼業型農戶基本持平,其中物資資源和可行能力維度相對貧困指數較大。政府兜底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深,相對貧困指數平均值較小,只有外出務工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的62.30%。

表1 農村多維相對貧困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3.1.3 多維相對貧困標準劃定
基于多維視角構建農村相對貧困評價指標體系,測算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以指數中位數比例值劃定農村相對貧困標準,識別相對貧困戶。因此,文章基于汪三貴、孫久文等研究成果[10,30],分別選取40%、50%、60%和70%等4 個值作為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中位數比例值將農戶分為兩個組,運用Dagum基尼系數分別驗證4種比例值劃分群體的組間差距(表3)。組間差距越大兩組群體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相差就越大,說明選取的比例值更具合理性,從而確定研究區農村相對貧困標準[23]。
從4種方案測算和驗證結果來看,方案一的測算結果與研究區實際情況不符,直接舍棄,不做Dagum 基尼系數驗證。方案二、方案三和方案四的Dagum 基尼系數驗證結果顯示,組間差距系數略大的是方案三。同時,根據研究區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和發展目標,最終選取60%作為研究區多維相對貧困指數中位數的比例值。

表2 不同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測度結果
3.1.4 多維相對貧困戶識別結果
基于多維相對貧困劃定方法,研究區5 502 戶樣本農戶中共識別655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11.90%。其中,傳統務農型農戶共識別223 戶相對貧困戶(表4),相對貧困發生率為19.54%,貧困發生率較高,僅次于政府兜底型農戶。外出務工型農戶共識別44 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2.46%,在所有類型農戶中相對貧困發生率最低,進一步說明了外出務工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較低。兼業型農戶共識別108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5.21%)僅高于外出務工型農戶。政府兜底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高,共識別280 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56.00%,遠高于其他三種類型農戶,說明低保戶、五保戶等特殊群體自身發展不足,需要政府兜底才能得以實現脫貧,是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應該重點關注的群體。
3.2 影響因素分析
3.2.1 影響因素變量篩選
農戶多維相對貧困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主要是內生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31-32]。因此,文章選擇個人因素、文化素質和經濟因素3 個維度9 個指標表征內生性影響因素,資源稟賦、地理區位和政策因素3 個維度9個指標表征外源性影響因素(表5)。
3.2.2 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影響因素分析
(1)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地理探測器探測結果顯示,共有10 個因素與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在不同水平下具有顯著性,其中4 個內生性因素,6 個外源性因素,決定力前四的均為外源性因素(表6)。具體而言,從內生性因素來看,家庭成員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決定力最大,為0.191,其次是家庭是否有黨員干部和生產發展意愿,決定力分別為0.168、0.106,農戶類型決定力較小,僅為0.095。其他4個指標未通過顯著性驗證。從外源性因素來看,資源稟賦對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大,其中海拔高程和人均耕地面積的決定力分別為0.301 和0.337,均在1%水平下顯著。地理區位中,到村組干道距離對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的影響較大,決定力為0.172,到鄉鎮政府距離的決定力為0.132,兩者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政策因素中,政策性貸款和產業幫扶的決定力較大,分別為0.312 和0.218,均在1%水平下顯著。其他因素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3 研究區不同相對貧困標準的驗證結果
(2)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研究結果顯示,內生性因素對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大,共有6個指標顯著,外源性因素共有5 個指標,而決定力前五的均為內生性因素(表7)。具體而言,個人因素中僅有家庭是否有黨員干部通過了顯著性驗證,決定力為0.316。文化素質中,3 個指標均與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呈現顯著性,決定力分別為0.304、0.101、0.271,均在1%水平下顯著。經濟因素中,生產發展意愿對相對貧困戶的影響最大,為0.460,土地流轉收入的決定力為0.161,兩者均在1%水平下顯著。戶主年齡、農戶類型、轉移性收入的影響不顯著。資源稟賦中僅有海拔高程對相對貧困戶的影響存在顯著性,決定力為0.230,其他指標未通過檢驗。地理區位對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大,3 個指標均顯著,決定力分別為0.255、0.171 和0.211。政策因素的產業幫扶對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決定力為0.104,政策性貸款和扶貧政策滿意度兩個指標未通過顯著性驗證。

表4 不同類型農戶相對貧困戶數統計表
(3)兼業型相對貧困戶。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的主導因素共有10個,其中5個內生性因素,5個外源性因素(表8)。具體而言,從內生性因素來看,家庭是否有黨員干部對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的決定力為0.188,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家庭成員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成員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決定力分別為0.245、0.096。經濟因素中土地流轉收入和生產發展意愿的決定力分別為0.186、0.376,均在1%水平下顯著。但是,是否少數民族家庭、戶主年齡、農戶類型和轉移性收入占比3個指標未通過驗證。從外源性因素來看,人均耕地面積對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大,決定力為0.497,海拔高程的決定力0.225,兩者均通過驗證,人均安全住房面積不具有顯著性。地理區位對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小,僅有到鄉鎮政府距離顯著,決定力為0.127,到村組干道距離和到村委會距離均不存在顯著性。政策因素中產業幫扶和政策性貸款的決定力分別為0.419、0.166,扶貧政策滿意度沒有通過顯著性驗證。

表5 研究區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評價指標體系

表6 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探測分析
(4)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研究結果表明,個人因素、經濟因素和政策因素中的指標對其影響較大,共有7個指標存在顯著性(表9)。具體而言,個人因素中戶主年齡和農戶類型對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具有顯著性影響,決定力分別為0.204 和0.257,家庭是否有黨員干部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文化素質對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小,3個指標均未通過顯著性驗證。經濟因素對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較大,尤其是轉移性收入占比和土地流轉收入,決定力較高,分別為0.302、0.248,生產發展意愿的決定力為0.187,三者均在不同水平下顯著。資源稟賦和地理區位中的海拔高程、人均耕地面積和到鄉鎮政府距離等6 個指標對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的影響沒有通過驗證,不具有顯著性;政策因素中,政策性貸款和產業幫扶對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的決定力分別為0.108 和0.194,分別在5%和1%水平下顯著,扶貧政策滿意度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3.3 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形成機理分析
(1)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研究區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主要以外源滯后型為主,資源稟賦、政策支持和地理區位是影響農戶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因素(圖1)。傳統務農型農戶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資源、氣候、生產技術等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以獲取生產生活必需品。天柱縣耕地資源較少,耕地破碎度較高,利用方式粗放,尤其是高海拔地區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導致相對貧困戶農業生產效率較低,農業生產主要以小規模粗放式經營為主。產業帶動效果有待提升,69.93%的合作社帶動農戶僅簡單分紅。到鄉鎮政府距離和到村組干道距離說明農村基礎設施有待完善,特別是生產便道和村組公路較為突出。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主要依靠家庭生產實現自給自足,申請國家政策性貸款的積極性不高,金融資本未能撬動農村市場和激活農村經濟。家庭成員最高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較短,導致相對貧困戶文化水平較低,獲得發展的機會較少,限制了相對貧困戶生產發展意愿。

表7 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探測分析結果

表8 兼業型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探測分析
(2)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研究區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主要以內生滯后型為主,可行能力、教育水平、產業發展帶動和政策激勵是影響天柱縣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主導因素(圖2)。研究表明,家庭成員最高受教育程度、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是否少數民族家庭3個主導因素表明研究區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文化水平較低,自身能力和發展意識相對較差,個別少數民族交流溝通能力有待提升。個人因素和文化素質導致農戶生產發展意愿不強,務工時間較短,務工收入較低,發展機會較少,家庭承包土地流轉收入成為了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但是土地流轉收入僅是外出務工型農戶的35.78%,大部分耕地撂荒,導致滿足該類農戶生活和發展的物質資源匱乏,從而陷入相對貧困狀態。同時,海拔高程和到鄉鎮政府、村委會距離反映務工政策宣傳至關重要,偏遠地區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對政策了解不夠到位,享受激勵措施較少。

表9 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探測分析

圖1 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影響機理
(3)兼業型相對貧困戶。兼業型農戶家庭成員分別從事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或間歇性務農和務工,家庭相對貧困程度主要受務農和務工兩個方面影響,兼具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和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特征,屬于內生外源滯后型(圖3)。
研究表明,資源稟賦將影響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的農業生產活動,人均耕地面積作為發展農業生產載體,是該類農戶處于相對貧困的主導因素,而海拔高度抑制了農業生產水平和效率。產業幫扶效果和政策性貸款執行有待提高,以解決農戶產業發展技術和資金難題,推動產業發展,增加農戶收入。文化素質影響兼業型農戶生產方式的選擇,導致家庭之間在經濟條件、發展機會和可行能力等存在差異,也將影響農戶發展意愿和積極性。同時,土地流轉收入、生產發展意愿和到鄉鎮政府距離將通過經濟收入、社會保障、內生動力等影響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總體來看,農戶自身能力較差、文化水平較低、產業發展緩慢、主動發展意識較弱和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強,這五個方面是影響兼業型相對貧困戶的主導因素。

圖2 研究區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影響機理

圖3 研究區兼業型相對貧困戶影響因素分析
(4)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研究區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以內生滯后型為主,社會保障、政府幫扶和收入持續性等對解決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至關重要(圖4)。政府兜底型農戶主要由低保戶、五保戶等特殊家庭組成,大部分屬于絕對貧困臨界戶或監測戶,是相對貧困程度較深的群體。研究結果表明,土地流轉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占比反映天柱縣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收入結構單一,可持續性不強,主要依靠國家各類補貼,自身條件較差,但國家補貼僅能維持基本生存,農戶實現美好生活的目標難度較大。生產發展意愿說明個別農戶內生動力不足,可能存在“等靠要”思想。戶主年齡和農戶類型是該類型相對貧困戶的主導因素,年滿60 周歲即可領取五保金,低保家庭均有國家補貼,但社會保障僅能實現基本生活,存在被剝奪現象。政策性貸款和產業幫扶突顯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但脫離國家幫扶措施則將陷入絕對貧困中,可行能力和發展機會剝奪嚴重,物質資源僅能滿足生存所需,全面發展嚴重受阻,陷入相對貧困的風險較高。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文章從不同生計類型農戶視角出發,基于多維相對貧困理論,運用多維相對貧困測度模型、Dagum 基尼系數和地理探測器等方法,識別研究區不同類型相對貧困戶,深度剖析相對貧困戶致貧原因,探究影響因素相互作用,研究結論如下:
(1)研究區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程度較深,差異性較大。其中,外出務工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低,兼業型和傳統務農型農戶次之,政府兜底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高。具體而言,外出務工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平均值為0.61,政府兜底型農戶相對貧困程度最深,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僅為外出務工型農戶的62.30%,兼業型和傳統務農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基本持平,分別為0.58、0.57。
(2)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識別。運用Dagum 基尼系數驗證了以多維相對貧困指數中位數的60%識別不同生計類型相對貧困胡的標準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研究結果表明,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最多,其次是傳統務農型和兼業型,外出務工型最少,這與前文的研究結果一致。具體而言,傳統務農型農戶共識別223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為19.54%,外出務工型農戶共識別44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2.46%,兼業型農戶共識別108 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5.21%,政府兜底型農戶共識別280戶相對貧困戶,相對貧困發生率高達56.00%。
(3)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影響因素差異較大。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主要以外源滯后型為主,其中資源稟賦、政策支持和地理區位是影響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4 個內生性因素和6 個外源性因素。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主要以內生滯后型為主,涉及6 個內生性因素和5 個外源性因素。兼業型農戶兼具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和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特征,屬于內生外源滯后型,包括5 個內生性因素和5 個外源性因素。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主要以內生滯后型為主,主要有5 個內生性因素和2 個外源性因素,社會保障、政府幫扶和收入持續性等對解決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至關重要。
4.2 建議

圖4 研究區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影響機理
基于研究區不同生計類型農戶多維相對貧困程度和影響機理分析結論,分別提出以下建議:①構建“一個中心三個著力點”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治理模式,以產業發展為中心,以支農惠農政策、轉變教育理念和模范作用為著力點,全方面多角度解決傳統務農型相對貧困戶物質、經濟、能力、機會、保障和內生動力等問題,以期為地方政府培訓新型職業農民提供借鑒。②構建“雙核心雙動力”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治理模式,以能力提升和教育扶貧為雙核心,提高外出務工人員的可行能力和綜合素質,增加發展機會,解決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內生性影響因素,以產業帶動和激勵措施為雙動力,增加農戶土地流轉收入,實現轉移性就業,解決外出務工型相對貧困戶的外源性影響因素。③構建“N+1”的兼業型相對貧困戶治理模式,通過技能培訓、發展產業、轉移就業、發放獎補、激發動力、黨支部引領等N 項措施解決兼業型相對貧困戶全面發展1 個中心問題。④構建“三管齊下”的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治理模式,即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轉變幫扶方式和拓展收入渠道,解決政府兜底型相對貧困戶生活保障、內生動力和收入持續性等問題,共享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