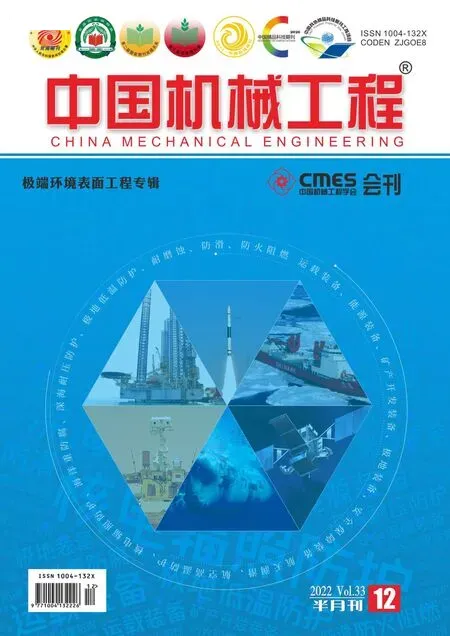激光熔覆工藝參數對鐵基雙層涂層組織和殘余應力的影響
周嘉利 程延海 陳永雄 梁秀兵 白成杰 杜 望
1.中國礦業大學機電工程學院,徐州,2211162.軍事科學院國防科技創新研究院,北京,1000713.徐州華恒機器人系統有限公司,徐州,221137
0 引言
在極端環境中服役的重型設備廣泛應用于資源開采、基礎建設和海洋開發等領域,它們具有設計周期長、造價高、零件易損壞的特點,因此,基于再制造技術的重型設備循環利用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1-2]。激光熔覆因具有高精度、高效率、低污染和低成本的優點而被廣泛應用于裝備表面強化和再制造[3-4]。研發基于激光熔覆的盾構機刀圈表面強化及再制造技術具有重要意義[1,5]。
激光熔覆技術在盾構機刀圈再制造領域應用的主要難題是熔覆層具有高裂紋敏感性[1]。激光熔覆的急冷特性和耐磨粉末的高硬脆性使得熔覆層具有較大的殘余應力,適當的殘余壓應力可以抑制涂層內裂紋的擴張,而殘余拉應力和過大的壓應力都會導致裂紋產生,進而影響涂層的成形質量[6]。因此,探究激光熔覆過程中殘余應力的產生和演變機理,并通過調控熔覆工藝控制涂層的殘余應力分布實現高成形質量耐磨層的制備,具有重要工程應用價值。LIU等[7]采用三維模型分析了激光重熔對NiCrBSi涂層殘余應力的影響,結果表明重熔區域表現為拉伸殘余應力;LUO等[8]采用激光沖擊技術消除了涂層內部較大的殘余應力,并優化了涂層的微觀結構和力學性能;DAS等[9]發現激光重熔可以使涂層表面產生殘余壓應力,這抑制了裂紋的產生和擴張,從而顯著降低了涂層的裂紋密度。
目前,對激光熔覆層殘余應力和缺陷控制的研究集中于熔覆工藝對單層涂層成形質量和機械性能的影響[10-13],但對于大型裝備的再制造修復,涂層需要多層多道激光熔覆,相比于單層熔覆層,多層涂層在逐層堆積過程中會出現應力累積現象,使其具有更高的開裂敏感性[14]。本文采用激光熔覆技術制備了Fe基雙層多道涂層,研究了熔覆路徑、激光功率和掃描速度對涂層顯微組織、力學性能和殘余應力的影響規律,為盾構機刀圈表面強化和再制造修復的激光熔覆參數選擇和路徑規劃提供理論指導和數據支撐。
1 試驗方法
1.1 試樣制備
基體材料采用Q345鋼,熔覆材料為Fe基合金粉末,其化學成分如表1所示。

表1 基體與Fe基粉的化學成分(質量分數)
在激光熔覆前,基板經過砂紙打磨除銹和酒精沖洗;粉末采用101-00B型電熱鼓風干燥箱進行100 ℃-2 h的烘干處理。采用YLS-4000型光纖激光器進行熔覆層制備,激光器的輸出波長為1070~1080 nm,光斑為直徑3 mm的圓形光斑,搭接率為50%,送粉速度為1.8 r/min。共制備9組試樣,其工藝參數如表2所示。

表2 激光熔覆參數設計方案
1.2 表征方法
采用320~2000號的砂紙對涂層斷面進行打磨,并用拋光布進行拋光。采用王水(15 ml HCl+5 ml HNO3)對涂層斷面腐蝕3~5 s,并用酒精沖洗后烘干。使用JE0L-6510型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其組織形貌。
采用華銀HVS-1000型硬度儀對試樣沿涂層深度方向進行硬度測量,施加力為5 N,作用時間為10 s,每間隔100 μm選取一個測量點,且在每個測量深度上測量3次取平均值。
采用X-350型X射線衍射儀測量涂層的殘余應力,儀器的測試精度為±20 MPa。測量時取熔覆面平整且質量較好的兩個位置進行測試,選擇入射角為0°、15°和35°,采用交相關函數法獲得殘余應力值與誤差值。殘余應力測試點位置如圖1所示。測量參數如下:輻射靶材為Cr-Kβ,衍射晶面為(311),應力常數為-366 MPa,X射線管電壓為24 kV,X射線管電流為7 mA,掃描角度為162°~148°,計數時間為0.25 s。

圖1 X射線殘余應力測試
電化學剝層試驗采用直流雙橋穩壓電源,基體的尺寸為70 mm×60 mm×20 mm,熔覆層的尺寸為40 mm×20 mm。圖2為電化學腐蝕剝層試驗臺的原理圖。采用直流穩壓電源,正極接銅板,負極接試樣,電解質選用飽和NaCl溶液。通過多次預試驗,選擇電壓為6.5 V,兩極間距為35 mm,腐蝕時間為120~150 min,預計每次剝除厚度為0.3 mm。

圖2 電化學腐蝕剝層原理圖
電化學腐蝕剝層的優勢是不會改變涂層內的應力場分布,但涂層結構的改變終究會引起小部分應力釋放。通過計算可以得到上一剝層對當前剝層殘余應力的影響,進而能夠對測得的殘余應力進行修正。圖3顯示了電化學剝層修正原理。設σx為試樣內部在x方向均勻分布的殘余應力,A、B表示基體和剝除層,H為試樣的剝除層總厚度,σ1為厚度Δh剝層中的內應力。在剝除層未剝除時,它與基體間存在拉力F=σ1Δh,剝層以后拉力可以分解為拉應力σF和彎曲應力σB[15]。

圖3 剝除層修正原理
由材料力學的相關知識可得
(1)
(2)
由式(2)可得
(3)
由于Δh非常小,所以式(3)可化簡為
(4)
又因為
(5)
所以剝除部分對剩余部分的影響可表示為
σm=σB+σF
(6)
第一層測量的應力不會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影響,第二層開始應力的實際值σi為測量值σc加上修正值σmi:
σi=σc+σmi
(7)
式中,i表示第i剝層,i=2, 3,…。
進一步分析可得
σi=σc+(σm(i,i-1)+σm(i,i-2)+…+σm(i,1))
(8)
式中,σm(i,i-1)為第i-1剝除層對第i層剝除層殘余應力影響的修正值。
剝除過程中某一剝除層對當前剝除層殘余應力影響的修正值計算公式為[15]
(9)
式中,k為正整數;Δhk為第k剝除層的厚度;j表示第i層之前的某一剝除層,j=1, 2,…,i-1;σm(i,j)為第j剝除層對第i層剝除層殘余應力影響的修正值;σm(j+1,j)為第j剝除層對第j+1層剝除層殘余應力影響的修正值。
根據式(9)可以得到之前每一剝除層對當前剝除層殘余應力的影響,代入式(8)即可得到未受電化學剝層影響的實際殘余應力值。
2 試驗結果與分析
2.1 微觀組織分析
圖4所示為試樣2的斷面形貌。涂層的厚度約為1.6 mm,表面堆積著少量未熔粉末顆粒。涂層斷面經過腐蝕,顯示出較為明顯的涂層-基體熔合線。涂層和基體間形成了高強度的冶金結合,且無明顯的裂紋、孔隙等缺陷,成形質量良好。由于圓形光斑的激光能量密度呈高斯分布,使得基體和涂層的結合帶是連續的波浪線型,這樣的結合界面在涂層受剪切力時可以阻礙界面發生滑移,有利于提高基體-涂層的結合強度。此外,從圖中未發現層與層之間有明顯的結合帶,這是由于兩層涂層的熔覆材料相同且層與層之間發生了重熔導致其宏觀形貌無差別。

圖4 試樣2涂層的斷面形貌
為探究掃描路徑對涂層厚度的影響,在每組試樣中取一個對照樣品,使用砂紙和金相磨拋機將樣品磨損至涂層-基體結合帶波浪線的中位線處。采用螺旋測微器測量該對照樣品厚度,測量3次取平均值作為基體厚度,未磨損樣品厚度減去基體厚度作為涂層厚度,測量結果如圖5所示。由于所選試樣的激光功率和掃描速度相同,故其厚度只與掃描路徑有關。在激光功率為1.8 kW和掃描速度為0.02 m/s時,路徑1和路徑2涂層的厚度接近,路徑3和路徑4涂層厚度相對較小。這是因為路徑1和路徑2均為直線往復式激光掃描,涂層厚度會線性累加。路徑3激光軌跡垂直交叉,打亂了涂層厚度的線性累積且涂層相對致密,導致涂層厚度較小。路徑4為輪廓偏置式激光掃描,使得熔池冷凝過程中內應力的方向是發散的,增強了涂層的致密性使得涂層厚度較小。

圖5 不同激光掃描路徑下各試樣厚度
以試樣2、8、9分析掃描路徑1、3、4對涂層微觀形貌的影響,見圖6,其中,圖6a、圖6b和圖6c所示分別為對應掃描路徑1、3、4的涂層頂部形貌。三組不同激光掃描路徑下涂層頂部顯微組織相似,晶粒細小且組織致密,涂層具有良好的成形質量及力學性能。相比于路徑1,路徑3和路徑4的晶粒生長方向具有多樣性,這是由于晶粒的擇優生長方向為最大溫度梯度方向。路徑3和路徑4的掃描方式避免了晶粒的同向生長,受到外部應力時可以阻礙晶界滑移,有利于提高涂層硬度。
圖6d、圖6e和圖6f分別對應掃描路徑1、3、4的涂層層間形貌。受液態熔池凝固特征、界面熔化特征等多方面的影響,相鄰層微觀組織分別呈現與掃描方向或搭接方向相對應的形貌特征。在路徑1中,兩層間的晶粒形貌及大小相似,但其生長方向略有不同。此外,兩層之間的熔合區顯微組織晶粒致密,這是由于層與層之間發生了重熔現象,激光束重復掃描使得層間組織進行了一次淬火導致晶粒細化。在路徑3中,由于兩層涂層的掃描路徑垂直交叉,涂層之間的晶粒生長方向有顯著差異,這是垂直交叉掃描路徑涂層的典型特征[16]。涂層晶粒生長方向沒有明顯的規律,這是由于該激光掃描路徑下熔覆材料逐層堆積成形過程中道與道之間、層與層之間搭接復雜。在路徑4中,偏置輪廓的掃描軌跡使得晶粒生長方向變為各向異性,兩層涂層熔合線兩側的組織形貌有顯著差異。由于激光熱源熱量的累積效應,在涂層層間的冶金結合處易形成氣孔、裂紋等缺陷。
圖6g、圖6h和圖6i分別對應掃描路徑1、3、4的涂層-基體熔合線處形貌。三種不同激光掃描路徑下,涂層熔合線處的顯微組織差異較小,基體與熔覆層均能形成良好的冶金結合,熔覆層和基體結合緊密,不容易脫落。三組熔覆層的涂層-基體熔合線區域均出現了平面晶,而后轉變為胞狀晶。在熔池凝固過程中,溫度梯度從熔池底部到涂層表面逐漸減小,在熔池底部溫度的降低是均勻的,基本保持穩定的平面狀,所以產生了平面晶。隨著界面的向上移動,溫度變化加快,同時伴隨著激光束沖擊、送粉氣吹拂以及未熔顆粒濺射的擾動,凝固界面轉變為非平衡態,因此產生了胞狀晶、樹枝晶和等軸晶[17]。

(a)路徑1涂層頂部形貌 (b)路徑3涂層頂部形貌 (c)路徑4涂層頂部形貌
圖7為微觀組織生長規律示意圖。涂層的微觀組織主要由溫度梯度(G)和晶粒生長速率(R)決定,G/R影響組織的形貌,GR影響晶粒大小[18]。在涂層-基體熔合線處,晶粒的形核屬于異質形核,這是因為均質形核的形核功ΔG1為[19]

圖7 微觀組織生長規律[17]
(10)
式中,ΔHm為熔化潛熱;σLS為固液界面張力;ΔT為過冷度;Tm為熔點。
而異質形核的形核功ΔG2為[19]
(11)
式中,θ為接觸角。
由式(10)和式(11)發現,當ΔG1≥ΔG2并且θ=0°時ΔG2=0,異質形核阻力小于均質形核阻力,故熔池液相會優先附著于基體固相形核;同時,熔池底部具有高的G/R,涂層-基體結合帶處晶粒形狀為平面晶。由結合帶到涂層頂部,G/R逐步減小,晶粒形狀發生如下變化:平面晶→胞狀晶→柱狀樹枝晶→等軸樹枝晶。
2.2 顯微硬度分析
圖8為激光掃描路徑1、2、3、4的涂層斷面顯微硬度分布曲線。由斷面硬度梯度可以將試樣分為涂層、熱影響區和基體,涂層硬度為499HV~634HV,而基體的平均硬度為170HV,涂層硬度是基體的2~3倍,具有優異的耐磨性能。激光掃描路徑2、3、4的涂層具有相似的硬度分布規律,其表層涂層的硬度略低于內層。這是因為內層熔覆層組織受到表層熔覆成形過程中激光能量的影響,進行了一次重熔和淬火硬化。路徑1涂層的斷面硬度變化較大,且沒有明顯的變化規律,這可能與涂層致密性和均勻性相對較差有關。熱影響區厚度約為1.2 mm,其硬度由涂層向基體過渡,在靠近熔合帶處變化幅度較大,熱影響區的硬度變化與激光淬火和元素擴散有關[8]。此外,路徑3的熱影響區硬度相對較大,這可能是由于激光垂直交叉掃描制備的涂層厚度較小,激光對基體的熱輸入量更大,使熱影響區的淬火硬化相對充分[20]。

圖8 不同激光掃描路徑下的顯微硬度分布
2.3 不同激光功率下殘余應力演變規律
以試樣1、2、3探究激光功率對涂層殘余應力的影響。激光功率分別為1.6,1.8,2 kW時涂層沿深度方向的殘余應力演變如圖9所示。涂層表面表現出壓縮殘余應力,X點的平均殘余應力為-333~-279 MPa,Y點的平均殘余應力為-332~-231 MPa。在涂層內部,X點的平均殘余應力為-601~-26 MPa,Y點的平均殘余應力為-614~-56 MPa。殘余應力在熔合線附近出現突變,熱影響區表現為拉應力,X點的平均殘余應力為107~282 MPa,Y點的平均殘余應力為74~357 MPa。圖9表明激光功率不會改變涂層內殘余應力的分布規律,只會改變其大小,適當的壓縮殘余應力有助于阻礙裂紋的產生和擴張,但需要避免拉伸殘余應力和較大的壓縮殘余應力出現,前者會增加涂層開裂敏感性,后者會導致涂層易剝落甚至翹起[8,21]。

(a)X點
圖10統計了激光功率P分別為1.6,1.8,2.0 kW時,涂層與熱影響區的平均殘余應力分布。激光功率為1.8 kW的涂層具有最大的壓縮殘余應力,且其熱影響區具有最小的拉伸殘余應力。在X點,涂層的平均壓應力為-441.18 MPa,熱影響區的平均拉應力為119.41 MPa;在Y點,涂層的平均壓應力為-446.75 MPa,熱影響區的平均拉應力為167.99 MPa。因此,激光功率為1.8 kW下涂層具有最優的殘余應力分布。

(a)熔覆層平均殘余應力
2.4 不同掃描速度下殘余應力演變規律
以試樣2、4、5、6探究激光掃描速度對涂層殘余應力演變規律的影響。掃描速度v分別為0.010,0015,0.020,0.025 m/s時涂層沿深度方向的殘余應力分布如圖11所示。涂層表面和內部均表現出壓縮殘余應力,而熱影響區表現為拉伸殘余應力,掃描速度的變化未改變殘余應力的分布規律。激光功率恒定時,提高掃描速度會減小熱輸入,且使得熔池冷卻速度加快。熱輸入減少會降低涂層內殘余應力的大小,而冷卻速度加快使得熔池溫度梯度增大,熱膨脹系數差異帶來的“正體積”效應增大,導致殘余應力增大,涂層內的殘余應力大小是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

(a)X點
圖12統計了掃描速度v分別為0.010,0015,0.020,0.025 m/s時涂層與熱影響區的平均殘余應力分布。當掃描速度為0.020 m/s時,涂層具有最大的平均壓縮殘余應力,且熱影響區具有最小的平均拉伸殘余應力。在X點,涂層的平均壓應力為-441.18 MPa,熱影響區的平均拉應力為181.27 MPa;在Y點,涂層的平均壓應力為-446.75 MPa,熱影響區的平均拉應力為199.02 MPa。綜上所述,激光功率為1.8 kW、掃描速度為0.02 m/s時的涂層具有最優的應力分布。

(a)熔覆層平均殘余應力
2.5 不同掃描路徑下殘余應力演變規律
以試樣2、7、8、9探究四種掃描路徑下殘余應力的分布規律。激光掃描路徑1、2、3、4下試樣在沿涂層深度方向的殘余應力分布如圖13所示。激光掃描路徑的變化同樣未改變涂層的殘余應力分布規律,涂層為壓應力而熱影響區為拉應力。涂層表面的殘余壓應力略小于涂層內部的殘余壓應力,這是因為涂層表面易出現應力釋放現象。同時,路徑3的涂層在層間結合處壓應力突然減小,這是因為垂直交叉的掃描方式打亂了涂層內應力的線性累積。掃描路徑的改變主要影響涂層的晶粒生長方向,進而調控涂層的殘余應力分布。

(a)X點
圖14統計了激光掃描路徑1、2、3、4下涂層與熱影響區的平均殘余應力分布。路徑1和路徑2的掃描軌跡較為相似,所以所得涂層的厚度、硬度、組織形貌相似,但是它們的殘余應力出現了差別。殘余應力測試結果顯示,它們的熔覆層殘余應力值相似,而熱影響區路徑2的拉應力小于路徑1的拉應力,所以其殘余應力分布優于路徑1。此外,偏置輪廓式的掃描軌跡(路徑4),涂層具有最大的平均壓縮殘余應力,且熱影響區具有最小的平均拉伸殘余應力。在X點,涂層的平均壓應力為-441.18 MPa,熱影響區的平均拉應力為119.42 MPa;在Y點,涂層的平均壓應力為-446.75 MPa,熱影響區的平均拉應力為167.99 MPa。輪廓偏置式掃描路徑使涂層的晶粒生長方向更為多樣化,且涂層內應力方向發散避免了應力集中,這對涂層的致密度和應力分布具有積極影響[22]。

(a)熔覆層平均殘余應力
2.6 殘余應力演變機理
殘余應力的產生與金屬的形變有關,在激光熔覆時,激光束對熔池有沖擊作用,使其體積收縮,激光束掃描過后沖擊力消失,故熔池有“體積膨脹”趨勢。然而,溶池此時已完全冷卻不會發生體積變化,所以涂層內產生了阻礙“體積膨脹”的壓應力,顯然該壓應力對提高涂層致密度以及阻礙裂紋擴張有積極影響。而在熱影響區,激光的淬火使其晶粒細化,在致密度提高的同時也有“體積收縮”趨勢,在冷卻后該區域會受到周圍材料的反作用,表現為拉應力。理論上,熱影響區會開裂,涂層不會開裂,但實際上涂層易開裂,而熱影響區很少開裂,這是由于熱影響區的材料韌性優于涂層,并且熱影響區處于涂層和基體之間,受到其他區域材料的擠壓和包覆,雖然其內部為拉應力,有產生裂紋的趨勢,但是裂紋難以在熱影響區擴展延伸。試樣在不受外力影響時,其內部應力是平衡的,涂層的壓應力和熱影響區的拉應力互相平衡。此外,涂層中的裂紋通常是以熱影響區為起點向上延伸貫穿涂層始終的,這是因為在熔池冷卻時,劇烈的溫度變化使得試樣熱影響區某處拉應力遠大于上方涂層內的壓應力,因此產生了裂紋。
激光功率和掃描速度決定了熔池中心溫度和冷卻速率,這影響了涂層的晶粒形狀和晶粒大小,掃描路徑則會影響晶粒的生長方向,而這些因素都會對涂層內的殘余應力產生影響。激光功率為1.8 kW、激光掃描速度為0.02 m/s、激光掃描路徑為輪廓偏置式掃描時,涂層壓應力最大,熱影響區拉應力最小,涂層具有最優的顯微組織和應力分布。
3 結論
使用激光熔覆在Q345鋼表面制備了雙層多道Fe基涂層,利用掃描電鏡和X射線衍射法分析了工藝參數和掃描路徑對涂層顯微組織和殘余應力的影響,結果表明:
(1)由基體-涂層的結合帶到涂層頂部,晶粒形狀發生如下變化:平面晶→胞狀晶→柱狀樹枝晶→等軸樹枝晶;輪廓偏置式掃描路徑使涂層的晶粒生長方向更為多樣化,提高了涂層的致密度。
(2)涂層表面和內部為殘余壓應力,在涂層-基體熔合線處殘余應力發生突變,熱影響區表現為殘余拉應力。適當的殘余壓應力能夠抑制裂紋的產生和擴張。
(3)激光功率為1.8 kW、激光掃描速度為0.020 m/s、激光掃描路徑為輪廓偏置掃描時,涂層具有最優的顯微組織和應力分布。殘余應力的產生主要與激光束對熔池的沖擊作用以及熔覆層的非平衡凝固特性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