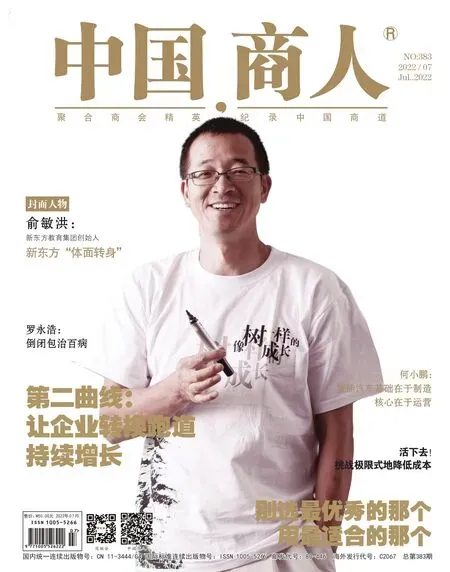美團的破局點:組合式創新形成第二曲線
李善友

只有被逼到絕境的時候,CEO的戰略功底才能真正顯現。可你真的懂戰略嗎?戰略很空洞,我們天天說、天天聽,但如果問你什么叫戰略?可能沒有幾個人能說清楚。
美團當年如何從千團大戰中突圍上岸?讓我們回顧當年的燒錢大戰。
美團、糯米、團寶、拉手、團購網……截至2011年8月,中國共有5058家團購網站,并由此引發了千團大戰。
這把火是從太平洋對岸燃起來的。團購網站Groupon2008年11月在美國成立。2009年6月融資1.4億美元,前兩年半共融資10.6億美元;2011年6月申請IPO,預期估值250億美元。
團購的概念迅速火了起來。彼岸的一個蝴蝶,引發了此岸的蝴蝶效應,中國的VC和創業者蜂擁而至,引發了千團大戰。
2011年4月,拉手網前三輪融資共計1.6億美元,大眾點評網前三輪融資1.27億美元。而現在傲踞群雄的美團網當時在資金上處于劣勢:2010年底,美團網A輪融資1200萬美元;2011年7月,美團網B輪融資5000萬美元。
最后為什么只有美團活了下來?
這些團購網站當時融來的錢大部分用于投放廣告,2011年各團購大戶迎來了廣告大戰。這場燒錢大戰中,大家都在融資燒廣告,而王興根本沒有錢。
每個人的人生一定遇到過這些關鍵時刻的選擇。這時王興的戰略是什么?作為龐大水池中資力并不雄厚的一員,一個策略失敗意味著短期內會被對手甩開距離,緊接著被行業淘汰。他該如何取舍?
王興當年逼迫自己做過一次選擇。
凡做決策總要有判斷的基礎。美團的基礎是什么?美團賦予了自己這樣的使命:“We?help?people?eat?better,?live?better”聽起來像口號,仿佛有點忽悠,然而并不是。
王興曾經明確說過:“客戶分為消費者和商戶兩端,兩端都很重要,都要服務好。如果兩者有沖突,選擇把消費者排在第一位。如果沒有消費者,商戶是不會用我們的。”
2010年年底,王興就想清楚了這件事:消費者第一,商家第二。有了這個定海神針,其他誘惑就相對容易破除了。
“消費者第一,商家第二”的價值觀,是美團的增長引擎和驅動輪。以此作為標尺來看,所有的迷霧就都被撥開了。
王興當時做了幾個決定:第一,堅決不打線下廣告;第二,瘋狂采購線上流量;第三,建立強大的地推團隊。
由于不打線下廣告,電梯里就永遠滾動著競爭對手的廣告,可以想象王興的壓力有多大。但他想得很明白,即便在線下看到了某商家的廣告,最后還得到線上搜索。
于是他采購線上流量,甚至把競爭對手的關鍵詞全買了。競爭對手做了大量廣告,但當消費者到線上搜索時,又會跳轉到美團。
事后看,2011年沒有打線下廣告,是美團歷史上做得最正確的戰略決策之一,避免了無謂的燒錢,讓美團活了下來。
這是美團成功轉折的關鍵點。找到了那個“一”就有了依據,沒找到那個“一”,跟著別人走會是什么情況呢?那一年團購網站市場規模漲了1倍,但其背后市場推廣費用漲了10倍,投資漲了10倍,人員規模漲了10倍,成本也漲了10倍……
也就是說,當年大量的廣告投放是無效的。所以到2014年,全國團購網站僅存176家,死亡率為96.5%。
“消費者第一”支撐美團在血海中殺出一條路,成功上岸,這句話是美團的使命、文化價值觀,也是它的戰略起點,有了它才有了美團后來的一切。
美團的案例教會我們,只有面臨沖突才是對一個領導者戰略能力的最終考驗,被逼到絕境的時候,CEO的戰略功底才能“立”起來。這一切的前提是,一定要找到那個不變的“一”。“舍九取一”是戰略素養。
如果只能取“一個”,該取哪一個?找到“不變的一”,戰略才能成形,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有限的事務上。
比如,亞馬遜的“一”是消費者,它的使命是“成為全世界最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公司。”研究貝索斯會發現,他對他的B端即供應商極其兇殘,但貝索斯對C端非常好——這迎合了它的使命。
阿里的選擇恰恰相反。阿里的“一”是商家,證據很明顯——它的使命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阿里賺的是B端的流量費,如果B和C沖突,它選擇保護B。所以面對2B的生意,阿里總是贏,這跟它最初選擇的“一”不無關系。
戰略本身什么都不是,它必須找到某一個支點,把資源壓在這個支點上,撬動增長飛輪。因此,好戰略就是杠桿作用。
格魯夫——英特爾公司前CEO曾敏銳地發現一件事:每一個戰略轉折點都表現出10倍速變化,而每一個10倍速變化都會導致戰略轉折點。
他給了一個數量上的標識:增長速度的十倍速變化。請注意,我們要找到的是——單一要素十倍速變化。一個系統里的組合要素很多,不是組合要素的整體發生十倍速變化,而是整體里的某一個關鍵要素短時間發生十倍速變化。這才是選擇的關鍵點。
這是格魯夫在工業時代用過的模型,這六個變化里但凡有一條發生十倍速變化,就有可能是破局點來臨的標志:競爭的十倍速變化,技術的十倍速變化,用戶的十倍速變化,供應商的十倍速變化,互補企業的十倍速變化,營運規則的十倍速變化。
什么是破局點?第一條曲線會遭遇極限點,然后出現非連續性,新的第二曲線才能打破這個極限點。而第二曲線最開始出現時有一個關鍵點,這個關鍵點就叫破局點。在破局點之前,曲線是下降的,只有打破破局點,才能進入到正循環和高速增長的軌道中。如果不能打破這個破局點,創業公司面臨永遠低水平重復的窘境。
如何擊穿破局點?接下來的問題在于,就算你找到十倍速變化的單一要素作為破局點,之后如何擊穿?最大化單一要素,最小化其他要素。
新產品的產生并不是做一個更大更全的產品,而是原有體系里的某一個功能點,把它放大為一個新產品的整體。
幾乎教科書一般,讓我們來回顧埃隆·馬斯克創業的早期。
伊隆·馬斯克說,“早期創辦PayPal的時候,我們先打算用PayPal提供整合性的金融服務。這是多么復雜的一件事情,結果每次我們跟別人介紹這個系統的時候,大家都沒什么興趣。等到我們介紹這個系統里有一個小功能——可以用電子郵件付款的時候,每個人的眼睛都亮了。于是我們決定,放棄所有其他一切,只把電子郵件付款這個小功能拿出來作為PayPal的全部,結果PayPal一炮而紅。”

單一要素最大化,聚焦第一曲線的一個核心要素,重度投入資源,把它生長為第二曲線的全部。
大多數人想做更大更好更全,而創新的秘密,恰恰在于單一要素最大化。
美團比整個行業早一年開始向移動互聯網轉型。一直到2012年,李彥宏還認為移動互聯網沒有來到,而王興在2009年就知道移動互聯網要來了。那時他堅決轉型移動互聯網,即使PC上還有巨大流量。
在有限的資源下,美團斷了PC所有投放,用全部資金買移動用戶。在那之前,它的PC轉化率甚至高達30%。結果呢?2011年底移動端交易占比5%;2012年底移動端交易占比30%;2013年初目標50%,年底達到70%,提前一年完成移動互聯網轉型。
這件事使得美團在千團大戰中廝殺出來。王興講過一句話論證了我們今天講的方法論:“一個行業某個關鍵要素產生五到十倍變化的時候,行業才可能有百倍的爆發。”
2012年智能手機發生了十倍速的變化,所以2012—2014年是從PC向互聯網轉移的非常重要的時間,因此王興選擇把所有資源all?in在這個單一要素上,把它最大化,擊穿這個破局點。
這件事情對創始人能力有特別大的考驗:第一,能不能判斷出來?第二,判斷出來之后,敢不敢投入有限資源?
你的破局點,也是別人的極限點,遭遇極限點以后如何轉化為破局點迎接第二曲線?辦法就是創新,即從第一條曲線轉換為第二曲線。
中國的創業走到今天,紅利和管理的效率空間已經耗盡,有效的增長引擎只有一個——創新。如何做到呢?
當我們講創新的時候,腦子里的直觀感受是發明和創造。大家通常把創新基于科技,所以每次講創新的時候,會聯想到科技的創新。
有媒體曾采訪王興,問道:“很多人說你從來沒有做出一些原創性的顛覆性產品,言外之意,王興其實你沒有什么創新能力。”
王興回答:“我同意,并不是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100%原創,那也不是我追求的。大家可能對創新的理解有點偏。舉一個最夸張的例子,你是一個記者,你寫的每一篇文章,里邊每一個漢字,全都是已經存在的,你并沒有發明任何一個漢字,你所做的事情是通過重新排列組合,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想法,你的創新并沒有體現在創造文字上,而體現在對文字的排列組合上。”
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認為王興是一個理解什么叫創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