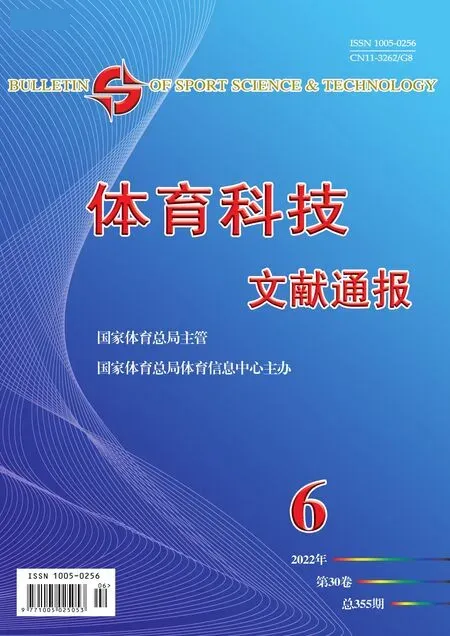完美主義與運動表現的關系研究及進展
車旭升,陸姍姍
前言
完美主義是一種與成就相關的人格特征。在運動情境中,完美主義被發現是競技運動員的共同特征[1-2],甚至是成為奧運冠軍的前提條件[3]。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完美主義是一種適應不良的特征,是阻礙而不是提高運動成績[4-5]。因此在運動心理學中,完美主義具體是如何影響運動表現的,仍然存在爭議。為了進一步梳理完美主義與運動表現的關系,系統檢索了中國知網、PubMed、Web of Science中從1950年至2022年已發表的相關文獻,著重整理了2000年至今的研究進展,分析了完美主義在運動表現中所扮演的角色,為提高我國運動員的運動表現提供新的思路。
1 完美主義的概念構成及其發展
傳統上,狹義的完美主義近似于人們日常中的強迫癥。早期的心理學概念認為完美主義是心理失調和紊亂的標志,也被心理學家視為一類神經癥,其主要特征是極度追求完美,伴隨著高標準的承諾與追求和對自我行為過于挑剔的自我負評價傾向[6-7]。這種人格特質被認為是單維的,并且對于個體而言,只有消極作用[8]。
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探索,賦予完美主義更多元的含義。Hamachack從適應功能的角度提出了雙維度概念——正常完美主義(normalperfectionism)和功能障礙完美主義(dysfunctionalperfectionism)[9],認為前者會積極追求成就,后者則過于害怕失敗而導致難以獲得成就感。這一里程碑式的觀點也奠定了日后完美主義多維化的發展道路。
在多維完美主義的分類與測量上,有兩類觀點比較多,第一類是Hewitt和Flett[10]的模型。由于考慮到影響完美主義有來自于個人和社會方面,因此將完美主義分為了三個維度,即自我導向型、他人導向型和社會規定型完美主義。在這個模型中,自我導向型完美主義的特點是嚴格的個人標準和自我評價,是施加于自身的;他人導向型完美主義被認為這些嚴格的標準與評價是向外的,是強加于他人的;而社會規定型完美主義是指個體盡力去滿足他人對自己的嚴格標準和評價。這些維度的得分可以通過《休伊特多維完美主義量表》(簡稱MPS)來測量。第二類是Frost等[11]的模型,將完美主義分為了六個維度,分別是個人標準、關注錯誤、父母期望、父母批評、行動的疑慮和組織性。同時,這些維度的得分可以通過Frost等人設計的《佛羅斯特多維完美主義量表》(簡稱FMPS)來考察。但也有學者在后期驗證FMPS的信效度時提出不同見解,比如我國學者訾非[12]依據調查,認為將父母批評合并到父母期望,條理性修改為組織性更符合中國大學生的人格特征,方新[13]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將父母批評和父母期望合并到父母要求。
隨著近二十年科學研究的不斷探索,完美主義進入到了一個詳細而混亂的局面。詳細在于完美主義的概念和結構已被深入剖析,測量工具也被無數次驗證與更新。混亂在于由于學者們認識到完美主義的表現方式和對個體的影響有其積極層面和消極層面,因此將完美主義區分為兩種基本形式。第一,這兩種基本形式受個人主觀因素和學術環境影響的原因,被賦予了不同的名稱,如正常完美主義和神經質完美主義[14]、主動和被動完美主義[15]、積極和消極完美主義[16]、適應性和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17]、功能性和功能失調的完美主義[18]、健康和不健康的完美主義[19]、盡職盡責和自我評價的完美主義[20]。因此統一完美主義形式的名稱是個重要問題。第二,許多學者在設計完美主義量表時,將完美主義的兩種形式通過維度的方式體現出來,但是完美主義量表有很多版本,到底哪些維度可以被歸為積極形式,哪些維度可以被歸為消極形式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基于以上問題,Stoeber等[20-21]提出了以下觀點:首先,完美主義的兩種形式為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這也是完美主義的兩個高階維度。完美主義追求是完美主義的積極形式和積極層面,抓住了那些與追求完美和設定極高的表現標準有關的方面;完美主義擔心是完美主義的消極形式和層面,關注的是那些與犯錯誤相關的方面,害怕別人的負面評價,以及期望和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感。Stoeber等[22]指出,盡管這兩個維度通常高度相關,但這兩個維度往往顯示出不同的、對比的關系模式。完美主義追求常常與良好適應的指標正相關,如積極情感、積極的成就追求、自我實現、高目標取向、較好的學習成績等[23-29]。而完美主義擔心維度與抑郁、壓力和焦慮、過度的自我批評等不適應指標正相關[30-34]。其次,代表完美主義追求水平的有FMPS中的個人標準分量表、MPS中的自我定向的完美主義分量表、APS-R中的高標準分量表、MPS-S中的個人標準分量表、MIPS中的追求完美分量表;代表完美主義擔心水平的有FMPS中的對錯誤的關注量表或對錯誤的關注和對行動的懷疑量表的組合、MPS中的社會規定的完美主義、MPS-S中的關注錯誤分量表、MIPS中的對不完美的負面反應分量表。這兩個觀點成為現今國外完美主義研究者的理論基礎。
2 完美主義與運動表現的關系
優秀運動員的績效是身心相互協調的產物。運動員作為在運動技能上表現突出的一類群體,在競技領域中具有追求高標準、高要求、精益求精的傾向與完美主義特性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因此研究運動員與完美主義之間的密切關系,成為受運動心理學家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對運動領域完美主義的研究趨勢大多聚焦在運動員完美主義與競賽焦慮、心理疲勞、失敗恐懼、自尊和運動成績方面。國外研究者傾向于采用MPS-S[35]、MIPS[36]測得運動員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兩個水平,進而分別分析與運動表現的關系。國內研究者傾向于采用MPS-S-C[37],詳細分析各維度與運動表現的關系。
2.1 完美主義與運動競賽焦慮
競賽焦慮是指運動員在比賽中出現心律加速、機體緊張、流汗等生理反應和難以集中注意力、擔憂或消極看待比賽結果等認知反應的現象[38]。高水平的競賽焦慮會使運動員難以發揮正常水平,最終影響比賽成績。Hall等[39]認為發揮失常是完美主義運動員產生焦慮的重要原因。運動競賽本身具有社會評價性,因此運動員不可避免承受了巨大壓力,常常會發生運動競賽中的“超常發揮”(clutch)和“發揮失常”(choking)。一個有完美主義特質的運動員是不容許自己出現失誤的,面對本不該發生的失誤,會導致運動員喚醒水平的提高,隨之緊張、焦慮的程度也會增強。
研究發現,完美主義擔心往往和競賽焦慮存在顯著正相關,例如Ivanovic等[40]發現完美主義擔心與年輕運動員在比賽期間的認知焦慮、軀體焦慮呈正相關,Stoeber等[41]發現完美主義追求與更高的水平的自信正相關,而此前有研究[42-44]表明自信水平較高的運動員賽前焦慮的發生率往往較低。Freire等[44]的調查研究進一步證實了運動員的完美主義擔心與認知焦慮、軀體焦慮的升高呈顯著正相關,并且在男運動員上表現更為強烈。
李雷等[45]對191名國內大學生運動員進行研究,研究程序分為了兩步,第一步分析了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與競賽焦慮的相關性,結果顯示均與競賽焦慮呈顯著正相關。第二步將追求完美和對不完美的負面反應交迭的消極作用分化出來,結果發現完美主義追求與競賽焦慮表現出顯著負相關。這一結果說明追求完美本身并不是不利的,相反,追求完美甚至可能減少他們對失敗的擔心程度(認知焦慮),緩解身體的緊張反應(軀體焦慮)及提高自信。
以上研究均表明,完美主義擔心總是與認知焦慮、軀體焦慮呈正相關,而完美主義追求與認知焦慮、軀體焦慮呈負相關,與自信呈正相關。因此可以推測,完美主義追求水平高的運動員在比賽時給予自己更多鼓勵和肯定,提升了自信,從而使比賽狀態更為放松,緩解了競賽焦慮的程度。
2.2 完美主義與心理疲勞
二十世紀初,國外學者便注意到完美主義會引起生理與心理方面的倦怠反應,即心理疲勞,嚴重的心理疲勞會使運動員出現心理疾病。Gould等[46]認為完美主義作為一種與成就相關的人格特征會導致運動員產生心理疲勞。Stoll等[47]認為完美主義引起運動員心理疲勞的原因在于完美主義會使運動員產生過高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往往是超出現實條件的。
Madigan等[48]首次發現可以通過完美主義追求與完美主義擔心水平間的相關性來預測運動員心理疲勞的變化。當利用調節回歸分析完美主義追求×完美主義擔心的交互效應時結果顯示顯著,即完美主義追求水平可以緩解關注錯誤的負向影響。這給了研究人員啟發,運動員的完美主義傾向是普遍存在的,有些著名的優秀運動員傾向程度可能更高,比如喬丹等等(雖沒有研究對他們進行心理測量,但據運動員自己的表述,可以猜測其得分會比較高),但是他們的運動表現可以說十分精彩,似乎是完美主義締造了他們的成功,或許就是因為這些優秀運動員的追求水平緩沖了擔心水平。他們的注意力更集中在達成自我標準上而不是在運動情境中犯的錯誤,包括這些錯誤或者失誤帶給自己的壓力,動機也可能是更滿足于自我的成長(比如訓練是否有成效,這場比賽的狀態是否令自己滿意),或許他們相信只要自己按照標準來,那么就“不可能犯錯”,比賽名次也就一定不會差。
Demirci等[49]調查了267名運動員的完美主義和心理疲勞的水平,回歸分析顯示完美主義擔心可以顯著預測心理疲勞的成就感降低和情緒/身體疲憊兩個分維度的水平。除此之外,他們還發現激情(passion,指個人傾向于將時間和精力花在他/她喜歡甚至愛并認為重要的事情上的程度[50])的消極性成分(強迫性激情,指參與一項活動來自于外部壓力或者參與該活動感到不愉悅)與完美主義擔心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疲勞呈顯著正相關,而積極成分(和諧性激情,指參與一項活動完全來自于個人意愿)與完美主義追求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疲勞呈顯著負相關。可以進行推理,更來源于自身的熱愛、更少或者更不在意來自外界的壓力的運動員其完美主義追求水平更高,也就更不容易產生心理疲勞。這與前文的推測一致,因此提高運動員對運動的興趣和喜愛,提高其內部動機,可以有效改善他們的心理疲勞,保持其健康的心理狀態。
Olsson等[51]對190名運動員進行了兩項研究。第一項研究討論了完美主義各維度和心理疲勞的相關性,結果表明不論是來自運動員自身還是他人以及社會對他們的期望,都與心理疲勞有顯著正相關。第二項研究將完美主義-心理疲勞的關系拓展到了教練層面。回歸分析表明,當運動員感知到教練導向的完美主義時,更容易產生倦怠。也就是說,教練對運動員施加的壓力和期望越大,運動員越容易產生心理疲勞。
國內方面的研究進展主要在于分析完美主義各維度與心理疲勞各維度上的相關性。王翠萍[52]的研究指出關注錯誤與心理疲勞的關系最緊密,最能預測失敗恐懼;陳偉源和盧賽君[53]也發現射擊運動員完美主義的關注錯誤與心理疲勞的各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對心理疲勞各維度及其總分起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幺蘭等[54]發現大學生運動員心理疲勞的成就感降低與完美主義的個人標準維度呈顯著負相關,與完美主義的其他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情緒體力耗竭、運動負評價與完美主義除個人標準以外的其他各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運動員完美主義的個人標準顯著負向預測成就感降低,關注錯誤顯著正向預測成就感降低。郭正茂和楊劍[55]利用MPS-S-C對956名青少年運動員進行調查,發現關注錯誤比個人標準對心理疲勞的預測作用更顯著;基本心理需要在運動員完美主義與心理疲勞之間的中介作用也得到了驗證。因此提高青少年運動員的基本心理需要水平,是使完美主義對心理疲勞的影響降低的有效方法之一。從以上的國內研究可以看出,完美主義的個人標準與心理疲勞呈負相關,關注錯誤與心理疲勞呈正相關,且關注錯誤可以更好地負向預測心理疲勞。因為MPS-S-C是基于MPS-S修訂的,因此可以說明國內的研究也支持了完美主義的積極維度對心理疲勞有負向影響,消極維度對心理疲勞有正向影響的結果。
2.3 完美主義與失敗恐懼
失敗恐懼顧名思義即為對失敗的恐懼傾向,是一種消極的情緒體驗[56]。伴隨著失敗而來的,是羞恥、慚愧、低自尊,甚至憤怒等等,而這些消極情感可能會阻礙運動員的成長與發展,因此需要弄清完運動員美主義影響失敗恐懼的機制。
Anshel等[57]發現,當運動員有完美主義的傾向時,會過度追求目標上不切實際的“完美”,從而易形成賽前焦慮、比賽時過度關注失敗進而產生失敗恐懼。Stoeber等[58]對運動員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完美主義追求與失敗恐懼呈負相關,而完美主義擔心與失敗恐懼呈正相關。Sagar等[59]后續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研究發現,完美主義追求與失敗恐懼害怕經歷羞恥和尷尬呈負相關,與成功后的積極情感呈正相關,而完美主義擔心與失敗恐懼的害怕經歷羞恥和尷尬以及失敗后的負面情緒呈正相關。此外,對羞恥感和尷尬感的恐懼在完美主義擔心失敗后的負面情緒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說明對經歷羞恥和尷尬的恐懼是完美主義與失敗恐懼二者關系間的核心。McGregor等[60]也認為羞恥感是失敗恐懼的核心情緒。運動員的完美主義使其渴望成功,渴望他人、社會的正面評價,而失敗意味著不完美,換來的是輕視、嘲笑甚至辱罵,因此會引發強烈的羞恥感。
國內方面,閔東旭等[61]考察了233名大學生運動員完美主義和失敗恐懼的關系,并檢驗了自尊在二者間的中介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大學生運動員的完美主義與失敗恐懼各維度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其正向預測失敗恐懼及其各維度,說明大學生運動員在追求卓越成績與表現的同時,會伴隨恐懼比賽失利的情況,即一種“想贏怕輸”的心理。這種心理是矛盾的,因為即使不具備完美主義特征,運動員也總是希望自己能發揮最好,獲得盡可能好的比賽成績,但是比賽本身就是充滿了競爭與挑戰,對于參賽者來說,有人贏必有人輸,但是任何一個運動員都不希望出現在自己身上,這使得運動員既想贏又怕輸,而有完美主義特征的運動員這種表現會更強烈。除此以外,他們發現自尊在完美主義和失敗恐懼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說明提高大學生運動員的自尊水平,可以顯著降低因完美主義引起的失敗恐懼。
裴彩利調查了187名大學生運動員,考察了他們的完美主義、失敗恐懼和自我妨礙之間的相關性。結果發現大學生運動員的完美主義和失敗恐懼以及自我妨礙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完美主義和失敗恐懼均能預測自我妨礙;采用逐步回歸分析發現,失敗恐懼在反復思考與自我妨礙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關注錯誤、知覺父母壓力、知覺教練壓力與自我妨礙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62]。可以說明大學生運動員越是渴望有完美的表現,就越是害怕失敗及其后果,也越容易為自己的失敗尋找借口,出現自我妨礙傾向。
2.4 完美主義與自尊
自尊體現了個體對自我價值的感受[63]、評價[64]程度,低水平的自尊容易使運動員對自我價值出現認知偏離,造成心理問題。因此理解完美主義影響自尊的原因有助于提高運動員的自尊水平,提高其心理健康。
Blatt[65]早就意識到,運動員過度追求完美時會導致他們自尊水平下降,具體原因為兩點:第一,當屢屢達不到自己所定的要求時,會陷入強烈的自我懷疑中,回質疑自己水平和能力。第二,一旦產生第一種現象,他們會難以接受,由此導致低水平的自我接受。Gotwals等[66]發現,非適應性完美主義者的自尊水平更低。Koivula等[67]的研究發現,自尊水平高的運動員在完美主義追求上的得分更高,而在完美主義擔心上的得分更低,說明完美主義的消極維度與運動員低自尊密切相關。Antonio等[68]測量了運動員的完美主義水平,首次揭示了運動員完美主義、自尊、憤怒管理之間的關,表明高完美主義追求水平的運動員有著更高的自尊水平,高完美主義追求水平可以預測更高的憤怒管理水平。
高水平的自尊意味著更高的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訓練比賽滿意感[69-70],可以有效提高人的心理健康水平[71-72],因此通過的自尊的中介作用可能會降低運動員因完美主義引起的消極運動表現。張連成等[73]對260名體育院校學生進行完美主義、自我設限和自尊方面的調查問卷,并分析自尊在完美主義和自我設限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結果表明,自我設限與完美主義除個人標準以外的分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與自尊呈顯著負相關。自尊在完美主義的關注錯誤、知覺父母壓力和知覺教練壓力與自我設限中的中介效應成立且完美主義對自我設限的預測值下降。可以看出,通過自尊的中介作用可以使運動員完美主義對自我設限的影響程度降低。
2.5 完美主義與運動成績
運動員的終極目標是不斷超越自己,創造優異的運動成績。通過調查研究和實驗研究,具體分析完美主義對運動成績的影響,有助于運動員、教練員如何從人格的角度幫助運動員提高成績。國外一共有五項研究探索了運動員完美主義對運動成績的影響,其中有四項研究支持了運動員完美主義追求水平可以提高運動成績的觀點。
最早的實驗研究者是Anshel等人[4]。他們首先用FMPS分別測得30名男大學生運動員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的水平,然后對他們進行了20次的身體平衡試驗,其中有10次試驗,運動員沒有收到關于他們表現的反饋;另外10次,他們收到虛假的負面反饋,提示他們沒有達到以前的最佳狀態。最后的研究結果表明,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在沒有收到反饋的情況下對運動員的成績沒有影響,而在給予虛假負反饋的情況下對運動員的成績有負向影響,說明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均對運動員的成績有負向影響。然而值得考慮的是,因為實驗組的運動員接受的是虛假反饋,他們的動機更可能是避免錯誤而不是表現更好。因此在現實生活環境中,如果當運動員收到關于他們表現的真實反饋時,不排除完美主義追求水平會對他們的表現會有積極影響。
Stoll等[74]在采用MIPS中測得112名大學生運動員的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的水平后,對其進行了四項籃球試驗。結果表明,完美主義追求均與更好的成績相關,即傾向追求完美的運動員比擔心錯誤的運動員表現更好。Stoll等的實驗結果不僅驗證了完美主義追求水平對運動表現存在積極影響,同時還發現完美主義追求與完美主義擔心水平的交互作用可以預測更好的成績增長,其中高水平完美主義追求與高水平的完美主義擔心的運動員表現出最大的成績增長。
Stoeber等[75]對鐵人三項運動員進行了兩項詳細的實地研究,利用MPS分別調查了他們的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水平,并且要求他們報告了本季節內的最佳成績和個人最佳成績。第一項研究調查了112名鐵人三項運動員在半鐵人距離(1.9公里游泳、90公里自行車、21公里跑步)比賽中的表現,第二項研究調查了321名鐵人三項運動員在奧運會距離(1.5公里游泳、40公里自行車、10公里跑步)比賽中的表現。結果發現,這兩項研究在控制了性別和年齡后均只有完美主義追求才與運動成績顯著正相關,而完美主義擔心與成績無關。除此以外,Stoeber等還讓運動員完成了一份關于成就目標[76]的問卷調查,旨在進一步分析完美主義追求水平如何影響運動員表現與成績。中介分析顯示,表現接近目標(如:對我來說表現得比別人非常重要)與表現回避目標(如:我只想避免表現得比別人差)之間的差異在完美主義追求與表現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說明高完美主義追求的運動員追求的是接近成績的目標而不是回避成績的目標,兩個目標之間的差異越大,他們的比賽成績越好。簡而言之,擁有高水平完美主義追求的運動員在比賽中設定了更多的表現接近目標,從而取得了比低水平完美主義追求運動員更高的比賽成績。這兩項研究結果對運動領域完美主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現實生活中,在沒有錯誤或失敗反饋的情況下,高水平完美主義追求的運動員比低水平完美主義追求的運動員可能獲得更高水平的運動成績。更重要的是,完美主義追求預測的競爭表現超出了運動員先前表現水平的預期。這一研究結果給了研究人員啟發:推測運動員追求成就目標的種類和組合可能代表了另一種機制,即高水平完美主義追求的運動員通過更強烈地支持表現接近目標而獲得更優異的運動成績。
在以往關于完美主義與運動表現的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遺憾是缺乏對團隊運動表現的關注——只考察到個人層面上的完美主義與運動成績之間的關系。基于此,Hill等[77]采用Hewitt等的三因素模型,探索性地考察了36條賽艇團隊的完美主義與運動成績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中,研究結果從四個方面擴展了目前對完美主義與運動成績關系的理解。第一,此研究首次提出并驗證了完美主義追求水平與運動表現之間的正向關系可能延伸至整個團隊的表現。第二,自我導向型完美主義會對團隊表現有積極影響,但是影響較小。第三,他人導向型完美主義(把嚴格標準與評價施加于他人)標準對團隊表現有較大的積極影響,并且是提高團隊表現的主要驅動力,因為個人完美主義追求對個人表現的影響可能反映在期望團隊其他成員對團隊的完美表現上。第四,社會規定的完美主義對團隊表現沒有影響。
3 小結
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是運動員完美主義的兩個核心維度。研究表明,完美主義追求與運動成績呈正相關,并可以預測更高的個人成績,即超出個人的一般能力或先前表現水平的預期。對于運動員而言,高水平完美主義追求似乎是一種激勵性的品質,能帶給他們一種額外的“動力”,讓他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額外的努力,并取得盡可能好的結果。一些臨床心理學家也開始認識到,完美主義追求是追求卓越的健康表現[78-79],而完美主義擔心往往與消極運動表現呈顯著正相關,阻礙了運動員的成績和發展。更重要的是,具備高水平完美主義追求且低水平完美主義擔心的運動員和高完美主義追求與高完美主義擔心的運動員在運動表現方面有明顯差異,完美主義擔心對運動表現不只存在消極影響,特別是高完美主義追求與高完美主義擔心水平的運動員,其運動成績的增長也十分明顯。因此應該關注到對運動員的完美主義加以正確引導和發展,提高運動員完美主義追求水平對運動員有著健康、積極的作用。
其次,在團隊項目的運動員中發現了他人導向的高水平完美主義是提高團隊整體表現與成績的主要驅動力,這對于研究者十分具有啟發性。個人和團體/集體項目的運動員因運動項目性質上存在的差異,其完美主義對運動表現的內在影響機制必然也會存在差異,個人項目的運動員可視參照物往往是其教練和同項目的其他運動員,即使他們是在同一教練下或同一訓練隊中,也分屬于獨立的個體。但是團體/集體項目的運動員有著一種榮辱與共的信念,不僅會要求自己的完美表現,更會要求他人有著同樣完美的表現,以期獲得最佳成績。這種強加于隊友身上的高標準在團隊利益的驅使下,可能演變成團隊內部共享的期望,成為整個團隊一致的目標。據此,完美主義對于團隊運動成績有積極影響的結論可以成立。
目前國外研究者傾向于通過調查與實驗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運動員的完美主義,但是國內研究者目前還停留在調查研究,因此應當加強實驗研究。其次,將成就目標這一變量引入到運動員的完美主義研究中,可以多角度探討運動員完美主義影響運動表現的機制。除此以外,可以嘗試從完美主義追求與完美主義擔心的角度對一些優秀運動員進行訪談和個案研究,以獲得最可靠的數據,深入分析他們在賽前、賽中、賽后的心理變化過程,為因人而異地制定提高運動表現的最優化方案提供參考和借鑒。再者,對MPS-S-C進行積極維度與消極維度的劃分,以便測量和了解中國運動員完美主義追求和完美主義擔心的水平,為提高國內運動員的運動表現提供更可靠的依據。最后,在未來研究中,可以加強對團隊運動項目的研究,將完美主義對個人層面的影響擴展到集體層面,以豐富和完善運動員的完美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