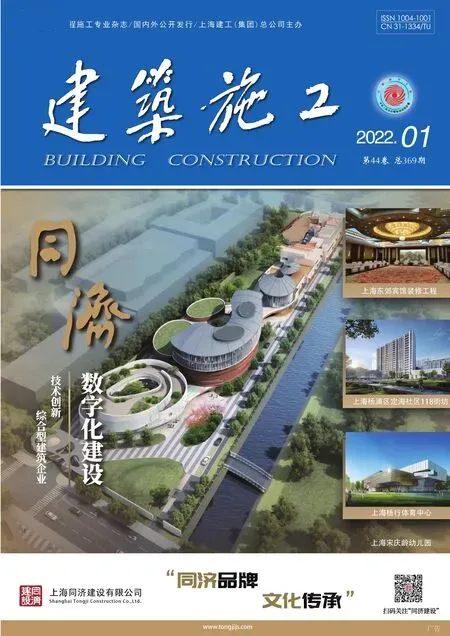以性能化分析手段研究主動防火系統對人員疏散環境的影響程度
蔣科明
上海建工集團工程研究總院 上海 201114
性能化分析是一種借助計算機軟件,對建筑進行等比例建模,設置關鍵參數,模擬周圍環境或某特定因素對建筑物及其內部人員的影響程度,并分析模擬結果的一種手段。譬如結構設計時用到的PKPM受力分析軟件,方案設計時用到的CFD風環境模擬軟件、Ecotect日照分析軟件、FDS火災煙氣模擬軟件,運維管理時用到的Pathfinder人員疏散模擬軟件等。性能化分析不僅可以作為方案比選的一種直觀顯現手段,其對設計思想的走向、應急預案的制定、建筑性能的評估等也提供了很大幫助。性能化分析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借助計算機模擬出現實中難以進行的試驗(譬如火災),收集試驗結果及相關數據,從而“預知”某些特殊事件的發展過程及對建筑的影響情況,并提前在設計、管理等方面尋找解決方案,以最大化消除事件發生時對建筑物的負面影響。
本文以性能化分析為手段,以上海市某辦公樓為實際案例,研究不同主動防火系統對火災時人員安全疏散的影響情況。
1 研究背景
1.1 消防性能化分析
消防性能化分析旨在研究火災情況下火災生成物對建筑物及其內部人員疏散環境的影響情況,以此來輔助設計師對主動防火系統和被動防火系統的設計。
由于火災模擬試驗全程在計算機上進行,因此,設計師可輕松改變任一消防系統的性能參數,并觀察其對火災發展狀態的影響程度。
一般而言,消防性能化分析分為火災煙氣模擬和人員應急疏散模擬[1-2]。前者實質為模擬火災產生的各類有毒有害煙氣(含CO2、CO、SO2、固態顆粒等)在建筑內的蔓延情況,該模擬手段被廣泛應用于建筑防火分隔、擋煙垂壁、自動噴水滅火系統(簡稱“噴淋系統”)、防煙排煙系統等設計的合理性檢驗;后者實質為模擬緊急情況發生時建筑物內人員的疏散情況,一般被用于輔助制定火災、大型聚會等容易造成人員擁堵、踩踏事件的應急預案,如圖1所示。

圖1 消防性能化分析
在實際生活中,由于設備生銹老化、年久失修、人為因素等原因可能導致部分主動防火系統在火災發生時無法及時啟動,例如物業管理人員將本應處于“自動起泵”狀態的消防水泵調至“手動起泵”狀態,導致火災發生時雖已觸發自動噴水滅火系統噴頭動作,卻因水泵未及時啟動而導致噴頭無法出水,延誤火災撲救。這就是本文研究所對應的現實背景。
1.2 主動防火系統
主動防火系統和被動防火系統是建筑防火工程(消防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主動防火系統主要由自動噴水滅火系統、火災自動報警系統、防煙排煙系統、消防控制室等設施設備組成。其作用為及時感知火災的發生,通報火災發生地點,并主動撲滅初期火災或限制火災的發展規模,減少火災對建筑物造成的破壞和對人員生命健康的危害。被動防火系統則是指通過提高或增強建筑構件、材料承受火災破壞的能力,達到防止火災擴大、減少過火面積、增強疏散能力的目的,如合理確定防火間距、提高建筑物的耐火等級、設置防火/防煙分區、合理布置疏散通道等。
本文案例建筑為結構完工建筑,被動防火系統已無太大調整空間,因此本文從建筑主動防火系統出發,展開研究論述。
1.3 火災模擬軟件Pyrosim
受限于計算機算力及時間成本,消防工程計算機火災模擬試驗一般不考慮建筑火勢的蔓延,僅考慮煙氣的擴散,因此火災模擬也被稱為煙氣模擬。
目前用于建筑火災模擬的性能分析軟件較多,如美國NIST開發的場模擬軟件FDS、區域模擬軟件CFAST、網絡模擬軟件CONTAMW,英國火災研究站開發的場模擬軟件JASMINE等。其中以流體力學和燃燒學相關公式為核心算法的場模擬軟件FDS最受業界認可,接受程度較高。美國Thunderhead Engineering公司以FDS為基礎,開發了另一款火災模擬軟件Pyrosim,在完整保留FDS全套算法的同時,提供了更為友好的可視化建模界面和結果處理界面,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軟件操作的門檻,使得建模和數據分析過程更為便利。
2 辦公建筑火災煙氣模擬
2.1 項目概況
本文所選案例為上海市某Ⅰ類高層辦公建筑,選用標準層第22層作為研究對象。
具體建筑防火設計情況如下所述。
2.1.1 防火分隔
該層建筑面積為3 958 m2,被防火墻和耐火極限不低于3 h的防火卷簾(水平式側向防火卷簾)劃分為2個防火分區,設有6個安全出口(每個防火分區各3個),分別通向該建筑的4個防煙樓梯間。
2.1.2 防煙排煙系統
采用密閉式吊頂設計,吊頂下方設高500 mm擋煙垂壁,整層被劃分為4個防煙分區,防煙分區未超越防火分區(圖2)。辦公區由4臺排煙量33 000 m3/h排煙風機負責排煙(按防煙分區均布),圍繞核心筒周圍的走道區設2臺排煙量15 000 m3/h排煙風機排煙(按防火分區均布),設2臺補風量32 000 m3/h補風機(按防火分區均布)。

圖2 防火防煙分區示意
2.1.3 火災自動報警系統
火災自動報警系統由感煙火災探測器、感溫火災探測器、手動報警裝置、消防廣播、閉路電視、消防控制室等組成,火災發生時能有效聯動控制各消防系統設施。
2.1.4 自動噴水滅火系統
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按防火分區分區設計,每個防火分區由1根獨立干管引出,采用吊頂隱蔽式下噴頭設計,選用68℃快速響應型噴頭。
2.1.5 聯動控制邏輯
為了提高火災響應的靈敏性,當煙氣觸發任一防煙分區1支感煙火災探測器時,啟動負責該防煙分區的排煙系統;觸發任一防煙分區2支獨立感煙火災探測器時,啟動防火卷簾。
2.2 設計火災場景
該樓實行全樓禁煙制度,由煙頭引發火災的可能性較小,該層為商業辦公區,辦公用電設備較多,不排除因用電設備線路老化或員工違規使用大功率電器而導致的電氣火災,因此,可將用電設備短路引燃桌椅作為此次火災模擬的燃燒物。
為分析不同主動防火系統對火災發展的影響情況,本文以控制變量法為原則,交替模擬排煙系統、噴淋系統失效的火災場景,此外再設置排煙、噴淋均有效和排煙、噴淋均失效場景作為對照試驗(表1)。
2.2.1 火源設計
火源為用電設備老化引起的電氣火災,主要燃燒物為硬殼塑料、泡沫坐墊和刨花面板,經查閱《Handbook of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3]及NFPA 101A《Guide on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fe Safety》[4]中有關建材燃燒煙氣成分的測定結果,將該類型混合燃燒物的CO生成率設為0.016 g/g,煙粒子釋放率為0.035 g/g,火源尺寸為2.0 m ×1.5 m(圖3)。

圖3 火源位置示意
根據GB 51251—2017《建筑防煙排煙系統技術標準》第4.6節規定[5],該類型火災適用于火災增長系數α=0.011 kW/s2的中速發展火災,火源達到穩態時的熱釋放速率(最大熱釋放速率)分別為1.5 MW(有噴淋)、6.0 MW(無噴淋)。
火源熱釋放速率隨時間變化的公式為:

將火災場景1—4所對應的最大熱釋放速率Q及火災發展系數α分別代入式(1),計算可得各場景火源達到穩態燃燒所需時間t,如表2所示。

表2 Pyrosim火源參數設置
2.2.2 最小清晰高度
清晰高度指煙氣層下邊緣至室內地面的高度,一般而言,火災發生時,當煙氣層下邊緣低于設計最小清晰高度時即可認為煙氣已開始對人員造成影響。GB 51251—2017《建筑防煙排煙系統技術標準》第4.6節中指出,儲煙倉底部距地面的高度應大于安全疏散所需的最小清晰高度[5],清晰高度應按式(2)計算確定:

該層建筑層高為4.5 m,采用封閉式吊頂,吊頂底至室內地面的高度為3.0 m,計算最小清晰高度Hq時,H′應取值3.0 m,代入式(2)計算可得Hq=1.9 m。在火災模型中于室內地坪標高1.9 m處設置二維探測切片(2D Slice),用以探測火災模擬過程中最小清晰高度處煙氣層危害值的變化情況。
2.2.3 危害因素及危害值的確定
在火災煙氣模擬中煙氣層對人體的危害(危害因素)宜從毒性、高溫性、減光性這3個方面進行考慮。本次模擬試驗選用CO濃度作為煙氣層毒性參數,人體危害值設為754 mg/kg;選用溫度作為煙氣層高溫性參數,人體危害值設為60 ℃;選用能見度作為煙氣層減光性參數,人體危害值設為10 m。當某區域內的3項危害因素任一項達到危害值時即可認為煙氣已達人體的耐受極限,滯留人員將因難以忍受煙氣的危害性而自發轉移,前往未被煙氣侵襲的安全出口尋求逃生。
結合各火災場景實際模擬結果來看,上述3項危害因素指標中能見度指標達到設計危害值所需的時間最少,遠小于其他2項危害值超標所需時間,因此,本文著重記錄能見度指標在火災模擬過程中的變化情況。
2.3 火災場景1:噴淋有效、排煙有效
本火災場景為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有效、排煙系統有效模型,火源最大熱釋放速率為1.5 MW,火災增長系數為0.011(中速火),火災發展時間為369.27 s,模擬持續時間1 200 s,選取各安全出口附近清晰高度處能見度依次達到危害值的時間作為關鍵時間點,模擬結果如圖4所示。

圖4 火災場景1模擬結果
由模擬結果可知,當火災持續至334.8 s時,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已降至10 m以下,達到設計危害值,人員疏散開始受到影響,滯留人員因無法耐受煙氣危害而自發轉移至其他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503.3 s時,西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滯留人員轉移至南側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1 200.0 s時,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維持在10 m以上,可以認為此區域內煙氣尚不對滯留人員構成危害,人員尚有更多疏散時間可用。
2.4 火災場景2:噴淋有效、排煙失效
本火災場景為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有效、排煙系統失效模型,火源最大熱釋放速率為1.5 MW,火災增長系數為0.011(中速火),火災發展時間為369.27 s,模擬持續時間1 200 s,選取各安全出口附近清晰高度處能見度依次達到危害值的時間作為關鍵時間點,模擬結果如圖5所示。

圖5 火災場景2模擬結果
由模擬結果可知,當火災持續至185.6 s時,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已降至10 m以下,達到設計危害值,人員疏散開始受到影響,滯留人員因無法耐受煙氣危害而自發轉移至其他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375.5 s時,西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滯留人員轉移至南側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449.0 s時,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
至此,所有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的煙氣層均達到人體耐受極限,滯留人員完全暴露在煙氣之下,煙氣將造成該層尚未逃生人員的傷亡。
2.5 火災場景3:噴淋失效、排煙有效
本火災場景為自動噴水滅火系統失效、排煙系統有效模型,火源最大熱釋放速率為6.0 MW,火災增長系數為0.011(中速火),火災發展時間為738.55 s,模擬持續時間1 200 s,選取各安全出口附近清晰高度處能見度依次達到危害值的時間作為關鍵時間點,模擬結果圖6所示。

圖6 火災場景3模擬結果
由模擬結果可知,當火災持續至315.5 s時,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已降至10 m以下,達到設計危害值,人員疏散開始受到影響,滯留人員因無法耐受煙氣危害而自發轉移至其他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462.6 s時,西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滯留人員轉移至南側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687.2 s時,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
至此,所有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的煙氣層均達到人體耐受極限,滯留人員完全暴露在煙氣之下,煙氣將造成該層尚未逃生人員的傷亡。
2.6 火災場景4:噴淋失效、排煙失效
本火災場景為自動噴水滅火系統失效、排煙系統失效模型,火源最大熱釋放速率為6.0 MW,火災增長系數為0.011(中速火),火災發展時間為738.55 s,模擬持續時間1 200 s,選取各安全出口附近清晰高度處能見度依次達到危害值的時間作為關鍵時間,模擬結果如圖7所示。

圖7 火災場景4模擬結果
由模擬結果可知,當火災持續至186.9 s時,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已降至10 m以下,達到設計危害值,人員疏散開始受到影響,滯留人員因無法耐受煙氣危害而自發轉移至其他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365.0 s時,西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滯留人員轉移至南側安全出口尋求疏散;當火災持續至430.2 s時,南側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清晰高度處能見度降至10 m以下。
至此,所有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區域的煙氣層均達到人體耐受極限,滯留人員完全暴露在煙氣之下,煙氣將造成該層尚未逃生人員的傷亡。
3 模擬結果分析
對火災場景1—4的模擬結果加以總結,得出火災情況與人員可用疏散時間(ASET)的對應關系如表3所示。

表3 火災場景與可用疏散時間(ASET)對應關系
通過對比表3數據不難發現,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排煙系統對于火災時人員疏散時間的爭取均有積極作用,其中,排煙系統對于人員疏散時間的爭取效果十分明顯,噴淋系統對于疏散時間的爭取效果則較弱。這是因為噴淋系統主要通過抑制火災發展,限制火源達到穩態時的最大熱釋放速率來控制煙氣產生的快慢,其主要影響階段為火源達到穩定燃燒之后的階段,對煙氣的影響較為間接;排煙系統則通過直接抽取吊頂下方儲煙倉內的煙氣來達到延緩煙氣積累的效果,其對煙氣的影響更為直接,無論火源是否達到穩定燃燒,只要煙氣觸發火災自動報警系統排煙聯動控制程序,即開始產生影響。
4 結語
綜合上述分析,從人員可用疏散時間(ASET)的爭取角度來看,主動防火系統均成功啟動時,對人員疏散環境的改善效果最顯著,均未啟動(失效)時,火災環境最危險;排煙系統產生的正面效果相較于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更為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性能化分析具有針對性,即此次模擬試驗得出的結論僅僅只針對該層建筑的防火設計情況有效,并不具備普適性,譬如某些建筑物在滿足規范條件的前提下甚至可以不設置機械排煙系統,此時排煙系統與噴淋系統對火災抑制的貢獻程度將不具備可比性。因此,若想研究不同消防系統對火災發展的影響程度,或單純分析火災在現有建筑防火條件下的發展情況,還需合理搭建不同的火災模型,這也正是性能化分析的實際價值之所在——以計算機為平臺調整不同變量形成對照試驗,而無需搭建相應數量的實體火災場景。